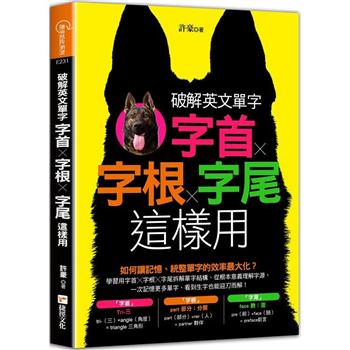我才十七歲,
但是擁有比誰都大的世界!
我才十七歲,我對這個世界知道一點,不知道的有很多點。知道的雖然只有一點,卻絕對是全部,而不知道的,全他媽的不重要。
我才十七歲,是個任女生糟蹋的年代。我隨時都需要一個女朋友,也隨時可以不要,陽光走了仍會回來,世界不就如此,總是陰陰晴晴。
我才十七歲,連考得爛都不孤獨,每個認識的人都圍在我身邊,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雖然我只有十三個人的電話,但我很少打電話,因為我們每天在一起。世界看起來很小,其實很大,大到十三個號碼便讓我忙不過來。
我才十七歲,我他媽的除了抽菸之外什麼屁也不懂,但我清楚知道,我擁有的是整個未來!
作者簡介
張國立
輔仁大學東語系畢業,通日文、英文、台語,通歷史、軍事、體育,事實上他從小就通曉事理。
他善於以文字蠱惑人心,從散文、雜文、詩、劇本,到小說、遊記無所不寫。才氣縱橫,囊括國內各大文學獎項,如:皇冠大眾小說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央日報文學獎、香港亞洲周刊華人小說獎等等。
他以重量級的史詩巨作《匈奴》贏得皇冠『大眾小說獎』百萬首獎!又以華人世界的『比爾?布萊森』般的嘲諷幽默寫出《一口咬定義大利》、《大齙牙咬到西班牙》、《兩個人的義大利》、《兩個人的日本》、《再咬幾口義大利》等旅遊文學作品,以及《亞當和那根他媽的肋骨》、《我真的熱愛女人》、《女人讓我缺氧》等兩性散文作品,本本都既叫好又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