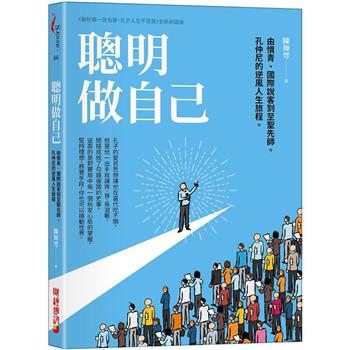米蘭.昆德拉的第一本小說!出版40週年紀念版!
榮獲捷克作家協會獎!
根據昆德拉親自修訂最新法文版重新翻譯!
就算我能將這幾天毫無意義的日子從我生命當中一筆勾銷,那我又能夠蒙受什麼利益?既然我一生的『整個』歷程本身即是以一場錯誤開展的:那張明信片的笑話,那次巧合,一個荒謬。我懷著驚懼覺悟到,由錯誤所孕育的事情竟然和由理性和必然性所孕育的事情同等真實。
一封明信片裡的玩笑,瓦解了路德維克的世界。愛情與友情輕如飛灰般消散空中,學籍和黨籍被撤銷,路德維克被列入黑分子,提前入伍,日復一日被勞動消磨心志、被粗魯敗壞靈魂。但在這裡,他遇見了露西,他情感的烏托邦,可是,露西卻逃離了他。
路德維克回到故鄉,回到他充滿恨的過去,進行一項復仇計畫。過去像夜裡的惡夢般緊緊揪住他,他全身驚顫、卻無力掙脫。也許,生命與歷史都是謬誤,也只是玩笑。
作者簡介
米蘭.昆德拉
一九二九年生於捷克的布爾諾。一九七五年流亡移居法國。作品有長篇小說:《玩笑》、《賦別曲》(榮獲義大利最佳外國文學獎)、《生活在他方》(榮獲法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的『麥迪西大獎』)、《笑忘書》、《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朽》、《緩慢》、《身分》、《無知》;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評論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簾幕》;此外還有一部舞台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靈感來自狄德羅小說《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譯者簡介
翁德明
現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譯有《被背叛的遺囑》、《簾幕》、《睡眠帝國》、《昨日之島》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