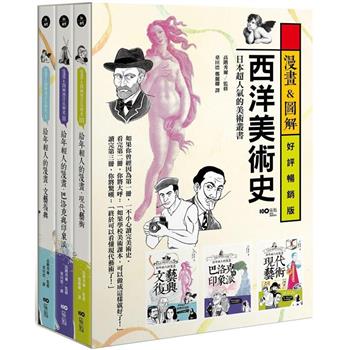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同學會』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
多年後,當你無預警的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對方報了名字,但你卻熊熊一下子想不起來。
在恢復記憶之前,必須一邊維持禮貌的應對,盡力不要讓尷尬的氣氛流得滿地都是,一邊在腦海裡搜索『檔案或資料夾』,同時祈禱老舊的記憶體別lag得太厲害……
現在,你終於想起來了。
不僅僅是對方的身分——原來這傢伙是你國中時代的班長——以及他那張十三、四歲時、被青春痘和細鬍根恣意攻佔的臉龐,你們一起上課的那間教室,每天都留到九點多的國三晚自習,巡堂扛著劍道用竹刀、拿尺跟剪刀檢查頭髮的機八訓育組長……
還有你暗戀過的那個女生。雖然她在你精心挑選的畢業紀念冊上,只寫了『努力用功,祝你考上好學校』這種令人心碎的芭樂留言……
突然之間,同學會成了連結過往記憶的甬道。
有趣的是它並不帶你回到過去,而是壓縮這些年來你所錯過的,直接將改變之後的結果一股腦帶到你眼前來。
這種混雜了已知與未知、懷緬與驚喜的狀況,最容易觸發情感上的波動。
出了社會,才漸漸能體會什麼叫『好對象難找』。
一介上班族,每天被操得死去活來,讓工作綁死在辦公室裡,生活中大部分的視野跟關注,都難脫這一塊彈丸大小的空間。大部分的公司行號不鼓勵辦公室戀情是有道理的,工作裡摻雜了太多的情緒,做不好那是天經地義。
去夜店或PUB把妹,或許能找到很好的床伴,但人生大部分的問題,不是打幾砲就能解決。
我們會寂寞、想依靠,希望被愛、被需要,甚至渴望有人一起分享夢想,規劃未來……這些,砲友都不能為你做到。
在選擇不多、出路困難的情況下,從(曾經)熟悉的人裡頭找伴侶,毋寧是一條可能殺出重圍的血路。
所以,現在辦同學會如果不提前一兩個月聯絡,整個就是沒人參加。因為女孩子要把握時間減肥、挑衣服,男生會開始考慮是不是要把年底換車的計畫往前挪。
我跟身邊周圍的朋友們聊到時,大家都一致認為:同學會是最容易讓班對舊情復燃、甚至跟老同學發生新戀情的可怕場合……
大三下學期的某一天,我接到一通奇妙的電話。
『喂!你猜猜我是誰?』很爽朗的女聲,語氣中帶著笑。
那是個電話詐騙還沒有被發明的年代,一切都十分的美好,我們還不習慣用一聲『幹』加掛電話來應付這種開場白。
我愣了一下,回答得小心翼翼。
『呃,我是李明煒耶!』小姐,妳可能打錯電話了,趕快發現吧!
『廢話!』她哈哈大笑,聽起來樂得很,完全就是女土匪的架式:
『我自己撥的電話,我會不知道嗎?你當老娘是智障啊!』
我一下子熊熊被嚇到,居然『喀嚓!』一聲,本能的把電話掛掉。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孬,不過我當時身邊周圍可沒有會自稱『老娘』的女生,怎麼想都像是碰到了神經病。我還在懷疑,對方怎麼會有我新宿舍的號碼時,天殺的電話鈴聲再度響起。
『喂……喂!』
『媽的!你敢掛我電話!』老娘明顯是氣炸了。
她越是理直氣壯,我就越怕自己腦筋短路,真的忘了什麼老相好。為了不得罪朋友,只好拚了老命用力回想:這到底是哪一路的強人……
『你該不會聽不出我是誰吧?』女土匪的聲音開始有些陰沉。
『呃,我……我這幾天感冒,耳咽管有痰堵住……』我心虛到不行:『而且妳那邊收訊不太好,要不要大聲一點?再說個兩分鐘之類的……』
女土匪突然安靜下來。
我以為她正在集氣,準備隔空發一招大絕『唰!』切斷我的頭。這種事情並非不會發生:電話可以通往母體,可以接上靈界空間,還可以打到女神事務所,突然來一道斷頭光波應該也是還好而已。
我屏住呼吸,沉重的心跳聲撞擊著鼓膜,耳咽管顯然是夠暢通了,怦怦、怦怦的悶響似乎迴盪在死寂的話筒兩頭……
如果從這裡開始筆鋒一轉,描寫我被光波斷頭後一直書寫文章至今,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故事。
但,事情的發展卻總是出人意表。
『你這個負心漢!』過了一會兒,她才幽幽的說:
『那年分手之後,你就忘記我了嗎?』
電影或卡通裡的大魔頭,都會犯一種很糟糕的錯誤。
每當反派佔盡上風,打得好人滿地亂爬的時候,就會開始很白痴的哈哈笑,然後卯起來打嘴砲,一直打到主角們集氣補血完畢,呼朋引伴一起來圍爐,一口氣逆轉得勝為止。
我從國中開始,一直到大三當下,從來沒交過女朋友!就算暗戀的女生,也只有一個剛打我槍的黃靜仍而已!
女土匪,在反派的路上妳還只是一個小孩。『言多必失』四個字會不會?回去寫一百遍明天交過來!
超越時代的腳步,我初次感受到詐騙電話的可惡之處;身為正義的一方,頓時理直氣壯了起來。
『非常抱歉,我從來沒交過女朋友!說,妳到底是誰?』
本來以為會有『哼哼,既然被拆穿了,你也滿有一套的嘛!』之類的對白,沒想到女土匪沉默片刻,突然爆出一串清脆爽朗的笑聲。
笑什麼笑?魔王破功就只有領便當而已,誰不是乖乖死掉?妳有看過反派不要臉的一直笑,笑到九局下半逆轉勝的嗎?別說是《新少快》、《星少女》,就連蓬萊仙山都不敢這樣演啊!
『妳再不說清楚,我可要掛電話了!』
『我是周令儀。』女土匪呵呵笑著,帶著一抹狡黠:
『說實話,你剛才根本就沒聽出來,對吧?死撐什麼啊!』
我愣了大約十秒鐘,腦海裡才倏然浮現名字主人的模樣。
記憶裡,周令儀總是用紅緞帶綁著兩條烏黑滑亮的粗大辮子,穿著黑皮面的女用學生鞋,就是腳背橫過一條細帶子的那種,雪白的短襪長度僅到踝上,把綴著蕾絲花邊的襪緣反折下來,清爽中有著說不出的規矩和文靜。
那個時候的女孩子都是這樣打扮,但周令儀可一點也不文靜。
她左邊的眉毛末梢有一條小小的縫線斜疤,據說是爬樹摔的;我記得她那時嗓門就有夠宏亮,好打抱不平,什麼事都要管,會抄起掃把追著一群男生跑遍整個校區,打得人人抱頭鼠竄……
想著想著,我忍不住嘴角上揚。
『我現在聽出來了。好久不見啦,大小姐有何貴幹啊?』
『這個星期天晚上,文化大學後面。』她自顧自說著,像連珠砲一樣:『你如果有機車就騎機車,開車也很不錯,我們六點要先集合……』
我聽得一頭霧水。
『等等、等等!星期天晚上……要幹什麼?「我們」,又是指誰?』
『同學會啊!』周令儀哈哈大笑:『你敢不來,就給老娘試試看!』
陪她笑了一陣,這次輪到我安靜下來。
周令儀似乎看穿了我的猶豫,出乎意料的耐心等待著。
反倒是我自己侷促起來,為了化解尷尬,我試著轉移話題。
『這麼快就要辦啦?上一次我記得是……』
『快五年前的事了。是高二那年辦的。』
她忍不住哼了一聲,我記得她從前似乎有輕皺鼻尖的習慣。
『如果我們的班長勤勞一些,或許你會比較記得我的聲音。』
她難得小心翼翼:『你……會來吧?』
『如果我說不去呢?』
『我會把你綁過來。』
周令儀是個說到做到的女孩子,有著眷村大姊頭的海派。
為了找出失聯已久的我,她打電話回我南部的老家,向我媽問到親戚牌愛心宿舍的電話,還有我的手機。我一點都不懷疑同學會當天,她會到樓下狂按電鈴,直到確定我會乖乖赴約為止。
從她擔任警衛股長的那天起,我就知道這丫頭絕對是狠角色。
『還……還有誰會去?』我垂死掙扎著。
她忍不住笑起來。
『其實,你想問的是「她」會不會去吧?都被我套出來了,原來你一直都沒交女朋友啊!嘖嘖嘖,這麼守身如玉。』
『不要用這種酒醉老頭子的口氣說話!』
『你該不會還在躲她吧?沒用的男人。』
『妳是專程打電話來戰的嗎?』
『你跟小蕙也算青梅竹馬吧?我以為你們一定會結婚咧!』
『……少說風涼話了。』
我有些哭笑不得,周令儀卻很樂,完全得理不饒人。
『小蕙她會去的。這次,你可別再逃走啦!膽小鬼。』
小蕙是我這輩子第一個寫情書的對象。
在我離開她們的生活以前,小蕙一直都是我的『老婆』。我們的課桌併在一起,我是全班作文寫得最好的男生,她是全班作文寫得最好的女生,我們用撕下來的筆記簿紙給對方寫信,對折兩次成小小的一方,就在桌子底下傳來傳去,玩著手摸手的遊戲。
如果只要說出『我愛妳』三個字,就算是某種愛情的承諾、無論是否了解其義的話,那麼小蕙可以算是我的初戀情人。
我們交換承諾的同時也交換了初吻,對我來說那是無比刺激的新體驗,對她的意義卻似乎全然不同。
那年,我們小學六年級。
這是一場小學同學會,我就是那個因為轉學、突然從周令儀她們的青春期裡缺席了的班長。
我原以為這不過是在茶餘飯後,可以拿出來隨興說笑的童年往事,卻不知在我所及之外,它已經悄悄改變了許多人,並在不久以後,將為我們帶來更巨大、更難以想像的改變……
從小,我就很有長輩緣。
遠的叔伯親戚、近的社區鄰居就不用說了,媽媽那邊的阿姨、舅媽,爸爸這邊的姑姑、嬸嬸……全都在我的守備範圍內。
老師當然也不例外。
比起漂亮的小男生或小女生,大人們更喜歡心地柔軟的孩子。
希望自己被喜歡、被肯定,不想替別人帶來困擾;遇到好的事情會由衷的高興,當別人遭遇悲傷時,也能夠感同身受……這些,都是『心地柔軟』的證明。只可惜現在的教育並不教小孩這些。
我一直覺得,小時候就懷抱著同理心的小孩,長大後也比較懂得愛——無論是接受或給予。
如果將來,我和我現在的女友琳終於有了為人父母的勇氣,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心地柔軟的小孩。
在我的那個年代,小學是以低、中、高年級為界,每兩年重新編班一次;換了新同學,順便賞你個痛快……不,是換給我們一個新導師。
我小學五年級的導師姓洪,是個體專畢業的女國手,專長似乎是手球或羽球。
對比我中年級的導師、剛從師院畢業的正妹陳麗妃老師,已經有兩個女兒的洪老師,顯得非常的幹練而嚴厲,被曬得通紅的面頰閃著一層薄薄的油光,連笑起來的眼神都像箭一樣的銳利逼人。
開學的第一天,整個教室裡異常安靜。
一方面是因為同學們還很陌生,吵也吵不起來,另一方面的壓力則來自教室後頭的導師辦公桌,洪老師低頭振筆,似乎是抄寫學生名冊之類的東西,強大的壓迫感在教室裡逐漸擴散……
等國中開始看《北斗神拳》、《聖鬥士星矢》等漫畫之後,我堅信洪老師那股強大的威壓感就是『鬥氣』——什麼小宇宙、北斗傳承,都是日本人唬爛出來的,但高手,絕對是真真實實存於我們的生活四周,就算潛伏在國民小學裡也不奇怪。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
這是洪老師開口對我們說的頭兩句話,然後才轉身,在黑板寫下自己的名字。
『這是我的座右銘。往後,我也會用這兩句話來要求你們。』
全班都嚇傻了,沒人敢隨便吐口大氣。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軍事化管理。
洪老師說到做到。她上課永遠拿著一根拇指粗的長藤條,活脫脫就是從家具工廠弄來的殺人兇器,只比掃把略短。我直到國中才知道有『教鞭』這種東西,但要說到夠威,前身是藤椅扶手的長藤條,才是體罰界的至尊王者啊!
洪老師打學生是不帶一點情緒性的,不會因為越打越high、搞到見血,也絕對不會因為你眼淚汪汪而打得比較輕。
我們在被打之前就已經知道要挨多少下,譬如早自習說話被登記的,要打兩鞭;月考成績沒到八十分的,少一分抽一鞭……諸如此類,公開報價,童叟無欺,你敢犯錯就得要有心理準備。此外,沾水的藤條打人真的是痛到不行!在我印象中,只有交叉編法的鱷魚皮帶能一較高下。
在我們從五年一班變成六年一班、最後由我代表畢業生上台致詞前,沒有一週是沒拿過整潔或秩序名次的。當時,每週評比第一名的班級,學校會把一塊『整潔(秩序)第一名』的牌子掛在走廊的班級牌下,象徵一種榮譽。
星期一朝會宣佈名次時,我的胃總是忍不住一陣痙攣。如果跌出前三名之外,全班每個人都要挨一下長藤條,身為班長的我則要挨三下。
『因為班長的責任比其他人重。』洪老師看著我說。
洪老師把全班分成六組,八張桌子拼成一個小組。全班第一名到第八名一組,坐在導師桌的正前方,這一組同時也是班級幹部,其他同學就混合打散。
我並不是全班第一名。洪老師為什麼挑我做班長,大家始終都不很明白。
『我也覺得很奇怪。』後來閒聊,周令儀總愛揶揄我:
『又不是養小白臉,老巫婆幹嘛一定要選你做班長?』
周令儀的嗓門最大,理所當然做了警衛(風紀)股長;坐在我旁邊的小蕙文靜秀氣,月考幾乎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洪老師派她做文化(學藝)股長。
一直到現在,小蕙在我心裡的樣子,都還是那麼樣的白皙安靜,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微瞇,靦腆中帶有一絲絲難以察覺的慧黠。
我就讀的國小附近,剛好有一個眷村,所以班上有將近三成比例的眷村孩子,周令儀是,小蕙也是。嚴格說來,她們才是真正青梅竹馬的姊妹淘,媽媽們還都是十幾年來同打一桌的牌搭子。
先說在前頭:雖然我是本省人,在將近二十年前的台北市,省籍已不算是壁壘分明的隔閡,現在更不應該是。我只是在述說一段逝去愛情的回憶而已,不希望被任何意識形態的指責與對立所污染。
在我看來,眷村的女孩有種颯烈直爽的特質。
無論是大咧咧的男人婆周令儀,抑或安靜害羞、笑起來柔柔怯怯的小蕙,骨子裡都是一處同生的直率女孩,有一種我無法企及的『剛』,迄今依然如此。
我跟小蕙是怎麼『在一起』的,坦白說記憶已經模糊。
奇妙的是:寫情書、送禮物這些追求的動作,是在我們已經是情侶之後才做的,似乎有些本末倒置。這或許反映了小孩世界裡的某種純真。
說到我跟小蕙的『交往』,就不得不提體育股長王亮宏。
王亮宏跟我是完全相反的類型:他的數理成績非常之好,體育更是強得驚人,長得高頭大馬,喉結凸出嗓音沙啞,連青春痘都比我早長了兩年,簡直一副國中生的樣子,在老師眼裡一整個就是『皮』。
洪老師常開玩笑:如果把我跟王亮宏揉在一起,再平均分成兩半,那就會得到兩個剛剛好的人。
瞎子都看得出來,從我們分到五年一班的第一天起,王亮宏就非常、非常喜歡小蕙。他會故意跑去鬧她,說些惹她瞪大眼睛的話,小蕙生起氣來,還會罕見的追打他。
王亮宏的家境也比我好很多,比我跟小蕙家都好。他們家裡有裝衛星小耳朵、有用Bata帶的錄放影機,聽陳百強、譚詠麟的廣東歌,吃剛進台灣的麥當勞,還試圖邀小蕙搭公車去西門町的日新戲院看電影……
回想起來頗為稚拙,但,王亮宏可是很認真的在追女生。
有動機、有自覺、有行動,大馬金刀,可說是陣仗分明。那種難脫青澀的早熟姿態,並沒有嚇壞一向乖巧的小蕙,他們一直都是不錯的朋友,到後來還是。
我常常忍不住想:小蕙,為什麼會跟我在一起呢?在我泛黃支離的記憶裡,實在想不起自己用了什麼撇步,能夠壓倒性的贏過『很像大人』的王亮宏。
最後歸納的結果,可能是因為一座天橋。
我們放學回家的路上,會經過一座天橋。回家路隊到了這裡,就不得不一分為二,王亮宏再怎麼像大人,回家就是得走左邊,而我和小蕙則是一起走右邊……
就這麼簡單。
我每天送小蕙到眷村裡她家的樓下,每天早上,又到同一個地方去等她。
眷村門口崗亭的伯伯會用一種了然於心的眼光看我,帶著讓我臉上一熱的曖昧笑容直搖頭。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同窗的圖書 |
 |
同窗 作者:法爾索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1-2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57 |
大眾文學 |
$ 169 |
社會人文 |
$ 175 |
中文書 |
$ 175 |
小說 |
$ 179 |
愛情小說 |
$ 179 |
現代小說 |
$ 17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同窗
張曼娟:『讀完《同窗》,我要說,戀愛是天賦;創作愛情小說,更是難得的天賦。』一段最純真也最感官的初戀故事!
張曼娟:『好看又動人的愛情小說,其實很難尋覓。好看的愛情小說,是舒緩而緊密的;動人的愛情特質,是悠長而深刻的。我在法爾索的《同窗》裡,竟然看見了這樣的結構與人物。』
『同學會』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
曾經跟朋友聊到,大家一致認為,同學會是最容易讓班對舊情復燃,甚至跟老同學發生新戀情的可怕場合!只是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而且是同時發生……
大三下學期的某一天,我接到一通奇妙的電話。往事突然歷歷奔來,我想起了曾經如此愛戀的小學同學小蕙,以及高中時她望著我那迷霧般的眼神。想起小學時『不小心』偷窺到大姊頭周令儀發育中的渾圓小丘;還有她高中時充滿女性魅力的身形線條!
我以為這一切都離我很遠了,誰知道在那一次的同學會後,她們卻讓我飽嘗天堂和地獄的滋味……
這是一個關於三場同學會的故事。作者以趣味、又極盡細膩和感官的描述,娓娓道來一位青春男孩的情慾初體驗。不管是情節的舖陳安排、情感的流動轉折、慾念的急迫渴望,都真實得令人心裡怦然!
作者簡介:
法爾索
七○年代出生,土象星座。披著行銷人的外皮行走社會,其實骨子裡非常想做編輯——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選第一份工作啊!一旦入錯行就再也不能回頭了(淚)。
嗜讀書,有蒐集精裝書及作者簽名的癖好,希望能一輩子看書看到死,一如『遠離賭城』裡痛飲求終的尼可拉斯凱吉。以收藏玩具、外國影集為樂,偶爾打打電動,吃吃美食;少時參加過中廣流行之星比賽,以致步入中年後,仍極其不要臉的以『歌神』自居。堅信人無論處於何種境地,都不能放棄為自己找樂子的重責大任。
每個男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孩子,這是真的。住在我心裡的一定是個好孩子。
章節試閱
『同學會』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多年後,當你無預警的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對方報了名字,但你卻熊熊一下子想不起來。在恢復記憶之前,必須一邊維持禮貌的應對,盡力不要讓尷尬的氣氛流得滿地都是,一邊在腦海裡搜索『檔案或資料夾』,同時祈禱老舊的記憶體別lag得太厲害……現在,你終於想起來了。不僅僅是對方的身分——原來這傢伙是你國中時代的班長——以及他那張十三、四歲時、被青春痘和細鬍根恣意攻佔的臉龐,你們一起上課的那間教室,每天都留到九點多的國三晚自習,巡堂扛著劍道用竹刀、拿尺跟剪刀檢查頭髮的機八訓育組長……還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法爾索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1-21 ISBN/ISSN:9789573323839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