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班的班花,綽號叫『蛋蛋』。
我讀大學的時候,印象中似乎還沒有PTT西斯板(註),所以『蛋蛋』二字,並未專指某種器官的憂傷。蛋蛋之所以叫蛋蛋,其實是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無巧不巧,居然也跟姓氏有關。蛋蛋的父親,祖籍是在大陸青藏一帶的奇妙地方,所以她們家的先人以名為姓,漢姓就叫做『旦』。也因為這樣,蛋蛋似乎帶有一點點維吾爾族的血統,皮膚有著西方人的白,毛孔卻又像東方人一樣細膩,就像剝了殼的白煮蛋一樣,有種難以言喻的白皙幼嫩。
在文學院的科系裡,除非女孩子的素質相差太過懸殊,『班花』這個頭銜至少需要一到兩個學期的時間角逐拼鬥,才能殺出個結果來。然而蛋蛋實在太特別了,幾乎是一開學就穩坐本班的班花寶座,並且隨著不斷有該死的學長跑來探頭探腦、大獻殷勤,隱然有躍居系花的態勢。
蛋蛋在社團裡也非常受歡迎。我在動漫社社辦看漫畫時,都會有不太熟的學長來打聽她的事,而且不只一次,當她的同班同學只能說是非常困擾。
蛋蛋家住台中市,媽媽是鋼琴老師,爸爸則經營皮革工廠。當年遇到台灣經濟起飛,做皮革加工的蛋爸賺了很多錢,她們家在台中、台北都有別墅,蛋蛋卻堅持要自己出來,跟班上的女同學一起租房子住,食衣住行都非常的節省;儘管如此,還是一眼就能夠看出蛋蛋來自富裕的好人家,教養良好,有種很特別的潛在氣質。
蛋蛋到底有多漂亮?我覺得五官長相這種事,只能說是見仁見智,就像大家都說超正的蕭薔,我從小就認為所正有限;後來與我有過一段情的Candy在公司是萬人迷,但當初我真的不覺得她是我喜歡的型。
蛋蛋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她全身充滿一種既矛盾又協調的美感。
她的皮膚很白、五官夠立體,卻有種東方女孩的嬌小可愛,你一點都不覺得她是混血兒或歸國子女之類的,就是很自然。她個頭很小,腿的比例卻很長,連臉都是小小一瞇的巴掌臉,又很愛笑,整個人就是很陽光,也不會扭捏作態。
『班花』聽來高不可攀,蛋蛋給人的印象卻非冷豔高傲的千金小姐,她會參加心輔社之類的社團,寒暑假去偏遠山區帶小朋友的營隊,而且擅長跑步,運動神經很發達;KTV是每唱必到,唱到high起來,會踢掉鞋子跳上沙發,抓著麥克風唱『裙襬搖搖』或『愛情限時批』。
蛋蛋跟誰都能打成一片,而且非常好約。她唱KTV是要趕場的,班聚、家聚、社聚……不管到哪裡都是一大群人。蛋蛋就像是恆星,無論是不是那一場的主角,永遠都被身邊的男男女女包圍著。
有經驗的人就知道,大二在大學歷程裡,是個很特別的時間點。
因為從這年開始,你就有了學妹。
有正妹同學當然是件賞心悅目的事,但平平是妹,『學妹』聽起來就是硬生生嫩了點,就算學妹重考兩年或五專插大,根本就是姊姊,然而只要有『學妹』此一頭銜加持,就是一整個卜脆脆……
如果男生在大一時沒有看對眼的對象,通常大二就會調整射擊角度,把目標轉移到新鮮嫩綠的學妹身上──所以,你就知道蛋蛋有多正了。即使低我們一屆的學妹們表現不差,但恆星永遠只有蛋蛋一個,誰都搶不走她的耀眼光芒。
除了阿凱,班上也有幾個男生跟蛋蛋表白,下場也都一樣。
其中對系務非常熱中、後來接了系學會的阿豪,被拒絕後失魂落魄了一陣子,上進青年的憂鬱氣質居然引來大一最正的學妹佩君青睞。他們一直交往到研究所,才因為阿豪要唸書出國,最終和平的協議分手。
走文藝青年路線的狗毛,大一就開始兼家教、很會賺錢的大蝦,則選擇了繼續在蛋蛋身邊默默守護。還有一、兩個社團的學長,雖然我跟他們有夠不熟,不過印象中都是滿不錯的男生,都能說得出才能或個人特色,我並不覺得是不好的選擇。
只是任他們誰跟蛋蛋在一起,旁人不免會有『不夠完美』的感覺。
很帥的成績不好,成績好的家境比不上蛋蛋,有錢的似乎又沒有才華……如果算上那些不知死活、肖想追求蛋蛋的大一學弟,我猜大二上學期,蛋蛋的好人卡大概幾乎發了一條清龍,簡直就是賭神高進的境界。
就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應該是蛋蛋最要好的男性友人。
這絕不是自high,在班上,我是少數能單獨跟蛋蛋一起出去吃飯的男孩子,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在蛋蛋有意無意的『熱心』催生之下,我已經跟黃靜仍約出去兩次了,一次去看電影,一次去北美館──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醒大家,電影院跟北美館都不適合跟不太熟的女生去。
它們的共通點在於『最好不要開口說話』,對感情的增進毫無幫助……
背負著『黃靜仍』這塊安全盾牌,蛋蛋就算跟我手牽手去咖啡廳,也只會被當成諸葛亮對劉玄德的面授機宜而已:這一切,都是為了漢室的復興!
蛋蛋畢竟是個女孩子。除了愛慕者,她偶爾也會想跟普通的男性友人吃吃飯、聊聊天,聽聽沒機會傳到她耳裡的八卦,說說每天不斷在她生活裡交錯閃現的男生。炳爺對這種事毫無興趣,我是所剩不多的安全選項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蛋蛋是真的很喜歡我對黃靜仍的那種老式作派。
『你最近有沒有寫情書給她?』她托著柔嫩的圓臉蛋,睜著明亮的大眼睛,又彎又翹的睫毛就像古代宮廷的排扇一樣;一瞬間,我忽然有暈眩的感覺。
『沒。我們上星期才出去過耶!』
『負心漢!』蛋蛋手指一比。
『才沒有!』我一下沒準備,被指得皮皮挫:
『妳這個標準……會不會太嚴格了一點?』
『那好。』蛋蛋眉開眼笑:
『為了證明你對黃靜仍是真心的,現在寫封情書來看看。』
我拿起真鍋桌上的原子筆跟餐巾紙。一轉頭,玻璃帷幕外的噴霧像小瀑布一樣淌下。
『不行!』她瞇著眼睛,笑出一側的小梨窩,眼縫裡透出一絲狡黠:『我今天沒戴隱形眼鏡,你要唸出來給我聽。來,開始。』雙手托起腮幫子,自己卻咯咯咯的笑了起來。
我清了清喉嚨。
『「意映卿卿如晤……」』
『你很煩啦!』意映卿卿生氣了,衝我的手背就是一巴。我只好認真一點。
『「星期天那部電影很難看,不過還好妳看得還滿開心的。感謝老天。下次我會約個比較能講話的場合,畢竟沈默也不算是我的專長……」』
蛋蛋哈哈大笑。
『那部電影真的很糟嗎?』
『爛透了。爛到我連名字都不想記起來。』
『是你選的還是她選的?』
我沒答話。
蛋蛋沈默片刻,忽然嘆了口氣。
『我媽說,手掌厚的男人耳根子軟。』
她抓起我擱在桌上的左手掌,輕輕摩挲著指丘的部分,笑著搖了搖頭。
『你啊,沒藥救了。』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蛋蛋為什麼這麼說。她從很早以前,就預見了我和黃靜仍的結局,只是她說的我並沒有懂。
咖啡廳裡,我任她撫摸著手掌,蛋蛋細緻柔滑的指尖刮過掌心,就像搔癢一樣,把我的心抽成一絲一絲的。似乎很曖昧,對吧?但我們真的就只是朋友而已。在蛋蛋的生活裡,幾乎沒有一點點像這種曖昧的空間,為了維持恆星的平衡,她必須公平對待每個懷抱情意而來的男生,所有的應對都經過審慎的考慮。
當我意識到這點的時候,才瞭解蛋蛋的難處。
被包圍在眾人之間,卻不能享有一絲一毫的模糊曖昧;蛋蛋差一點點,就會變成那種玩弄男人的mean girl,而她維繫善良的代價,就是必須要忍受恆星的寂寞。
恆星,其實是非常寂寞的。必須恆立在星系的正中央,即使被行星包圍著,也不能有一絲ㄧ毫的偎近或傾斜……
身為蛋蛋的好朋友,我能為她做的就是守住這點曖昧的空間,讓她不必煩惱擦槍走火,不必擔心我會變成另一個熱情燃燒的愛慕者;在玻璃帷幕裡,在真鍋咖啡的噴霧瀑布下,可以由著她小小任性一下。這個時候的蛋蛋非常真實,一點也不特別,可愛與不可愛的地方,都跟其他的女孩子沒什麼不同。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蛋蛋只是個普通的女孩子而已。
下學期的某個星期天,我鬼上身的想看漫畫,又不想花錢去租,於是騎著耳東的腳踏車到學校的動漫社去。
耳東買了兩輛越野自行車,一輛賠給炳爺,一輛留下來自用──過了前兩週的興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我在騎。
星期天的下午,學校裡的人其實也不少,只不過大部分未必是學生,而是附近社區的居民來散步運動,所以少了很多平常見慣的熟面孔。我把腳踏車牽進男一舍的穿堂,打算寄放在同學的房間,免得被偷;隔著老舊的窗紗,我忽然看見蛋蛋和潘帥並肩走過,一路往坡下走。
蛋蛋雙手環抱著幾本書,跟潘帥有說有笑。
比起大部分追求蛋蛋的男生,他並未刻意靠近蛋蛋,也沒牽她的手,從我這個角度看過去,幾乎可以判斷他完全沒有觸碰她身體的意圖;所以,蛋蛋顯得非常輕鬆放心,就像走在我或炳爺身邊一樣。
走著走著,兩人停在三叉路前。潘帥比較靠近上坡路口,那是要往圖書館的路;蛋蛋則是背向下坡,往下走就是社團辦公室,顯然這裡是同行的終點。
他們聊了很久,潘帥從背後拿出一疊像筆記紙一樣的東西,遞給蛋蛋;她伸手要接的一瞬,他突然把紙舉到頭上,嬌小的蛋蛋搆不著,忍不住輕輕揍了他肩膀一下,笑著又叫又跳。
這是很親暱的動作,如果潘帥願意,短短三十秒內可以乘機佔點便宜,捏捏手、靠靠肩什麼的。甚至蛋蛋跳得太過頭了,飽滿的胸部差點撞到他身上,他都巧妙的往後讓一讓,一丁點侵略性也沒有。
我瞬間有種對不起他的感覺。
原來我的好朋友並不是不尊重女孩子的花心大蘿蔔,過去是我誤會他了……
忽然吹來一陣風。
映著酒紅色的陳舊瓷磚,不知名的黃色小花隨風落下,黃豔豔的小碎瓣沾上蛋蛋的臉龐,和著前額吹亂的細柔髮絲。雙手抱書的蛋蛋縮著脖子,本能的微微轉頭;就在一瞬間,潘帥替她拂去了鼻尖、臉龐沾著的小黃花,勾著她的鬢髮繞到耳後。
這個動作非常快,同時也非常輕柔。
蛋蛋露出錯愕的表情,但卻動也不動,直到潘帥的小指尖滑過她的耳後,沿著下頷邊撫過白皙的頸側,臉蛋才一下子『唰』地變得緋紅。可能是我的錯覺,我覺得她的身體微微發抖,道別後跑下階梯時,修長細直的美腿似乎有些踉蹌……
我終於懂了。
原來……這就是我一直想提醒蛋蛋要逃離的。
當潘帥以風林火山的姿態攻城掠地時,耳東還在持續他的白爛戰法。
有一次我聽到他跟蛋蛋講電話,從單方面的應答大致可以判斷:耳東邀請她吃宵夜,當然是被拒絕了,所以耳東想帶宵夜去看蛋蛋。
『這妳一定愛呷!嘸好吃我乎妳蹔!』
『來啦來啦……啊,嘸要緊!我帶去乎妳呷……』
蛋蛋最後答應了──當被足足糾纏一小時,就算他要帶汽油桶和番仔火來,恐怕也會一口答應。沒有比能立刻掛上電話更好的了,管他要幹什麼!
耳東歡天喜地的跑去買花枝羹,我卻不由得搖頭嘆息。這根本就不是追求,而是騷擾;這種事情再做一百次都沒有用,只是徒然消耗蛋蛋的耐心而已。比起潘帥,耳東不僅不是對手,根本就是來幫忙的。
爬上五虎大旅社,我轉動鑰匙鎖孔。
門打開的瞬間,我看到蛋蛋從飯廳的椅子站起來,白皙的臉頰羞得緋紅,低著頭小跑步的往大門衝來,差點撞到我身上。
『啊……』她抬頭才發現是我,更加手足無措,什麼也沒說就下樓去了。
跟著追來的是潘帥。如果不是他早一些發現我進門、本能放慢了腳步,嬌小的蛋蛋可能已經被一百八十公分的潘帥追上,我甚至可以想像她被一把拉住的畫面……
潘帥停下腳步,無言的看著我。
我身旁的空隙足以讓蛋蛋側身鑽過去,高大挺拔、肌肉發達的潘帥卻不行。
當時我的表情一定非常陰沈。他猶豫很久,勉強笑了一笑。
『借過。』
『你到底想幹什麼?』不知哪來的火氣,我踏前一步,鼻尖幾乎跟他撞在一起:
『你已經跟小緹學姊在一起了,到底還想要幹嘛……』
潘帥突然皺起眉頭,冷不防的一舉手,『碰!』把我的肩膀揮到門板上,懸空的鐵門重重撞上樓梯間的牆壁。我身體形成的軟弱壁障崩潰了。
『我的事,你不要管。』他看了我一眼,大步追下樓去。
『蛋蛋也是我的朋友!』我不甘心的大吼,聲音迴盪在破舊的老公寓裡。
我把裝滿漫畫的包包往耳東床上一丟,直覺的跑去拍阿凱的房門。
砰砰砰、砰砰砰……阿凱不在,手機關機。其實,我猜也猜得到,阿凱如果沒在房裡打電動,肯定上課去了;良哥也沒膽子翹C教授的課。
忽然間,我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印象裡潘帥永遠在笑,是個很nice、很nice的人。我不得不承認:剛才那個掄我去撞門的潘仲立是另一個陌生人,我被他的氣勢所懾,完全無法獨自應付。
我知道還有一個人也翹了課。但,我不能打電話給耳東。
懷抱著猶豫與茫然,我扛著耳東的越野車衝下樓,巷子的兩頭不見人影,我腦海中靈光一閃,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往神水宮的方向。一邊踩著腳踏車,我慢慢恢復了鎮定。
騎過兩條街,我追上了蛋蛋和潘帥。
蛋蛋雖然比例修長,其實也才一百六上下;儘管潘帥被我耽擱了一下,還是追上了她。
兩人在巷子裡一前一後的走著,潘帥始終跟在蛋蛋背後,每當即將並肩的時候,蛋蛋就三步併兩步的超前一些,低著頭、環著肩,渾身上下充滿警戒。在我看來,那只是溺斃之前,軟弱無力的垂死掙扎。
心中無礙的蛋蛋,一向可以很坦然的走在男孩子身邊。抱住肩膀其實什麼也攔阻不了。
我跳下越野車,遠遠的牽著、跟著。
原本悶熱的天,無預警的下起雨來。
如果你問我,我會說雨是一種很催情的東西。
被淋濕的衣服緊貼肌膚,有種赤身裸體、卻又被細細撫摩的曖昧;濕重的布料涼涼的、漿挺的,摩擦著乳尖、下腹、大腿內側及膝彎,力道不輕不重,卻又無法忽視不理,那是最高明的撫摸技巧。還有那種濕滑、水不斷淌下的感覺……全身浸泡在水中游泳,只能讓我們憶起在母親羊水裡的感覺,淋雨卻充滿著性暗示。
愛撫是可以達到高潮的。大自然藉由雨水的滋潤,不斷提醒著我們。
潘帥輕輕拉了蛋蛋一下。
蛋蛋像受驚的小鳥一樣,本能的揮開了他;兩人一前一後繼續走著,潘帥又拉了一下,動作一樣輕柔,一樣也是一沾即走。
蛋蛋可能沒料到這麼容易掙脫,大動作往後一揮,細棉質的白色薄外衣扯開來,小露出線條圓潤的左肩,沾著雨珠的白皙肌膚映著蘋果綠的細肩帶。
抗拒與追求,都是飽含激情的動作。我一直到了二十五歲以後才明白,『不斷推拒』,在某種意義上與『奮力迎合』共用一個情感平台,就像愛與恨都是非常濃烈的情感,儘管趨向不同,熾熱的程度卻無分軒輊。
不斷揮手抗拒的蛋蛋,正一步一步,落入潘帥的性愛陷阱之中。
憎惡、驚怕、惶惑、慾念、渴求……情緒累積到刻度的最高點,崩落的一瞬間就再也沒有差別。蛋蛋的步伐越來越碎,動作越來越慌,潘帥的輕扯越來越密集,停滯的時間越來越長,從她的肩、臂、手腕到手指……
在他們消失在騎樓的轉角之前,看起來就像一對爭吵後將以做愛癒合的情侶。
我牽著越野車繞到騎樓的另一側,突然愣住。
隔著凌亂的機車腳踏車,蛋蛋背向我,雙手抱胸,腳尖踮起,被潘帥像抓小雞一樣的緊緊擁在懷裡,姣好的嬌小身軀不停顫抖。
潘帥看見了我,表情卻不怎麼錯愕,眼睛就直望著我,低頭湊向蛋蛋的嘴唇。
在他低頭的一瞬間,我看見站在騎樓的另一側,兩手提著三個培育箱的耳東。蛋蛋微微一顫,纖細的腰板一下子僵硬起來。
大雨唰唰傾落,像是天空裡打開了瀑布的開關,地面的悶熱一瞬間蒸騰汽化,隨著雨風捲進騎樓裡來。我不忍再看,心中祈求老天,不要對耳東這麼殘忍。
耳東只是看著,什麼都沒說。
他的安靜攫住了我的注意力,讓我無法移開目光。
那是……那是種什麼樣的眼神?嫉妒?慌張?痛心疾首……和預期全然不同,耳東就是靜靜的看著,眼神平和卻不擔心,就是看著而已。
蛋蛋被他注視著,突然就掙開了潘帥。
潘帥露出錯愕的表情,伸手抱她的肩。這次蛋蛋沒揮手,只是退了一步。
曖昧的氣氛消失了。
蛋蛋躲進了她最堅固的堡壘,潘帥的魅力、催情的雨水,都無法再侵蝕她的理智與矜持。
多年後,當蛋蛋、潘帥、耳東都走出我的生活,我才慢慢明白:耳東對蛋蛋的意義,從騎樓下的這一眼才真正開始。
我的朋友,並不是一個供人取樂的丑角,儘管他毫不介意做大家的開心果。耳東沒有潘帥的調情手段,不如阿凱精明,也不像良哥有那種天真傻氣的浪漫,或者跟我一樣,會為蛋蛋守護著一點微不足道的小小曖昧;他只是信任著她而已。
而相信,是一件很難的事。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耳東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耳東 作者:法爾索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8-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42 |
愛情小說 |
$ 142 |
大眾文學 |
$ 158 |
中文書 |
$ 158 |
小說 |
$ 162 |
現代小說 |
$ 16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耳東
愛情不怕發生什麼,而是怕『什麼都沒發生』……
追求美女可不是光有勇氣就行的,
那麼,外號『耳東』、條件上有點『缺陷』的這位同學,
要怎樣才能阻止班花『蛋蛋』,再發出好人卡一張哩?
我們班的班花綽號叫『蛋蛋』,是個子嬌小的可愛型美女,有著白皮膚、小梨窩和動人的甜美微笑。蛋蛋跟誰都能打成一片,而且非常好約,班聚、家聚、社聚……蛋蛋就像是恆星,不管到哪裡,身邊總是環繞著一大群人,而就在蛋蛋的生日那天,耳東也成了她可愛微笑的俘虜。
雖然外型可以直逼柏原崇、但屬性『諧星』的耳東同學,從自願當挑夫、到逛街全陪,連『黃金角蛙』都養了……但是,這樣是很難贏得愛情的。耳東沒有潘帥的調情手段,不如阿凱精明,也不像良哥有那種天真傻氣的浪漫,或者跟我一樣,會為蛋蛋守護著一點微不足道的小小曖昧。
當蛋蛋被潘帥擁入懷中親吻時,耳東也只是看著,什麼都沒說。那是什麼樣的眼神?嫉妒?慌張?痛心疾首?……但是和預期全然不同,耳東就只是靜靜的看著,眼神平和卻不擔心。但蛋蛋被他注視著,突然就掙開了潘帥……
我們都喜歡蛋蛋,跟耳東更是麻吉,美女與野獸或許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美女與諧星呢?
作者簡介:
法爾索
七○年代出生,土象星座。披著行銷人的外皮行走社會,其實骨子裡非常想做編輯——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選第一份工作啊!一旦入錯行就再也不能回頭了(淚)。
嗜讀書,有蒐集精裝書及作者簽名的癖好,希望能一輩子看書看到死,一如『遠離賭城』裡痛飲求終的尼可拉斯凱吉。以收藏玩具、外國影集為樂,偶爾打打電動,吃吃美食;少時參加過中廣流行之星比賽,以致步入中年後,仍極其不要臉的以『歌神』自居。堅信人無論處於何種境地,都不能放棄為自己找樂子的重責大任。
每個男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孩子,這是真的。住在我心裡的一定是個好孩子。
章節試閱
我們班的班花,綽號叫『蛋蛋』。我讀大學的時候,印象中似乎還沒有PTT西斯板(註),所以『蛋蛋』二字,並未專指某種器官的憂傷。蛋蛋之所以叫蛋蛋,其實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個原因無巧不巧,居然也跟姓氏有關。蛋蛋的父親,祖籍是在大陸青藏一帶的奇妙地方,所以她們家的先人以名為姓,漢姓就叫做『旦』。也因為這樣,蛋蛋似乎帶有一點點維吾爾族的血統,皮膚有著西方人的白,毛孔卻又像東方人一樣細膩,就像剝了殼的白煮蛋一樣,有種難以言喻的白皙幼嫩。在文學院的科系裡,除非女孩子的素質相差太過懸殊,『班花』這個頭銜至少需要...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法爾索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8-11 ISBN/ISSN:9789573324485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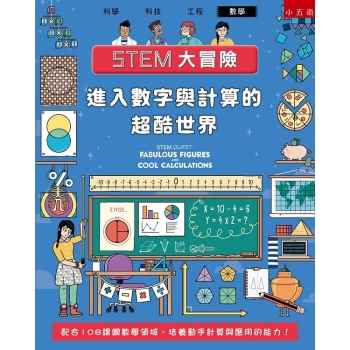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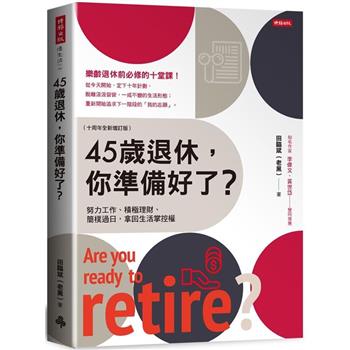






<耳東>是一本很發人深省的書,作者法爾索善於觀察人性、觀察朋友們對於戀愛的想法以及,法爾索高明的人物刻畫技巧讓我傾倒。大家不妨想想自己身邊是否有這些類型的人──永遠像是恆星的蛋蛋,或者是子路再世、令人噴飯的耳東,他們其實都存在──而這本書之所以令人深省,也正是因為法爾索點明了我們一直以來不曾想過或不願意去想的問題。 我認識這樣一顆恆星,小小的,可愛的不得了,永遠都不缺人陪伴寵愛──但我發現我竟一點也不懂得她的寂寞,或者說,我們不懂,是因我們在地平線上仰望,而非從恆星的高度來平視天空。我知道,要當這樣一顆恆星,真的很難。 耳東是一個非常奇特的角色,像子路一樣。但這個人太厲害了,細膩體貼的不得了。所以,當書末寫道小小和耳東的結局時,我是開心的。蛋蛋太好,有一點讓人不知所措,讓人卻步的心動。 謝謝法爾索,你始終站在一個超然的角度,完成這一切,縱使你錯過了某些心緒,但這樣的結局是完美的。<耳東>是一本很發人深省的書,作者法爾索善於觀察人性、觀察朋友們對於戀愛的想法以及,法爾索高明的人物刻畫技巧讓我傾倒。大家不妨想想自己身邊是否有這些類型的人──永遠像是恆星的蛋蛋,或者是子路再世、令人噴飯的耳東,他們其實都存在──而這本書之所以令人深省,也正是因為法爾索點明了我們一直以來不曾想過或不願意去想的問題。 我認識這樣一顆恆星,小小的,可愛的不得了,永遠都不缺人陪伴寵愛──但我發現我竟一點也不懂得她的寂寞,或者說,我們不懂,是因我們在地平線上仰望,而非從恆星的高度來平視天空。我知道,要當這樣一顆恆星,真的很難。 耳東是一個非常奇特的角色,像子路一樣。但這個人太厲害了,細膩體貼的不得了。所以,當書末寫道小小和耳東的結局時,我是開心的。蛋蛋太好,有一點讓人不知所措,讓人卻步的心動。 謝謝法爾索,你始終站在一個超然的角度,完成這一切,縱使你錯過了某些心緒,但這樣的結局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