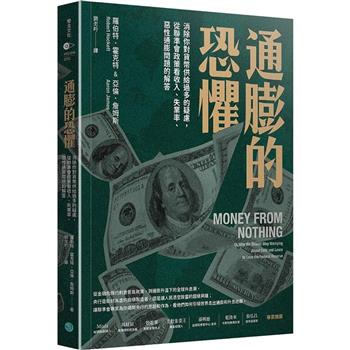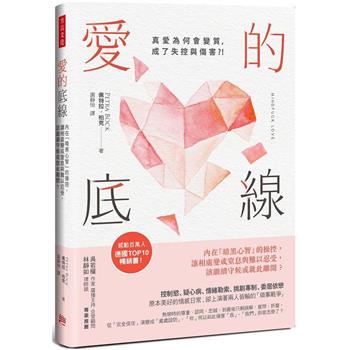飲食之樂不分東西,
飲畢食盡,浮上心頭的卻往往不只味道,
還有那食物背後最溫潤的回憶!
飲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享受一道又一道的佳餚時,人們入腹的不只是美味,還有更多的風土源長。譬如常見的漢堡排,其實是航海家改良過的產物,再融入現代文明的速度感後,就成了漢堡包;而樸拙、美味又能充飢的食物如玉米粥,則往往誕生在民生困頓的地區,充分表現出當地居民的精神群像。飲食也是文化交融、彼此提昇的最佳例證,像是中西合併的甜酸肉、雜碎菜,甚至台式西餐,新誕生的混血小兒糅合了父系母系的秀異風味,自成一格之後竟也卓然一方。
包括食物的身世、食材的烹調手法,乃至菜餚的地域轉變,每道菜上桌時,其中的歷史流轉與內蘊文化往往饒富探究的趣味。而說到東西美食文化,又有誰比居遊各地、遍嘗美食的韓良憶更適合評點品味?這次良憶便或爬梳食物的歷史來由,或介紹各地的風味料理,讓食物的味道因而愈顯出豐富的層次,而良憶筆下食物與回憶的微妙關連,也更加添了食物之所以能感動人的風味。
和良憶一起《吃‧東‧西》,你當能體會食物最純粹的美好!
作者簡介:
韓良憶
生活美食家韓良憶。
喜歡簡單的生活,認為生活中只要有好吃的食物、好聽的音樂、好看的書和電影,平日能在家附近散散步,一年至少去旅行一次,就很好了。尤其吃和音樂是最容易取得的樂趣,一日不能缺。
覺得吃東西時影響自己最多的是心情和食物的本身,再來就是一起吃的人。一看到就想買的CD,有Van Morrison、John Coltrane和Miles Davis。喜歡的作家很多,最喜愛又敬佩的『偶像』是已故的美國飲食文學作家M.F.K.,只要買得到的書,全部都收集了。
覺得幸福就是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但是對人生仍懷有夢想。總覺得,沒有夢的人生,不值得活的。
正因為如此,目前定居荷蘭,雲遊四海,依舊繼續享受著美食和旅遊的生活。
章節試閱
鴨的回憶
晴朗的午後,不知怎的,突然想念起一樣既屬於他鄉卻又依稀熟悉的味道,於是搭著電車,叮叮噹噹來到鹿特丹西區,這裡有家法國食品店,我每隔一陣子總會上門光顧,買些別處沒有的食材。
這一天,勾起饞癮的是來自法國西南部的油燜鴨肫和煙燻鴨胸肉,這兩樣都是現成的熟食,不必再加熱烹調,只要拌上兩、三種生菜、水煮嫩四季豆和核桃仁,淋上油醋芥末醬汁,就是一大盤色彩繽紛、份量十足的西南法風味什錦沙拉。
油潤卻有嚼勁的鴨肫和帶著燻香的嫩鴨肉一入口,旅途中的種種回憶,便栩栩如生地回到眼前。幾年前,我和丈夫兩度在西南法鄉下租了小屋居遊兼度假,就是在那裡首度嘗到油燜鴨肫,學會做這道沙拉。
油燜鴨肫是法國鄉土名菜油燜鴨(confit de carnard)的副產品,所謂油燜,就是用鴨油燜煮大塊的鹽醃鴨肉和整副的肫肝,文火燉熟燜爛了以後,連料帶油一股腦兒裝進陶盅裡,封存起來。在尚無罐頭亦無冰箱的時代,這個作法讓農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兩口肉,打打牙祭。
我本來就愛吃鴨肫,頭一回吃到西南法的油燜鴨肫,更深深愛上了那鹹中帶甘、越嚼越香的滋味,我嚼著嚼著,腦海中某個塵封的抽屜似乎被開啟了,原來這油燜鴨肫的味道,挺像我少女時代常吃的鹽水鴨肫。
當時我們家住在台北東門一帶,我每天放學後嘴饞,常到一家小店買個鴨肫,當零嘴吃,一吃就是好幾年,直到小店因為店主移民出國而歇業。這會兒一算,才驚覺人生匆匆,我竟然有二十多年沒再嚐到那滋味了。
從鹽水鴨肫又聯想到幾樣我很愛吃的鴨肉菜餚,好比鹽水鴨、樟茶鴨和近年在台灣被媒體炒作得火紅的北京烤鴨。小時候的我有點挑嘴,不愛吃雞,就喜歡吃鴨肉,母親曾開玩笑說,她這個女兒上輩子一定跟鴨子有仇,不然怎麼那麼愛吃鴨,一聽說爸爸要去台北伯伯家打牌,準會請求爸爸去伯伯家附近的鹽水鴨店買個半隻帶回新北投;全家一起上館子吃川菜,鐵定要求點樟茶鴨;而到『真北平』、『同慶樓』和『天廚』等北方館子時,更一副樂滋滋的模樣,因為今兒個可以痛痛快快大啖烤鴨啦。
媽媽提了這麼多餐館,偏偏就沒提到西門町的老店『鴨肉扁』,我好愛吃那裡的切仔米粉和白切『鴨』肉呢,還記得那兒的米粉,湯面汪著油,卻香而不膩,『鴨』肉也很嫩,一點都不老不柴,可惜爸媽很少帶我去,一來是因為出身江蘇的爸爸吃不慣那股油蔥味,二來是因為當時的『鴨肉扁』用餐環境有點邋遢,媽媽嫌不夠衛生,怕孩子胃腸弱,吃多了拉肚子。
這會兒再一想,媽媽沒提『鴨肉扁』,或許不是忘了,而是因為店家的名字裡雖有『鴨』字,賣的卻不是鴨肉,而是鵝肉。有關這一點,我知道的很晚,晚到自己都已經開始寫作,忝為所謂的食物作家以後,跟人聊起,才發覺多年來的錯誤,好不慚愧。怪不得我小的時候就老在納悶,那兒的鴨子怎麼會一隻隻都那麼龐大哩。
在低地國港都的一隅,我吃著來自法國的鴨肫和鴨肉,想起這些或甜美或可笑的瑣碎往事,突然覺得,人有味覺能品嚐酸甜苦辣,有往事能回味,真是件幸福的事。味覺帶給人的,不僅僅是感官的享樂而己,它還可以是通往過去、開啟記憶大門的鑰匙。回憶點點滴滴,如音符一般,組成了生命這首樂曲的基調,讓人在緬懷往事的同時,還有力量把握現在,有勇氣面對未來。
至於在這個清風徐徐的週末下午,儼然驅策著我專程上街購物解饞的,到底是西南法還是台北的回憶呢?答案或許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擁有這些記憶,並因而真真切切地感到,活著,真好。
從地中海到台灣海峽
今年夏季到普羅旺斯租了間農舍半居半遊,有天開車兜風,逛到馬賽西邊的漁港瑪提格(Martigue)。既是漁港,必有海鮮,吃海鮮遂成一行四人來訪的主要目地。
在一家小館子坐定,大夥公推我看菜單,我的法文程度極馬虎,就是讀菜單還勉強過得去,這一回卻一眼就瞧見一個陌生的單字,這 poutargue,究竟是什麼玩意呢?
『那是本地的特產,』胖胖的掌櫃解釋說:『就是鹽漬風乾過的灰鯔卵,下酒很好吃。』那不就是烏魚子嗎?這倒稀奇了,我早知義大利的薩丁尼亞和西西里這兩個島嶼都出產烏魚子,卻不曉得普羅旺斯人也吃這一味。
四人合點一份嚐嚐,大大的瓷盤上擺了黃檸檬,還有八、九片切得很薄的烏魚子,色澤比我熟悉的台灣烏魚子深了點,紅中帶棕。掌櫃建議,食時宜擠點檸檬汁,淋少許橄欖油,我聞言照辦,一吃便明白這種食法有其道理,因為這裡的烏魚子未經炙烤或油煎,基本上是生的,味較腥、略鹹,質地則偏乾,甚至有點硬,加點油和酸檸檬汁,有滋潤、去腥的效果。我覺得還是台灣的烏魚子較可口,不過這說不定是我先入為主,吃慣台灣口味之故,搞不好人家普羅旺斯人會嫌台灣貨較油膩,味道不夠濃呢。
我從小就愛吃烏魚子,這是從母系傳承過來的口味。兒時跟著媽媽到出身台南的阿嬤家食『腥臊』(即台灣北部人講的『豐沛』,意指吃一頓大餐),桌上必有盤烤烏魚子,一片片橙黃帶紅,間雜著著潔白的蘿蔔片與斜切的青蒜片,煞是好看。阿嬤家的烏魚子可不是店裡隨便買來的,而是她老人家親自到興達港選購新鮮魚子,請人醃製而成,形體特別碩大,顏色也格外飽滿。
阿嬤烤烏魚子必用炭爐,魚子烤前需浸泡米酒一會兒,而後仔細剝除薄膜,置於燒紅而無焰的木炭上烤之,其間需不時翻面,烤到兩面金黃起泡,此時的烏魚子外層似焦未焦,裡面則未全熟,軟嫩油潤,有股原始而迷人的味道,佐以甘甜多汁的冬季蘿蔔,滋味一濃陳一清新,口感一軟一脆,彼此烘托,相得益彰,嗜之者如阿嬤、媽媽乃至我,皆以為美味至極,惡之者如父親和我的洋丈夫卻覺得太腥,簡直難以下嚥。人的口味歧異竟如此之大,真是說不出道理的事,令我不禁想起宋人蘇易簡廣為傳頌的食家口訣:『物無定味,適口者珍』。
烏魚子時至今日已是台菜的代表菜色,我原以為這道『台灣料理』乃是日本殖民時代的遺風,後來翻閱史料才發覺,早在十七世紀荷蘭據台時代,漢人漁民便已在荷蘭人鼓勵下,在台灣海峽捕烏魚並製作烏魚子,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就記載說,烏魚『卵帶紅色,外膜厚,以鹽漬之,中國人視為珍品』,由此可見,在日本時代以前,台灣人就已懂得吃烏魚子了。
至於日本人,則是在十六世紀時開始食用此物,日本人稱之為『唐墨』,因為其模樣肖似墨,由這個『唐』字看來,烏魚子或有可能是從中國傳到日本。這下子問題來了:中國人是怎麼學會醃漬烏魚子的呢?
我不知翻了多少資料,都得不到定論,倒是讀到,地中海一帶早在三、四千年前便已有類似食品,據信是腓尼基人所創製。南歐諸國至今仍視烏魚子為美味,義大利人稱之為bottarga,法國人叫它boutargue,在西班牙人口中則是botarga,這三個字加上瑪提格人說的poutargue和希臘文裡的avgotaraho,都是從阿拉伯文中的bitârikh衍生而來。
說來說去,會不會搞了半天,不論是中國、日本或台灣的烏魚子,統統是地中海文明的遺緒?難道說,我在普羅旺斯吃到的乾硬烏魚子,才是它的本色?
鴨的回憶晴朗的午後,不知怎的,突然想念起一樣既屬於他鄉卻又依稀熟悉的味道,於是搭著電車,叮叮噹噹來到鹿特丹西區,這裡有家法國食品店,我每隔一陣子總會上門光顧,買些別處沒有的食材。這一天,勾起饞癮的是來自法國西南部的油燜鴨肫和煙燻鴨胸肉,這兩樣都是現成的熟食,不必再加熱烹調,只要拌上兩、三種生菜、水煮嫩四季豆和核桃仁,淋上油醋芥末醬汁,就是一大盤色彩繽紛、份量十足的西南法風味什錦沙拉。油潤卻有嚼勁的鴨肫和帶著燻香的嫩鴨肉一入口,旅途中的種種回憶,便栩栩如生地回到眼前。幾年前,我和丈夫兩度在西南法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