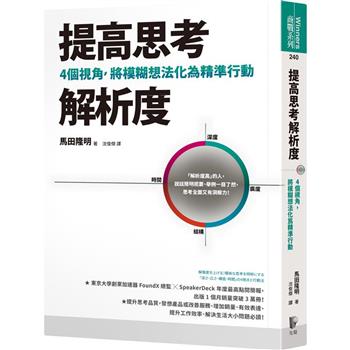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人間喜劇的圖書 |
 |
人間喜劇 作者:胡晴舫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小說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人間喜劇
人性的運作方式如此奇特,
這一幕幕身不由己的喜劇才能悲哀得如此精彩……
兩個世紀前,法國有大作家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道盡十九世紀巴黎的人性興衰;兩個世紀後,旅居香港的胡晴舫,則寫出了屬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下的《人間喜劇》。
十則短篇故事,跨越中、港、台及歐、亞各地,有人們在愛情、財富、權力、工作之間的種種掙扎,也有逃脫不了的貪婪、背叛與慾望。
以文化社會評論見長的胡晴舫,文學作品一向量少而質精,在一貫濃厚都會性及現代感的文字下,除了備受論者稱道的冷靜清明之外,這幕人間喜劇更多了一份對人性缺陷的同情與寬憫。
作者簡介:
胡晴舫
出生於台灣台北,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戲劇碩士,一九九九年移居香港。專事寫作,包括文化評論、小說與散文,發表於兩岸三地、新加坡等各大中文媒體。 著有《旅人》、《她》、《機械時代》、《濫情者》與《辦公室》等書。
商品資料
- 作者: 胡晴舫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22 ISBN/ISSN:9789573324904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