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喬得獎後第一部作品!
法國熱賣突破30萬冊!
我感覺過飢餓,知道飢餓是怎麼回事,
但我接下來要說的故事,講的是另一種飢餓……
這是光燦奪目的爵士年代,歌舞昇平的花都巴黎,布杭家族的獨生女艾蝶兒在鍾愛她的舅公照拂下,在週日沙龍的衣香鬢影中寂寞地成長。
這也是山雨欲來的大戰前夕,艾蝶兒與舊俄貴族之女榭妮亞、失怙的英國青年羅宏,在人生路口找到了彼此,一起對抗著紙醉金迷表象下的虛無暗流。
這時,艾蝶兒的舅公過世了,他將遺產以及與艾蝶兒一同設計的「紫房屋」重建計畫留給了她。但在戰爭的陰影下,這只是家族崩裂的第一個徵兆,而蟄伏體內的飢餓本能也讓艾蝶兒發現,她第一次有機會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勒‧克萊喬在榮獲諾貝爾獎後的第一部作品中,回歸家族記憶,以母親在二次大戰前後的成長經歷,寫下這部《飢餓間奏曲》。他以冷靜的語調,用爵士年代的璀燦風華反襯戰禍將至的沉重氛圍,寫出在無聲處聽見驚雷的震撼,也帶出這段不同凡響的戰爭回憶與家族故事。
作者簡介:
勒.克萊喬 J. M. G. Le Clézio
一九四O年出生於法國尼斯。二十三歲時,即以第一部小說《筆錄》榮獲法國四大文學獎之一的「賀那多獎」。一九八O年,再以《沙漠》一書獲頒法蘭西學院「保羅˙莫杭大獎」。一九九四年,法國《閱讀》雜誌舉辦讀者票選「最喜愛的作家」,克萊喬榮膺榜首。一九九八年,他又獲頒「摩納哥皮耶王子文學獎」,以表彰他在文壇上卓越的創作成就。二○○八年,克萊喬更進一步榮獲文壇最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文學之路攀上顛峰。《飢餓間奏曲》為克萊喬得獎後的最新力作,旨在紀念母親度過的戰爭年代。
克萊喬的作品多以漂泊不定的邊緣人物為主角,這些人物的存在,以一連串的遷徙建構起來,漂泊則是他們自由的標記。他的作品也常反映出他對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化的關注,他認為這些原始文明遠比建立在理智上的歐洲文明來得強烈、熱情,對世界也有更為感官性、直覺性的認知。為此,他在文字的運用上,也以激發讀者的感官為主,表現出「小說的本質不在於呈現重建過的真實感,它有點像舞蹈……能讓一旁觀舞的人覺得『腳癢』」。
他另著有《金魚》、《偶遇》、《奧尼查市》、《漂泊的星》等作品。
譯者簡介:
尉遲秀
一九六八年生於台北。曾任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文學線主編、輔大翻譯學研究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現專事翻譯。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雅克和他的主人》、《小說的藝術》、《無知》、《不朽》、《緩慢》、《生活在他方》、《相遇》、《戀酒事典》、《渴望之書》(合譯)等書。
章節試閱
我知道飢餓是怎麼回事,我感覺過飢餓。小時候,大戰結束,我跟著一群人在路上,追在美國人的卡車旁邊跑,我伸長了手去抓美國大兵使勁扔出來的口香糖、巧克力、麵包。小時候,我對肥肉如此飢渴,甚至會去喝沙丁魚罐頭的油,我快樂地舔著祖母為了讓我變壯而餵我魚肝油用的湯匙。我對鹽巴如此渴求,甚至會去廚房,從鹽罐裡挖出滿手的灰鹽來吃。
小時候,第一次嚐到白麵包。不是麵包師傅做的那種圓形大麵包──顏色介於灰褐之間,用變質的麵粉摻上木屑做成的,我三歲的時候差點因此送命。我吃到的白麵包是方的,高筋麵粉套模子做的,很輕,很香,麵包心跟我寫字的紙一樣白。在紙上寫字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嘴裡都是水,彷彿時光並未逝去,我和我的兒時直接連起來了。這片麵包入口即化,化作雲,我才塞進嘴裡就吵著要另一片了,還要,還要,如果祖母沒把麵包收進櫥子裡鎖起來,我可以一下子吃光,吃到不舒服為止。或許,沒有什麼比這更讓我滿足的了,從此我不曾吃過如此飽足我的飢餓、讓我如此滿足的東西。
我吃美國的Spam牌餐肉罐頭。許久以後,我還留著那些用一把小鑰匙捲開的金屬罐頭,我拿它們做成戰艦,還小心翼翼地塗上灰色油漆。罐頭裡的粉紅肉糜,邊上鑲著一圈透明肉凍,帶著點肥皂味,讓我充滿幸福的感覺。新鮮的肉味,餐肉在我舌上留下一層薄膜般的脂肪,覆在我喉嚨的深處。後來,對其他人來說,對那些不曾體會過飢餓的人來說,這種肉糜應該是恐怖的同義詞,是窮人食品的同義詞。二十五年後,我和餐肉重逢,在墨西哥,在貝里斯,在切圖馬爾、菲力佩-卡里約港、橘道鎮的商店裡。這種肉糜在那裡叫做carne del diablo,魔鬼的肉。同樣的Spam牌餐肉裝在藍色罐頭裡,包裝上的圖樣是切片的餐肉鋪在一葉生菜上。
三花牌奶粉也是。應該是在紅十字會的中心分發的物資吧,圓柱型的大罐鐵罐,畫著三朵胭脂色的康乃馨。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對我來說,這就是溫柔,溫柔與豐盛。我挖出一大匙一大匙的白色粉末,舔著,幾乎喘不過氣。同樣地,我可以說這是幸福。從此,沒有任何奶油、任何蛋糕、任何甜點,可以讓我得到更幸福的感覺。溫熱,密實,幾乎有一種淡淡的鹹味,我的牙齒和牙齦嘎吱著,我的喉嚨流淌著濃濃的液體。
這飢餓在我體內。我無法忘記。它散發著某種銳利的光,讓我忘不了我的童年。少了這飢餓,我的記憶恐怕留不住這段時光,如此漫長的歲月,一無所有的年代。幸福,是毋需憶起的。我不幸福嗎?我不知道。只是我會想起,有一天醒來,終於可以因為感到飽足而發出讚歎。這麵包太白、太柔軟、聞起來太香了,這浸漬沙丁魚的油流過我的喉頭,這一粒粒灰鹽的結晶,這一匙匙奶粉在我的嘴裡、在我的舌上,黏成一團糊,這是我生命開始的時刻。我走出灰暗的年代,走入光明。我自由。我存在。
接下來的故事,講的是另一種飢餓。
紫房屋
艾蝶兒。她在公園的入口。天黑了。光是柔和的,珍珠色。或許塞納河上有一陣轟隆隆的暴雨。她緊緊握著索里曼先生的手。她才剛滿十歲,個子還很小,頭才剛過她舅公的腰。矗立在他們眼前的,彷彿一座城市,建在梵生森林的樹叢當中,看得到塔樓、清真寺的尖塔、圓頂。四周的大街上擠滿了人。
這是個神奇的地方。艾蝶兒從未見過,也不曾夢見這樣的地方。他們走過入口,來到庇克僕斯門,他們沿著博物館的建築物走,博物館前人頭湧湧,索里曼先生不為所動。「有些博物館,妳什麼時候都可以來看。」他說。索里曼先生的腦子裡早有定見。他就是為了這個才帶艾蝶兒來的。
他們牽著手一直走到湖邊。在灰色的天空下,湖看起來很大,彎彎曲曲的,跟沼澤沒有兩樣。索里曼先生經常說起他從前看過的湖和澇窪地,在非洲,那時他在法屬剛果當軍醫。艾蝶兒喜歡讓他說話。索里曼先生的故事只說給艾蝶兒聽。艾蝶兒所知的一切世事,都是索里曼先生說給她聽的。湖上,艾蝶兒看見幾隻鴨子,還有一隻帶著點黃色的天鵝,似乎日子過得很無聊。牠們從一座小島的前方游過,這島上蓋了一座希臘神廟。人們擠著要走過木橋,索里曼先生問道(不過顯然是為了不讓良心不安才問的):「妳想要……?」人實在太多了,艾蝶兒拉著舅公的手。「不要,不要,我們立刻就去印度!」他們沿著湖邊走,逆著人群。這個高大的男人穿著軍裝大衣,戴著過時的帽子,這個金髮小女孩盛裝打扮,穿著花邊皺褶洋裝和短靴,人們走到他們面前就會自動散開。艾蝶兒跟索里曼先生在一起的時候很自豪,她覺得她身邊是一個巨人,一個無論世界如何混亂都可以打開一條路的人。
一旁,有條小徑離湖岸而去,走在上頭的人比較少。那裡有一塊告示牌寫著:舊•殖•民•地。這幾個字的下面是一些地名,艾蝶兒慢慢念了出來:
留尼旺
瓜地洛普
馬提尼克
索馬利亞
新喀里多尼亞
圭亞那
法屬印度
索里曼先生想去的就是這裡。他到了屋子前面,紅通通的臉露出無比的滿足。他不發一語,握著艾蝶兒的手,兩人一起爬上木梯,通往屋前的臺階。這是一棟非常簡單的房屋,淡色的木頭蓋的,四周都是有柱子的迴廊。窗戶很高,崁著暗色木頭雕成的阿拉伯窗片。屋頂幾乎是平的,鋪的是上釉的瓦片,上頭突出一座有雉堞的小塔樓。他們走進去的時候,屋裡一個人也沒有。房屋的中間是個內院,塔樓的燈光照亮這裡,整個內院浸潤在某種奇異的淡紫色的光裡。內院側邊,有個圓形的水池映著天空。水如此平靜,有那麼一瞬間,艾蝶兒甚至以為那是一面鏡子。她停下腳步,心跳個不停,索里曼先生也站著不動,頭微微往後傾,望著內院上方的穹頂。正八角形的壁龕裡,燈管散發出一種很輕的顏色,很不真實,宛如一陣煙,那是紫陽花的顏色,是海上黃昏的顏色。
索里曼先生沒動。他在內院中央動也沒動,他站在光亮的圓頂下,燈的微光把他的臉染成淡紫色,他的頰髯是兩道藍色的火燄。現在,艾蝶兒明白了:讓她顫抖的是舅公的激動。要讓一個這麼高大、這麼強壯的人定住不動,這棟房屋裡一定有個祕密,一個奇妙又危險又脆弱的祕密,只要稍微動一下,一切就會停止。
這會兒索里曼先生說話的樣子,彷彿這一切都屬於他。
「那裡,我要擺我的書桌,那裡擺兩個書櫥……那裡是小鋼琴,最裡面要放那些非洲的黑木雕像,打上燈光以後,它們就像待在自己的家了,我也終於可以打開那塊柏柏爾人的大地毯了……」
「這裡,我要放那張舊搖椅,就像在老家的迴廊下,下雨的時候,我會看著雨滴敲打水池裡的水。巴黎經常下雨……然後我要養一些蟾蜍,好聽牠們預告下雨的叫聲……」
「蟾蜍都吃什麼啊?」
「牠們吃一些小蒼蠅、飛蛾、蛀蟲。巴黎有很多蛀蟲……」
「也要種一些植物才行,會開淡紫色花的那種扁扁的植物。」
「對啊,蓮花。應該種睡蓮,蓮花在冬天會枯萎。可是我們不要種在圓形的水池裡。我會有另一個養蟾蜍的水池,在花園的最裡面。那個像鏡子的水池,我要讓它跟盤子一樣光滑,這樣才看得見天空。」
索里曼先生固執的想法,只有艾蝶兒懂。當他看到博覽會的規劃,立刻就選上了印度館,把它買了下來。他的土地不要蓋大樓,他的任何一棵樹都不准別人碰。他雇人種了泡桐、木防己、印度月桂。萬事齊備,就為了他瘋狂的念頭。
在她參觀博覽會之後沒多久。法屬印度館拆下來的建材和配件開始堆積在阿賀摩希克街的花園。為了防雨,索里曼先生用一大塊又黑又醜的篷布蓋在這些材料的上頭。後來,他帶艾蝶兒走到花園外頭的柵欄邊。他打開門上的掛鎖,艾蝶兒看到那一堆堆黑色的東西在花園深處的地上閃閃發亮,她看得楞在那兒,動也不動。
「妳知道這是什麼嗎?」索里曼先生故意逗她。
「是那棟『紫房屋』。」
他讚賞地看著她。
「嗯,沒錯,妳說得對。」他又加上一句:「『紫房屋』,這就是它的名字了,是妳找到這個名字的。」他握住她的手,艾蝶兒彷彿已經看到內院、迴廊,還有那個鏡面小池,映著灰色的天空。「將來這就是妳的,全都是妳的。」
可是他沒再提過這件事。總之,索里曼先生就是這樣。一件事情他只說一次,永遠不再重複。
榭妮亞
艾蝶兒已經不記得她們第一次相遇是在什麼地方了。或許在渥吉哈街的麵包店,也說不定在馬格杭街的女子高中前面。她又看見這條非常灰的街,這是雨天巴黎的灰,這種灰會侵襲一切,會進入一個人的深處甚至讓人落淚。她的父親總是嘲笑巴黎的天空,嘲笑巴黎黯淡的太陽,「像一顆阿斯匹靈。像一塊拿來封信的小麵糰。」
在這片灰色裡,她是一個金黃的小點,是一道光。就她的年紀來說,她的個頭不算高,十二歲吧,或許已經過了。艾蝶兒從來不知道榭妮亞的真實年齡。革命之後,她的母親在逃離俄羅斯的時候生下她。同一年,她的父親死在獄中,或許是被革命分子槍決的。她的母親從聖彼得堡逃往瑞典,然後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直到巴黎。
她跟她說了話。還是榭妮亞先跟她說了話?在一群人當中,在這片灰色當中,艾蝶兒望著她,彷彿這是一個比封信用的小麵糰更真的太陽。她還記得自己的心跳——因為她的美。她天使般的臉,皮膚很明亮,又帶著點暗沉,浸潤在夏末曬成淡棕的膚色裡;她盤在頭頂的金髮,像一根根麥稈籃子的提把,雜著紅色的毛線;她的洋裝是一襲打了皺褶的淺色連衫長裙,樣式簡單,不過胸前還是有一塊紅線刺繡;她的身形如此細小,好像用一隻手就可以圈起來。
這是榭妮亞的眼睛。她從沒見過像她這樣的眼睛。那是一種黯淡的藍,帶著點灰白——石板洗淡的顏色,北邊海洋的顏色,她想——但是令她驚訝的並不是這顏色。她幾乎立刻就注意到的,是這對眼睛給榭妮亞的臉帶來一種脈脈悲傷的神情——或者該說是某種遙遠的目光的感覺,來自歲月深處,滿載著苦難和希望,彷彿這雙眼睛是從一團塵埃裡穿透出來的。當然,她在那個當下並沒有想到這一切。這都是隨著月月年年過去,一點一滴明白的,但是這一天,在細雨綿綿的灰色街道上,返校開學的時節,這個年輕女孩的眼神以一道混沌而暴烈的光,刺進她靈魂的深處,她感到心臟跳得更厲害了。
榭妮亞立刻就注意到她。在學校的操場上,她筆直地向艾蝶兒走來,伸出手說:「我叫做榭妮亞•安東妮娜•查維洛夫。」她說她名字的「榭」的時候,喉頭深處輕輕發出噓氣聲,艾蝶兒一聽就覺得很神奇,她的姓聽起來也是。榭妮亞用一支迷你鉛筆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黑色的小記事本上,她把那一頁撕下來,一邊遞給艾蝶兒一邊說:「對不起,我沒有名片。」異國的名字、黑色的小記事本、名片,對艾蝶兒來說,太多了,艾蝶兒握住她的手說:「我想做妳的朋友。」榭妮亞露出微笑,但她的藍眼睛還是蒙著神祕的紗。「當然好,我也想做妳的朋友。」榭妮亞的手又小又柔軟,是孩子的手,艾蝶兒感到這隻手在她的手裡,心裡一陣激動,像是某種友誼的承諾,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擊垮這份情誼。後來,她憶起這最初的瞬間,憶起她的心跳。她想:「終於,我找到了一個朋友。」在黑色的小記事本上,艾蝶兒寫下她的名字和地址,像在簽署一項莊嚴的協約。不知為何,或許為了讓榭妮亞另眼相看,為了確定自己配得上她的友誼,艾蝶兒扯了一點謊。「我們住在這裡,不過我們不久就要搬家了。等我舅公的房子蓋好,我們全部都會搬去跟他住。」然而此刻,艾蝶兒其實已經知道「紫房屋」在短期之內是不會蓋好了。索里曼先生的健康每下愈況,他的夢想也越來越遠了。
一個秋日的午後,艾蝶兒帶榭妮亞去了花園。在花園的木門前,艾蝶兒把鑰匙拿給榭妮亞看。她的緊張是有感染力的。榭妮亞笑得有些神經質,她抓著艾蝶兒的手。「妳確定可以嗎?」連門鎖都卡住了。艾蝶兒試了好幾次才轉開鎖閂。鑰匙轉動時發出生鏽的吱嘎聲,兩個女孩聽到刺耳的聲音都叫了起來。她們衝了進去,艾蝶兒用鑰匙把門反鎖起來,彷彿有人緊緊跟在後頭要跑進來。「來,我給妳看我們的祕密!」艾蝶兒握著榭妮亞的手。
在阿賀摩希克街的花園裡,這個下午很長,非常長。兩個小女孩度過最初的時刻,檢查完那堆被荊棘侵襲的木板之後,在花園的深處坐了下來,索里曼先生從前在這裡擺了一張長椅,好在上頭舒舒服服地作他的夢。這個秋日的午後濕濕糊糊的,不過黯淡的太陽還是照亮了這塊地最深處的那面石牆。一隻褐色的蜥蜴從牆上鑽了出來,用牠金屬釦子般的閃亮小眼睛觀察兩個女孩。
艾蝶兒從來不曾跟任何人這樣說話。她覺得好像一下子變得更自由了。她笑著,說著一些生活裡的小故事,她想起從小累積起來的很多小細節。她說起一些計畫、一些想法、一套舞會的禮服。她們忘了一切,榭妮亞忘了生活的困頓,忘了她和姊姊的貧窮,忘了她們仰人鼻息的生活。艾蝶兒忘了父母間的爭吵,忘了父親和牟德小姐關係曖昧的閒言閒語,忘了索里曼先生躺在床上,穿得像是就要出門遠行。艾蝶兒聽過女傭伊妲告訴母親,索里曼先生要她每天早上都幫他穿好衣服,繫好鞋帶,因為他知道自己即將死去。
我知道飢餓是怎麼回事,我感覺過飢餓。小時候,大戰結束,我跟著一群人在路上,追在美國人的卡車旁邊跑,我伸長了手去抓美國大兵使勁扔出來的口香糖、巧克力、麵包。小時候,我對肥肉如此飢渴,甚至會去喝沙丁魚罐頭的油,我快樂地舔著祖母為了讓我變壯而餵我魚肝油用的湯匙。我對鹽巴如此渴求,甚至會去廚房,從鹽罐裡挖出滿手的灰鹽來吃。 小時候,第一次嚐到白麵包。不是麵包師傅做的那種圓形大麵包──顏色介於灰褐之間,用變質的麵粉摻上木屑做成的,我三歲的時候差點因此送命。我吃到的白麵包是方的,高筋麵粉套模子做的,很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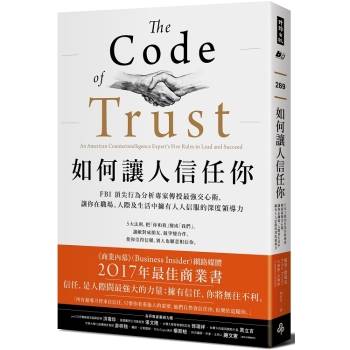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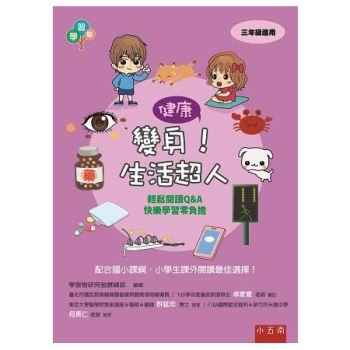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