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完美!《神秘森林》文壇才女更加扣人心弦的驚悚傑作!
據說,每個人都能在世上找到
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榮獲亞馬遜網路書店2008年度「編輯推薦選書」!
●橫掃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舊金山紀事報、美國書商協會、北卡獨立書商協會等各大暢銷排行榜!
那是我的臉、我的名字!
死在林中小屋裡的女孩竟和我是如此地相像,
而她臉上有種用密碼寫成的隱秘訊息,
如同心跳般,唯有我能解讀......
我走在自己失去的生命裡,彷彿一縷幽魂,卻在另一張相似的臉龐上,再次尋回了重生的機會......
自從在上一個案件身心受創之後,凱西黯然離開了重案組,並和同事山姆交往,但卻並沒有走出之前的陰影,而無法全心投入感情與工作。就在此時,山姆接到了新的兇殺案件,一名年輕女子在都柏林市郊的荒廢小屋遭人刺死。
從黑暗中浮現的女孩屍體靠坐在牆壁上,渾身浴血,但最令人震驚的是:死者根本就長得和凱西一模一樣,彷彿凱西的分身!而她身上發現的證件竟然正是凱西當年到販毒幫派臥底時所使用的假身分「蕾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線索,沒有嫌犯,這個「不存在」的死者的過去更完全是一團謎!警方發現蕾西是住在附近山楂林屋的五名研究生之一,五個人平常總是同進同出,完全不與外界往來,連學校和村民都不清楚他們的底細。
凱西的上司法蘭克發現機會千載難逢,便決定謊稱蕾西傷重未死,派凱西假扮成蕾西前往山楂林屋臥底追查真相。多年前和蕾西那段身分交錯的日子,曾經給了凱西一把打開人生枷鎖的珍貴鑰匙,但她卻萬萬沒想到,這個虛假的身分多年後竟以石破天驚的方式又回頭來找上她......
以《神秘森林》令國際文壇為之驚豔的才女作家塔娜.法蘭琪,再次以其如詩般優美的文字,完成了這部心理驚悚的傑作!主角擺盪在「凱西」與「蕾西」、現在與過去、真實與虛構的兩個身分之間,彷彿兩部交替出現的主旋律,彼此又纏繞糾結成一首扣人心弦的賦格曲。全書懸疑的佈局、幽深的氣氛,對照隱晦的真相、駭人的秘密,以及不斷升高的猜忌和背叛,也再次讓我們看得欲罷不能、讚嘆不已!
作者簡介
塔娜.法蘭琪 Tana French
從小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住過愛爾蘭、義大利、美國、馬拉威等地,直至一九九○年才定居都柏林。因為經常搬家,接觸不同文化,使得她的觀察力也遠比一般人敏銳。
她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接受專業演員訓練,並曾參與戲劇、電影、配音等工作,而這些經歷也幫助她能夠成功模擬角色的各種樣態。《神秘森林》雖是她的第一本小說,但她以聰明、細膩、優雅的敘事手法,配合人物心理的精準掌握,讓英國和愛爾蘭的出版社為之驚艷,立即以六位數英鎊的高價搶下版權。
而《神秘森林》出版後也果然贏得全球各地書評的一致讚譽,不僅榮獲「愛倫坡獎」、「安東尼獎」、「麥可維提獎」、「巴瑞獎」等四項「年度最佳處女作」大獎,更躍登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今日美國報、舊金山紀事報、洛杉磯時報、丹佛郵報、波士頓環球報、Book Sense、北卡獨立書商協會等全美九大暢銷排行榜,並入選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編輯推薦選書」。目前已售出超過三十國版權,銷量更已突破五十萬冊!全書優美的文筆、神秘的氣氛,帶領讀者難以自拔地走入這片蒼鬱的謎霧森林中。
而繼《神秘森林》獲得無數讚譽之後,塔娜.法蘭琪又再推出《神秘森林》二部曲新書《神秘化身》,同樣席捲國際文壇,並再次入選亞馬遜網路書店二○○八年度編輯推薦選書,也使得塔娜.法蘭琪成為當前最受矚目的文壇新銳!
譯者簡介
穆卓芸
文字手工業者,譯有《神秘森林》、《尋找松露的人》、《重擔》、《藍眼菊兒》、等書,現居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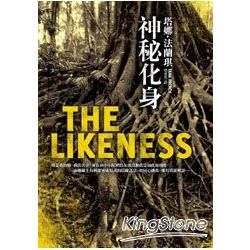
 2011/09/17
2011/09/17 2011/01/05
201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