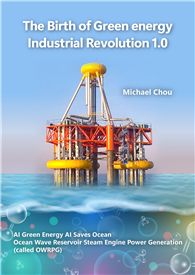第五大道其實是一條頗沉悶的街道,它被刻意妝點渲染,反而營造出一種形而上的氣氛,顯得如此虛幻,它像幻想,理想,像千百年前的古代,千百年後的未來,總之,是我無法擁抱的,那種無法擁抱的空落的感覺,使我走在其間只感到渺茫。那天遇到蘇真,是在這樣虛浮的氛圍裡。我從廣場旅館過街,經過一排列隊等待遊客光顧的馬車,進入中央公園。
公園坐落在赫赫有名的第五大道跟百老匯大道之間,兩邊林立的高樓,過去跟現代交錯完美的建築,使整座公園平添一股恢弘氣勢。曾經聽說過,在紐約如果想要旅遊,又沒有錢旅遊,那就到中央公園走一圈。
我循著公園裡的彎路走,滿是紅葉黃葉的樹林裡,有人帶著孩子在野餐,有更多的人橫躺在開闊的草皮上做日光浴,九月秋涼的天,還是不少人光膀子穿比基尼躺在那裡。一個大男孩在跑馬道上騎著駿馬,經過一棵很漂亮的銀杏樹,那馬忽然不安地停下來,馬蹄蹬了幾下,遺下一堆不整齊的馬糞。我快速轉向另一條彎路,到一把長椅上坐下。
我在一家中文報社裡任編輯,十二年了,每天替一批又一批似是而非的報導下標題,乏善可陳得使我不由得也要思索,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裡?我腳跟前這時過來一個人,抬頭望去,是個細長身形的東方女人,四十出頭吧,穿一身彩色鮮豔鑲亮片的印度服裝,裙長蓋膝,裡面穿黑色的緊身七分長褲。短髮上紮一條咖啡色滾粉藍邊的頭巾,臉上顴骨突出,膚色在東方人裡,也算是深的,好像曬過很多太陽,甚至有點灼傷,是那種重筆勾出的輪廓,之後,再著深色,那種個性很強,絕不被掌控,甚至,你有可能被她掌控的臉。
我們四目交接,幾秒鐘的相互打量,她先開口,試探地用中文,「我昨天在記者會裡是不是見過妳?那個講英文的記者會?」
我一聽,略微失望地應,「我沒去過記者會。」
「我是慕尼黑一個商務考察團的隨團記者,昨天有個記者會,這是我的名片。」
我接過名片,沒有多瞄一眼,直接放進大背包裡,問她,「商業考察團,那種報導也值得從慕尼黑跟到紐約來寫嗎?」
她無所謂地一笑,坐到我身邊,「只是藉口出來玩嘛,咦,地上有一個quarter,為什麼不撿起來?」她說起話來,甚至她渾身的氣息,顯得輕飄脆弱,這給我莫名的好感。
可我還是沉靜的,循著她的視線望過去,果然有個兩毛五分的硬幣掉在地上 ,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這還要彎腰才撿得到,彎個腰只值兩毛五嗎?」我開著玩笑。
「那我多添錢讓妳撿?」她興致勃勃地扭頭爭取我的意見。
我有點惱怒,但,沒有反應。
「真的,我銀行裡有十萬塊。」她認真地說。
「妳怎麼逢人就奉告這些?」我站起來走開。她卻跟在後面,這就是蘇真,老是有點出格的蘇真,後來跟我的生活糾纏在一起的蘇真。
她笑嘻嘻跟到我旁邊說,「我在紐約找不到失散的老朋友,正發悶呢。」
我回過臉看她,轉而好奇地問,「多久以前的老朋友?」
「十七年,太久了吧。一個也找不到了。」
我們不知不覺走出中央公園,又到了第五大道上,這次是到了七十二街的出口,「 乾脆再走一段,去博物館吧,既然已經到了這裡。」我向她這位觀光客建議。我們沿著中央公園旁邊,一排黃葉鋪蓋的林蔭道,林蔭下一個接一個的畫攤,如此,順著第五大道走下去,她在路上告訴我,她是台灣一家大報駐在德國的特約記者,在家裡還收了幾個學生,教他們彈鋼琴。「妳呢?妳是做什麼的?」我猶豫了一下,「我正改行要寫小說。」話一出口,立刻先把自己嚇一跳,她倒很自然地聽著,好像我說的是一個公司的打字員。到了大都會博物館,我們都有點累了,就在它前面的噴水池裡掬水泡手,涼快了一下。我一向喜歡噴泉,當然,最好是瀑布。我在日內瓦見他們把幾柱噴泉當景點,做為城市的標記,這實在太小兒科了。除了羅馬之外,噴泉只能算一點小小的個人的喜樂,怎能做為一個大地方的指標?當風水來用,還比較合適吧?如果一方的人,命裡都缺水,就在那地方多設幾座噴泉。總之,走過二十幾條街,我們都累了,便在博物館前面,一排一排的石階上坐下休息,「我發現妳滿能走路的。」我笑著呼出一口氣。
「我正要說妳呢。」
我們望著彼此腳上的大球鞋笑一陣,我發覺她的笑容很像過年穿大花棉襖的鄉下大姑娘,看起來非常憨厚,跟她自己重筆畫出的濃眉有種討喜的搭襯,很像小學生畫的「我的媽媽」、「我的姊姊」。我發覺我可以不斷地,在她臉上身上,發現各種怪怪的組合。
「我喜歡旅遊,喜歡一點不間斷的旅遊,我希望有一天,從這一點飛到那一點的時候,死在半路上。」
「那好像沒有終點嗎?我也對終點沒有興趣,可是,那也還是一個終點啊。」我忽然難過起來。
「我有癌症,剛照完鈷六十,妳沒看我膚色有點黑?這是我第四次一照完鈷六十就跑出來玩。」
我暗吃一驚,我所受到的驚嚇,大得好像被一顆炸彈炸到,只是,我向來是一個不錯的演員,如果曾經有過機會,我會去當一個演員,只是命運使然,使我只能在這種小舞台上表演。我裝得若無其事,「哪一種癌?」好像每人都有一種癌似的。
「最早是乳癌,後來跑到淋巴,有了淋巴癌,再後來跑到子宮和卵巢,有了子宮癌卵巢癌,現在又跑到骨頭,有了骨癌。」蘇真笑容滿滿的,好像遇到好對手,也提升了自己的演技。
「哇,跑那麼快!我們剛才走那麼多路,都沒有癌細胞跑得快。」
蘇真一下咕咕笑出來,伸出一隻腳讓我看腳踝上凸出的兩顆硬塊,「這是淋巴癌長的。每次我的醫生都說我活不過三個月。妳知道,玩這一趟回去,我馬上又要回醫院照鈷六十,同時也接受順勢療法。」
「妳一定要這樣跑出來玩?」我問。
「一定要。」
「妳真的這麼喜歡旅行?」
「旅行使我忘掉一切,使我變得不是一個妻子,女兒或母親,我誰也不是,我只是一個無根,甚至無思想的隨便什麼物體。」她說著,一下坐直起來,「我們現在這種對話,很像在接受順勢療法。妳是醫生,妳要在千百種藥材裡面,找出適合我的,只適合我一個人的藥,順勢療法的藥很小一顆喔,這麼小……」蘇真抓一根髮絲比劃著,「切斷一點,像一小點微粒,白色的很小的微粒,可是,只要找對了,它的藥效是大得可以把一個人身上所有的病痛一起解除。」
我聽得一陣顫慄,「會立刻死掉嗎?」
「胡說!」她狠狠瞪我一眼,「會把人醫好的。」
「對不起,」我不禁唏噓,轉而一想,「啊,我曉得了!所以不論妳的癌細胞跑到哪裡,妳都不怕。順勢療法會把妳醫好。」
「可以這麼說,不過,一切的一切都有局限性,順勢療法也一樣。」蘇真說,「我不是告訴妳,醫生每一次都說我活不過三個月?」
「醫生就這樣告訴妳?」
「是啊,我先生也一樣,他每次都說我快要死了,他也是醫生。他還告訴我他去找妓女。他本來不要找妓女的,他喜歡漂亮又有才氣的女人,他已經找了兩三年,還沒有找到。」蘇真說。
「我很想把我的故事寫成小說,可是整理不出來。」蘇真說,「我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要寫多少字?寫成一個短篇吧……反正,我寫不出來。」
「寫小說很需要體力,我來替妳寫吧。」我邊說邊思索。
「好啊,妳寫!」她爽快地說,如此爽快,我卻猶豫起來。
「妳讓我想一想。」想一想,蘇真一股腦告訴我這些,必定因為在她眼裡,我是一個跟她投緣的陌生人,我們相互感到面善,卻過了今天再也不會有明天,我們之能相互吸引,很大部分原因就是過了今天,再也不會有明天。她並不認為我真的會寫她的故事,也並不真要我寫她的故事。她只是把壓積在心裡面的話說出來,然而,卻跟沒有說出去一樣。我們之於彼此,純粹是旅遊中的一道風景,再好的風景也不過,一照面就要告別。可是,我忽然真的想寫她,因為她眉梢眼角間,透露的一點什麼?因為她如此真心的,把她內心最柔軟的部分整個暴露出來?因為她鼻跟唇間人中的地方,短短的,長得特別憨,特別嬌脆的模樣?因為她每天活在只能活三個月的焦灼恐懼裡?因為,到底是什麼古傳或新方的順勢療法在支撐她……我這般苦苦搜尋,為什麼要寫她的同時,竟使我著魔似的,越發堅定起必定要寫她的決心。
「我來替妳寫,只是,得癌症不算好題材。」我皺著眉衡量,「妳先生很可惡,如果把重點放在男人跟女人的戰爭……不行,這樣寫我也不喜歡,好膩味。要怎麼寫呢?妳什麼時候離開紐約?」
「後天。」蘇真說,忙不迭又補上一句,「男人跟女人的戰爭可以呀,我先生恨我不聽話,我只能捱罵不能還嘴。」蘇真一句接一句地說,「還嘴的話,他會拿刀子作勢要殺我。他嫉妒我比他聰明,他要我什麼都聽他的。」
我又是暗吃一驚,卻只是搖頭,「我就是不喜歡這種題材……把主題放在哪裡?這個讓我慢慢想吧。」轉而又故作輕鬆地說,「我很會想的,我有時候想到一隻蛤蟆從我的飯碗裡跳出來……不對,這不是瑞典那個大導演想過的?」
蘇真笑一聲,「不管怎麼,這篇小說就由妳寫。」
「我明天晚上把第一章給妳看。我等一下回去就開始寫。」蘇真聽我說得好像沖一杯咖啡一樣容易,不免疑惑地看我,我因此再強調,「我常常幻想我在寫小說,寫那種會讓人目眩神迷的小說,少說也寫過十幾本了。」
我說得陶醉起來,更認真地接著問,「妳希望故事寫得哀怨一點,或中性一點?」「反正是小說,就隨妳寫了。」蘇真又不放心地說,「我先生一說到我要死了,有時候也對著我哭,這一點妳不要忘了一起寫進去。」
「啊。」我低應一聲。在一次又一次的心驚之餘,這次,我感覺到應該被擊中要害,所謂人性的弱點了。可我只是埋頭從大背包裡掏出紙筆,一邊念一邊寫,「第一,關於妳接受順勢療法,第二,醫生說妳剩三個月,第三,妳先生敏感到自己不如妳聰明,特別要妳什麼都聽他的,不聽他的,他就會動刀殺妳,聽他的,他也會掉眼淚。是這樣吧?」
蘇真笑出來,「我有一種預感,我知道交給妳寫就對了。」
「可是我不喜歡悲劇。」我咕噥著,「妳一點不像病人,妳沒有掉頭髮呀,聽說應該掉頭髮的……可不可以把悲劇寫得像喜劇?」我胡亂說著,又動搖起來,「不行,不行,像喜劇的悲劇?那不是……那要絕頂高手才寫得出來,我不能自不量力。」
我沒有繼續說下去,默默地收好紙筆,內心裡卻一點一點的越發沉重起來。
蘇真這時解釋,「我沒有做化療,做化療才會掉頭髮。」接著雙手合十企盼地說,「我也比較喜歡喜劇,如果是喜劇就好了,上帝啊給我一個喜劇的結局吧。」忽又反過來問,「給妳這麼一點材料,妳就要回家燒大菜呀?」
我想了一下,微笑地回應她,「妳給的比一點還多,我要寫的也比一盤大菜還大。我現在是有了一條繩索,只差一條船了。」我回報她的幽默。
那天下午,我開始坐到電腦前噠噠噠地敲打,敲打,敲打……我感覺自己好像古代的鐵匠,敲敲打打正在鑄劍。不對,我並不想鑄造出什麼削鐵如泥的寶劍,我只是不斷在敲打,像要敲碎什麼地敲打,敲打。我亢奮地努力敲打著,直到我先生下班回家,這才匆匆燒好兩人的晚飯, 他卻對著桌上的飯菜,懨懨地咕噥,「又吃這樣簡陋的飯菜,我要出去吃木須肉,妳要不要一起去?」先生問。
「這是健康食品啊,」我多少有點違心地說,因為,還不是為了燒起來省事?「這樣吧,你這份乾煎有機雞胸肉給阿毛吃,你出去吃whatever you want。」
阿毛是我們家的老狗,去年開始就不會叫了,今年是狗年,阿毛沒法「汪!汪!」再喊叫兩聲,十分可惜,可我一點也不怪牠。阿毛老了,牠在家裡包著尿布,老得快要走不動了,食量也大不如前。牠原來可以舔得乾乾淨淨的雞胸肉,這時吃得七零八落碎屑四散。我不能不關心牠。「阿毛,走,我們出去散步。」兩年前,我出差兼旅遊一個月回來,發現阿毛竟衰老得不能動彈,情急之下硬拉著牠出去走,牠腿軟軟地走了幾步之後,慢慢硬朗起來,這使我更堅信「生命始於運動」。阿毛因為每天散步一個鐘頭,又活過來了。我猛然想到蘇真說,這是她第四次一照完鈷六十就跑出來玩。因為她到處趴趴走不停在運動,她還以為是鈷六十跟順勢療法一次又一次地救了她,其實只因為運動。我帶著阿毛走在沒什麼鄰居,多半是樹林和沼澤的小路上,我總是挑這條路走,因為不喜歡鄰居藏在窗簾後面說,「那個中國女人又帶她的老狗出來了。」
阿毛這兩個月明顯地走得很慢,我們走過沼澤的時候,牠看到野鴨也無動於衷,換上從前,那還得了,早就像箭一樣從我手中射出去,狗鏈哪裡拴得住牠?可牠現在只是埋頭拖著腳步走,醫生說牠已經看不見了,我曾動過給阿毛開刀的念頭,可阿毛是因為老才看不見,醫生可能治病,卻不可能治老。我憐惜地牽著牠,發誓做阿毛的眼睛。「看到嗎?阿毛,你的小朋友在那裡。」我蹲下去摟著阿毛,指給牠看小水灘上,一群還在撒歡的野鴨,牠們好像玩倦了,這時一起凌空飛起來,嘴裡發出像幼兒嚎叫的聲音,成群飛向遠方越發濃厚的暮色裡。我們往回頭路走,我牽著阿毛恍恍地向前走著時,心裡總浮動著正在寫的小說,我想回去把第一段改寫。
第二天,我整天敲打著,打鐵趁熱,在最有可塑性的第一時間裡,我加倍敲打著。到了晚上,我準時赴約,把幾頁打字紙交給蘇真。「放到桌上吧。」蘇真的聲音細得像蚊子,走路也輕悄得像蜻蜓點過水面,我不能說她跟昨天判若兩人,但她穿一身白色緊身內衣的樣子,的確前心貼後背的瘦得像一張白紙,好像所有的精力都在昨天揮霍光了。她走幾步過來替我開門,這已經使她累得靠到床頭不停喘氣,「我躺了一天,哪裡也沒去,我身上好痛。」
我頓時說不出話,看她的身體慢慢下滑,滑入被窩裡。我一言不發陪在旁邊,直到她睡熟才站起來,把桌上的稿紙丟進垃圾桶,悄悄關上門回家。回家後重新敲打,我換過另一種格式,還是平鋪直敘從頭道來吧,我敲完第一章的時候,接到蘇真從旅館打來的電話,「我剛剛醒來,把稿紙撿起來了,為什麼要丟掉?寫得很迷人。」
此後,我們失去聯絡,我的小說,也在我每天為阿毛清洗糞便的瑣碎工作裡中斷。再聯絡上蘇真是一個月後,她說,回慕尼黑的次日,就住進醫院檢查,她脊椎骨斷了,聲帶也癱瘓,連做了四個星期的復健,再加上不斷的順勢療法,又奇蹟似的活過來。又是什麼奇妙的順勢療法?我於是把已經打好的小半部再潤色過,傳給她,然後等她的回音。蘇真斷斷續續地回訊,卻總也不提小說。
時序已進入二○○六年的尾聲,我每天所能向蘇真報告的,就是阿毛的老況,明年三月六日阿毛將滿十六歲,雖說小狗的壽命是十五年,可是在我悉心照顧下,阿毛至少應該活到二十歲!一定要二十歲!
十一月底的一個中午,天色有點陰,我一整天還沒帶阿毛出去運動,這時趕忙帶阿毛出門,恐怕就要起風下雨了,果然才接近樹林,雨滴已經大點大點地落下來,阿毛實在走得太慢,我拉牠回頭,半空裡雷電交加,今年氣候特別,才會在十一月裡出現雷雨。「阿毛,快,快走!」阿毛一聞雷電就會全身發抖,「快走!別怕!快走!」動物的本能,使阿毛逃命似的加緊步伐,可牠還是跑不動,雨傾盆而下,我忙抱起阿毛,把牠裹進我的夾克裡,朝家的方向狂奔。我全身溼透,連球鞋都進水。口袋裡的手機也泡湯不能用了。阿毛沒有淋溼,舒適溫暖的縮在我懷裡。
蘇真給我的伊媚兒說,「我寧願做妳的狗,不要做他的太太。他每天罵我,我從不罵他。」
這使我淚盈於睫。我雖然已經兩三個月沒有繼續在電腦前敲打,可是至少已經陪蘇真度過不只十年的人生。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無法超越的浪漫的圖書 |
 |
無法超越的浪漫 作者:陳漱意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1-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小說 |
$ 225 |
愛情小說 |
$ 225 |
現代散文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無法超越的浪漫
她愛他如此全心全意地寵愛她,
但她也恨他幾近瘋狂地占有她。
在婚姻的束縛與疾病的牢籠中,
她要如何超越所有的疼痛與不幸,
甚至,超越死亡……
在病魔無情的摧殘下,日漸虛弱的身體,
要有怎樣堅強的靈魂,才能勇敢地愛恨?
蘇真,一名到紐約留學的台灣女孩、一個德國醫生的妻子、一位罹患多種癌症卻不肯投降的女人。
曾經,她天真地以為婚姻是永恆的港灣,與丈夫度過無憂無慮的日子,那種親密伴侶之間毫無芥蒂的純淨和快樂,卻在丈夫幾近瘋狂的占有與剝削中,一點一滴地消失殆盡。
曾經,她真實地感受生命的壯闊,總是有無窮精力去做想做的事,她是如此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然而,當癌細胞快速蔓延,那些美好的想望,也隨著生命的萎縮而不復存在……
擅長刻劃女性與婚姻的旅美作家陳漱意,根據真人實事改編,用哀而不傷的細膩筆調,娓娓道出一則殘酷的愛情童話。帶領我們與天真浪漫的女主角一起心動,為她進退兩難的艱難處境心痛,也為她抵抗現實的堅強意志而心疼不已;更從故事的背後,發現了一份相知相惜、至情至性的珍貴友誼!
作者簡介:
陳漱意
生長於台灣,六○年代赴美, 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藝術系,其後一直協助夫婿經營房地產至今。曾任圖案設計員,和紐約《中國時報》、《中報》、《華僑日報》、《自由時報》等各華文報紙的記者和編輯,也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的永久會員。
陳漱意很懷念她的出生地,台南縣新營鎮太子宮太北里,和後來生活過的屏東市、台北西門町。但是,將來不想要葉落歸根到那裡。她的家在紐約市哈德遜河畔的小鎮,有不少老樹林,冬天出名的霧大。
《無法超越的浪漫》是陳漱意最後的長篇,是她為摯友張筱雲所寫。在張筱雲短暫的生命裡,充滿年輕的見血見肉,刻骨般疼痛的愛恨,但她始終熱愛工作、熱愛生命,陳漱意希望她藉著這本書永遠活下去。
章節試閱
第五大道其實是一條頗沉悶的街道,它被刻意妝點渲染,反而營造出一種形而上的氣氛,顯得如此虛幻,它像幻想,理想,像千百年前的古代,千百年後的未來,總之,是我無法擁抱的,那種無法擁抱的空落的感覺,使我走在其間只感到渺茫。那天遇到蘇真,是在這樣虛浮的氛圍裡。我從廣場旅館過街,經過一排列隊等待遊客光顧的馬車,進入中央公園。公園坐落在赫赫有名的第五大道跟百老匯大道之間,兩邊林立的高樓,過去跟現代交錯完美的建築,使整座公園平添一股恢弘氣勢。曾經聽說過,在紐約如果想要旅遊,又沒有錢旅遊,那就到中央公園走一圈。我...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漱意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1-18 ISBN/ISSN:9789573326014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