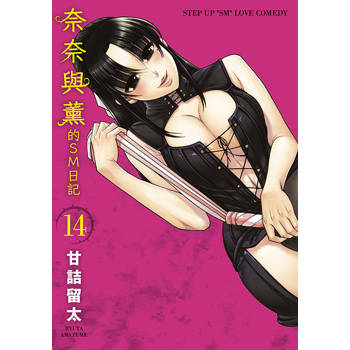義大利暢銷突破250,000冊!
法國亞馬遜網路書店5顆星完美評價!
有一股迷失的力量,從遠方回到我身上。
那個我多年來一直忍受,卻無法掌握的破碎世界,
已在那截道路上重新拼湊起來……
「這就是我天生的使命!」
我決定不告而別,離開憤世嫉俗的伊莉莎白,倒不是因為她一天到晚都說要「腐化這個世界」,而是在殘酷的世界上,在漫長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去做。
沒錯,只能由「我」來做。
我要去尋找一個寬闊的所在,完成七歲那年就已深植於腦海的夢想藍圖──一條不停轉彎的賽車道,封閉的,不通往任何地方,也不會在任何地方結束。
唯有如此,我才能確定,我,真的,活在這個世界上。
宛如樂曲節奏的行文字句、電影運鏡的敘事結構,當代最具創意的文學大師巴瑞科用這個故事,回溯那個開始加速的時代,帶給我們比鮮血更熱燙的想像、比故事更曲折的現實!
作者簡介:
亞歷山卓‧巴瑞科 Alessandro Baricco
一九五八年生於義大利杜林。他是當前義大利最受矚目的小說家,在全世界均擁有廣大的忠實讀者。他也是歐洲各項重要文學獎的常勝軍:《憤怒的城堡》是他的第一部小說,一出版即贏得法國文壇四大文學獎之一的「麥迪西獎」以及義大利威尼斯的「坎皮利歐文學獎」;《海洋,海》則榮獲義大利「維多雷久文學獎」和「波斯克城堡文學獎」。《絹》一出版更立刻登上義大利暢銷排行榜,熱潮迅即延燒全歐洲,被翻譯成三十種以上語言版本,並被改編拍成電影「異旅情絲」。
他一九九九年的作品《城市》,義大利甫推出便熱賣突破二十萬冊,在歐洲各國也極為暢銷。二○○五年推出的《這個故事》,則入圍同年法國「費米娜小說獎」的最佳外國小說。
巴瑞科每一部作品的題材都不一樣,但皆具有樂曲般的特質,並以舞台劇的形式鋪陳,頗具實驗性。他說:「我偏好以創新的寫法呈現每一部作品,讓讀者的眼睛為之一亮。倘若要我總是以同一種路線寫作,那麼寫作的樂趣將會消失殆盡。」巴瑞科不但享有卓越的文學成就,他同時也從事音樂評論,在義大利並以一個有關歌劇和另一個有關文學的電視節目,獲得極高的聲譽。
譯者簡介:
陳澄和
台大歷史系畢業,義大利Siena大學文學院研究。大半生在平面媒體打滾,以國際財經新聞為主業,業餘譯有多種英文、義大利文譯著。
章節試閱
○老么的童年
雖然他叫老么,其實是第一個孩子。
「最後一個。」他母親才從分娩恢復意識就這麼說。
於是,他從此被喚作老么。
起初,他似乎根本不想知道這些。在他生下來的頭四年,幾乎所有的病都生過了。他們為他施洗了三次:因為神父無法為這樣一個張著眼睛的小不點做臨終塗油禮,所以每次都轉而為他施洗,免得沒做聖禮就空手回去。
「這沒什麼壞處。」
老么每一次都活下來,雖然蒼白、瘦小得有如一片破布,但總是活著。他有顆強壯的心,老爸這麼說。他運氣好,老媽說。
他就這樣活下來,一九○四年十一月他七歲又四個月的時候,父親帶他到牛棚,指著他僅有的財產,也就是牛棚裡的二十六頭法索尼品種乳牛,告訴他先不要跟媽媽提起,但他已準備要永遠擺脫這大堆的牛屎。
他做了個寬闊的手勢,表情相當莊嚴,像是在擁抱整個幽暗、發臭的牛棚,然後一字一字緩緩地說:李貝洛˙帕立修車庫(Libero Parri Garage)。Garage是老么從未聽過的一個法文字,當時他還以為是「飼養」或「乳製品」之類的意思,根本不瞭解箇中涵義。
「我們修理汽車。」父親扼要地說明。
事實上,這還是個新玩意。
「汽車還不存在。」等有一天晚上,在熄著燈的床上,老么的媽媽終於被告知時,她這樣註解。
「這是早晚的問題,汽車已經問世了。」李貝洛•帕立告訴他的妻子,同時把一隻手伸到她的睡袍下。
「寶寶在旁邊。」
「沒問題,他也有事要做,他得學習。」
「寶寶在,手拿出來。」
「喔。」李貝洛•帕立想起來在冬天的時候,為了節省爐火,他們都睡在同一個房間。
他們溫馨地躺了一會,然後他又開口。
「我和老么談過這件事,他也同意。」
「老么?」
「對。」
「老么還是個小孩,他才七歲,二十一公斤重,而且有氣喘病。」
「那有什麼關係,他是個很特別的小孩。」
在生過這麼多病,加上許多難以解釋的事情後,他們都認定老么或許是個不尋常的小孩。
「你難道不能和塔林談談?那還差不多。」
「他不會懂的,他跟別人一樣,腦子裡只有土地,土地和牲畜,他準會把我當作瘋子。」
「也許他是對的。」
「不,他不可能是對的。」
「你怎麼這麼說?」
「因為他是特雷札特人。」
在那個地方,這是個無法爭議的論點。
「那你去跟神父談。」
如果李貝洛•帕立沒有成為無神論者或社會主義信徒,純粹只是因為他沒時間。只要給他幾小時多瞭解一點,他篤定會奉為圭臬。事實上,他痛恨教士。
「還有其他建議嗎?」他問。
「我只是開開玩笑。」
「不,妳不是開玩笑。」
「我發誓我是在開玩笑。」她伸一隻手到丈夫的褲襠裡,他喜歡她這麼做。
「寶寶在。」李貝洛•帕立含糊地說。
「裝成若無其事就好。」她建議說。
她叫佛羅倫斯,父親是法國人,在義大利混了很多年,四處推銷他發明的一款女鞋。平時只是一款普通的鞋子,但需要時可利用一個很實用的連桿裝上或卸掉高鞋跟。好處是一雙鞋可以變成兩雙來用,一雙工作時穿,另一雙晚上穿。至於壞處,按他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有一次他去了佛羅倫斯,從此為之著迷,所以第一個女兒就取這個名字。此外,他在羅馬也度過頗長的時間,隔年出生的長男,便取名羅密歐。接著,他轉而偏向莎士比亞,於是又衍生茱麗葉、里卡迪之類的名字出來。留意人們如何取名是很重要的事,人一直都在謀生活,但死亡與取名字,可能是最真誠不過的事。
佛羅倫斯鑽到被單底下,繼續她的工作,最後用嘴來完成。這種做愛方法在當地稱為法國式,一般認為並不適合妻子做,但她覺得自己做起來可是名正言順。
「我有弄得一團糟嗎?」李貝洛•帕立事後問。
「我不知道,似乎沒有。」
「希望如此。」
不過,反正老么都不會聽到,因為他人雖躺在房間盡頭的床上,腦子裡想的卻是兩個冬季前的某一天,他站在父親旁邊,在通往河邊的路上等候的情景。在大清晨裡,前一晚的結霜在充滿好意的陽光照射下,仍在田野間嘎吱嘎吱地響。老么從家裡帶了一顆蘋果準備要吃,此刻正在外套的袖口上擦拭著。他的爸爸邊抽菸邊哼著曲子。他們從家裡走到通往拉貝樓的岔路口,在那裡等著。
「你要帶他去哪裡?」媽媽問他。
「這是男人之間的事。」李貝洛•帕立回答。老么也沒有發問,因為如果你只有五歲,而你老爸把你帶在身邊,這就夠讓你高興的,不用再多問。所以,他就一直跟在父親後面,邊走邊跳到通往拉貝樓的岔路。父親結實的側影迎著飄蕩的晨霧,頭也不回地大步走在他前面,既不等他,也沒特別留意他是否還在身邊。他望著父親,不曉得這個畫面在他長大後,還會無數次地一再反覆浮現。父親以這種嚴肅,卻又毫不懷疑的態度,教導他如何做個父親:要懂得如何頭也不回地走路。儘管毫不客氣地邁著成人的步伐前進,但腳步要清楚而規律,這樣孩子雖然步履很小,也知道如何緊緊跟著。而且,如果你能做到,還要頭也不回地走:要讓他知道他不會跟丟的,因為兩人走在一起是不需懷疑的命運,是注定的。
○伊莉莎白的日記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
我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開始寫日記。
不是什麼詩意的事,我只是需要記錄我的事情。
就像一個目錄,只為了避免忘記。一個目錄。
我是誰。二十一歲。名字:伊莉莎白。俄羅斯人。聖彼德堡來的。
我在有五十二個房間的皇宮裡出生。人們說,皇宮已經不見了,他們在原來的地方蓋了木材倉庫。這只是最近六年的的改變之一。
我決定不去記錄早期生活的事情,特別是不再屬於我的土地,我要把一切歸零。不是出於怨恨,而是因為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俄羅斯。
我的新國家:美國,目前的。
我不認為我會在美國成長。我要的是:
我的父母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離開人間。他們是自殺的,在巴斯特基維茲的地產上服毒。無所謂。
美國大使救了我。那個晚上載著我離開的火車有十六節車廂。我們坐在第一節。我的姊姊愛瑪、美國大使、我,還有其他優秀的難民。美國大使愛上我姊姊。沒有帶著我的妹妹伊莉莎白我不走,她這麼說。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
說些其他的。
沒有錢,真的窮。我活得下去,是因為我會彈琴。當初學音樂是因為這是女人嫁人的必要嫁妝,還有義大利文、法文、繪畫、詩、跳舞以及園藝。但只有音樂派上用場。
夠了,以目前來說。
我晚上九點二十分上床。
我的身體
我的姊姊才稱得上漂亮。我呢:可悲的線條。大嘴巴,眼睛普通。頭髮太細,黑色,很黑。不過,男人都被我的身體吸引。我瘦瘦的,胸部,腿,珍珠般的皮膚,腳踝,袒胸露臂的衣服。男人都被我的身體吸引。因為我的臉醜,他們比較容易直接洩漏出性的胃口,不需再經過愛情或詩意的包裝。而我也陪他們玩。我喜歡展露我的身體。我常彎下腰露出胸部。我會打赤腳到處晃,或是讓裙子滑開,露出大腿;說話的時候,會把胸部靠在男人身上。我也會把一隻手夾在兩腿之間,靜靜地環顧四周。諸如此類的事。
所有男人都像小孩一樣。
我讓他們瘋狂。
我和十一個男人上過床,但我仍然是處女。我也不反對讓兩個男人從後面弄我,但他們大概不太滿意,因為兩人後來都沒有再露面。我想我讓他們覺得屈辱,我喜歡這樣。性是一種報復,至少目前是如此。不會永遠是這樣子,但現在是。
我需要對一些事情報復。
我需要對一些事情報復。
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
我計算過,我平均待在一個家庭一百二十二天。有些人上了最初幾堂課後,就停了下來。於是,我們就去把鋼琴載走,也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很多人則是度過三個月,也買了鋼琴,但放棄上課:他們愛上那件家具。他們覺得單是擁有鋼琴,就是很特別的事,即使靜默無聲也無所謂。只有很少人會利用額外的三個月課程。這些人到最後都希望我留下來,甚至當他們孩子的家庭教師。但我從來不想這麼做。於是,我繼續在新英格蘭的鄉村漫遊,有篷貨車上載著我、老么,以及兩台、三台或四台拆解的鋼琴,視情況而定。
再沒有比新英格蘭的鄉村更令人沮喪了。
於是,我孕育了我的計畫。這只是為了有個目標。每天泡在鄉村過同樣的日子,簡直會要我的命。
我預先訂下目標,要腐化我工作的每一個家庭。平均來說,我有一百一十二天的時間,有時候更短,但沒有關係,我必須實現目標。
這本日記就是我這番事業的目錄。
要腐化一個家庭不是什麼難事。所有的家庭都是腐敗的。
我要去睡覺了。
收到姊姊寄來的一封信。她住在開羅,過著溫室花朵般的生活。任何事都可能要她的命,因為她抵達埃及時,精神已經崩潰。這點她很清楚,但沒有什麼不悅。她告訴我一些消息,我從未回信。
奇怪的是,老么也每星期都收到一封信,但他不僅沒有回覆,連信都不曾打開看。老么通常都睡在貨車上,這樣可以省下旅館錢,另外存起來。他也有他的計畫。
很大的計畫。
哈,哈。
晚上十點十一分上床睡覺。餓著肚皮,就如預測的一樣,第二天了。
離終點還有四百九十八天,但願上帝高興。
但願上帝高興,這是我父親常用的典型句子。其他的還包括:
致上所有的敬意。
以適當的比率。
大聲說話,不是大聲思考。
願意謹守事實。
諸如此類的話。
死者雖已離開人間,但仍透過我們的聲音說話。
嘛。
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
我在庫提斯家時,起初想到的對象是太太。這家人有錢,但無趣。他們已經有鋼琴,可是他們喜歡我。太太停止彈琴多年,準備重新開始。她無事可幹。她把我當女兒看待。不過,除非你們買另一台鋼琴,否則也無法上課。於是,他們就買了。為了打發無聊,他們什麼都會做。太太有一票女性朋友,她因為無聊,有時會和她們玩些小遊戲。我可以想像那是她對忠誠觀念的一部分,是她們之間的勾搭。我會拿她做對象是很自然的事。有一天,她問我要不要試穿她的一些衣服,我說好。我在她面前又穿又脫,她很高興,我也裝作很快活。試到最後,都快試到床上了。但我要以文火慢燉,所以只和她親了一下。事情本應就這樣發展下去的,後來卻來了那場宴會。
太太決定辦場宴會,讓我在現場演奏。當然,我會得到我的酬勞,她說。那晚,我和庫提斯先生坐在陽台上,他喝著酒。我對他也必須扮演類似女兒的角色,這些人是那麼孤單,以致……
在某個節骨眼時,他突然哭了起來,告訴我他沒有錢付我的學費,沒有錢支付宴會開銷或其他費用,他身無分文了。每天早上他都假裝去辦公室上班,但辦公室早就不存在,他其實都去咖啡館,在那裡想辦法解決問題。我破產了,他說。起初,我想這些人會自己腐爛掉,然後我想到,也許我還可以推他們一把,如此也算是忠於我的計畫。我告訴庫提斯先生說我有個辦法。我不知道我那些點子都是怎麼來的,我就是有這種才華。於是,我在宴會上拿出幾張西伯利亞的照片,拍的是被共產黨下放到當地的一些人的慘狀,是我姊姊常寄給我的那類東西。我對這些東西向來無動於衷,我不在乎那裡發生的事情,我早就決定……這些和我無關。總之,我先談有關那些可憐蟲的事,說庫提斯先生鼓勵我為他們籌募一些錢寄過去,他已率先捐出一筆三百元的可觀金額。大家都鼓起掌來。在那種世界裡,慈善事業就像是運動,排名是很重要的事。大家都爭相捐出讓人頭暈眼花的數字,我收下所有的錢時,還裝出無法置信的感動模樣。之後,我偷偷把所有錢都轉給庫提斯先生。我會全數歸還的,他告訴我;說不定他真的是正人君子。我相信,我說。
六個月的時間期滿後,我向他們告別,然後一走了之。但在離開之前,我寫了一封匿名信給所有捐款給西伯利亞的人,建議他們查對一下捐款的下落。我相信庫提斯先生幾個月之後就舉槍自殺了。但反正他早晚都會走上這條路的。詐騙的人是他,我對警察沒什麼好怕的。他們找我也沒有用,來不及了。
重要的是要經常改變區域,這點無庸置疑。老么不瞭解,但我很清楚。
美國那麼大,這不是問題。
我還要在這裡停留多久?
老么還會在這裡停留多久?
說不定有一天,布爾雪維克黨的鐵騎會馳騁到這裡的平原,我們必須再次換個地方叨擾。
我寧可住在一個歷史不會降臨的地方。有這麼一個歷史缺席的地方嗎?有的話,我就要住在那裡。
我是躲藏在歷史巨船上睡覺的偷渡客。
老么也是偷渡客。
只有那些小人才帶著所有家當買票上船。他們關心船開往哪裡,我們不在乎。
但以後的事我不知道。
晚上九點五十五分,偷渡客去睡覺。
○老么的童年雖然他叫老么,其實是第一個孩子。「最後一個。」他母親才從分娩恢復意識就這麼說。於是,他從此被喚作老么。起初,他似乎根本不想知道這些。在他生下來的頭四年,幾乎所有的病都生過了。他們為他施洗了三次:因為神父無法為這樣一個張著眼睛的小不點做臨終塗油禮,所以每次都轉而為他施洗,免得沒做聖禮就空手回去。「這沒什麼壞處。」老么每一次都活下來,雖然蒼白、瘦小得有如一片破布,但總是活著。他有顆強壯的心,老爸這麼說。他運氣好,老媽說。他就這樣活下來,一九○四年十一月他七歲又四個月的時候,父親帶他到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