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如果我一直很乖……
小時候上作文課時,老師要我們讀故事寫心得。故事的內容是對日抗戰期間,女童軍送國旗給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守軍的故事。
照說,這個關於榮譽、愛國、奮不顧身的故事,心得一點也不難寫。
不過那時我故意唱反調,寫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詳細的文字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意基本上是:
一、如果不能打勝仗,送國旗也沒用。如果能打勝仗,國旗過幾天再掛也沒關係。
二、如果打敗仗還掛國旗,老百姓會誤以為打勝仗,錯過了逃亡的黃金時機。
還有,
三、國土失掉了,還可以收復,但女童軍命沒了,就無可挽回了。因此還是命比較重要……
我還寫了不少理由,總之,結論就是大唱反調。
可以想像,在那個國家、民族情操重於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師約談了。
老師問我:「老師平時對你好不好?」
我說:「好。」
「如果你覺得好的話,聽老師的話,別人怎麼寫,你就怎麼寫。」老師停了一下,又說:「大家會怎麼寫,你知道吧?」
我點點頭。「為什麼?」
「你相信老師,這是為你好,你聽話以後才有前途。」
「噢。」
我相信了老師,從此我的文章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種是公開的、「聽話」的文章,像是:作文課的作文、比賽的作文、考試的作文、貼在壁報上的作文。另一種是偷偷摸摸的、「不聽話」的文章,像是:傳小紙條的文章、寫情書的文章、投稿的文章……
一直到了我長大之後,我母親還很喜歡數落我小時候多麼頑皮、多麼不乖的事蹟。當然,四行倉庫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對我來說,那些其實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話,或者誠實地說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事情而已。當時我一點也沒想過,那就是所謂的「不乖」。
依照那樣的定義,我這一輩子其實還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時沒有郵資,偷爸爸的郵票。像是,為了讓稿子內容更精采,編出許多學校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為了看電影,偷偷翻牆爬進電影院,被老闆拎著耳朵拉出來……
或者,像是,約會時沒有徵得雅麗小姐的允許,就偷偷地吻她。或在實驗室做研究時,明明大家都覺得異想天開、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試。或明明大家覺得是沒有機會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辭去了醫師的工作,成為一個專職作家,成為一個編劇、廣播主持人、電視連續劇製作人……
回想起來,是這些「不乖」、「不聽話」的作為或決定,一點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決定性的部分。
有時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時候放棄了「不聽話」的文章,只寫「聽話」的文章,或者因為沒有零用錢買郵票,因此放棄投稿,或者先徵詢雅麗小姐同意,才敢吻她……少了這些「不乖」,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師講的一樣,所有要我乖的人幾乎都是很善意地為我好。我也相信,聽話的人的確會有前途。那時候我並不明白,不聽話的人,長大一樣會有前途的——差別只是,聽話的有聽話的前途,不聽話的有不聽話的前途。
回想起來,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想讓那個年輕、不乖又有點徬徨的自己,或者像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知道:
別擔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繼續努力、用力讓自己長大成心中想望的樣子,一切都會很好的。
那時,如果能聽到類似的話,從愛我或為我好的人口中說出來,或許我會少些猶豫,多點堅定與專注吧。
於是,我開始了這本書的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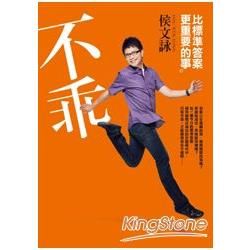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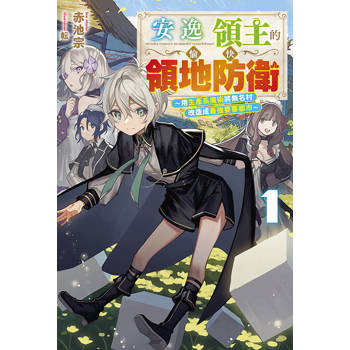

靜思語錄:「信己有力,凝聚衝破難關的勇氣; 立願付出,走出人生的大好坦途。」,有100個人,對一件事的看法和發展,100個人都同意這件事的看法,那表示以後就不會再有進步的空間。如果有99人,對這件事都持反對的看法,只要有一個人認同,你的未來發展的理念,那就大膽放手一博,也許你將有機會成為未來之星。 論語-季氏篇:「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大意是說:生來便知道的,是上等人;學習後知道的,是二等人;遇到困難再學習的,是三等人;遇到困難直接就放棄的,這就是下等人。阻礙我們前進的磚牆,不會無緣無故擋在我們前面。當它出現時,你可以選擇,痛過、跳過、繞道、逃避、沮喪........不論你要用什麼方式,請記住,絕不能往回頭,要勇往直前。這種磚牆的存在目的,不是為了把我們排除在外,而是要讓我們有機會證明多麼來要一件東西。 相信自己,勇敢追逐自己的夢想。夢想,要會有一股想哭的衝動,只有哭過,才會有屬於自己的感動。 前進,是為了應許自己能耐的極限; 後退,是蟄伏扶搖直上的風華絕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