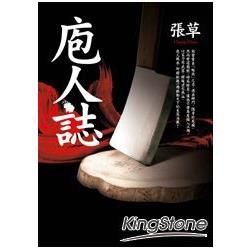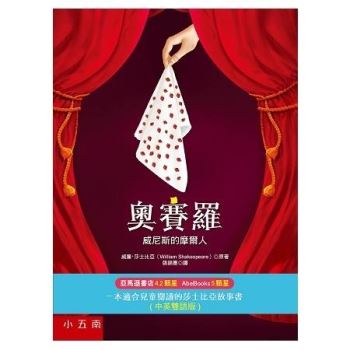似曾相識燕歸來──《庖人誌》
(一)
在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中,無論是錚錚鏜鏜的俠客英雄、毒毒惡惡的巨奸大憝、遮遮掩掩的偽君子、循循縮縮的濫好人、陰陰詭詭的真小人,都深切的明白,江湖,或者說是武林,是他們唯一淋漓盡致地展現自己所長的舞台。此一舞台,如果是構設在一個動亂的時局中,則更無異是如虎之添翼,得以讓他們匹馬煙塵,所向無前。他們通常會想像自己是一顆碩大無朋的巨石,將投注於江湖之中,激起無數的驚濤駭浪。人在江湖,無論是勝是負、是成是敗,能夠瀟瀟灑灑的走上這麼一回,也就算是不枉一生的英雄歲月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江湖是積極的、奮發的,具有無限光明前景,值得有心人士踴躍投入其中的。
只可惜,這樣的江湖,基本上都只是小說家言。小說和歷史一樣,喜歡著墨於引領風騷的英雄人物,從未想到,一將功成萬骨皆枯,千千萬萬粉身碎骨的無名屍骸,堆垛了英雄名將的崇高地位,那些陷陣鏖戰犧牲的士卒固無人記得,荒村廢墟、城池溝壑下輾轉流離的普通老百姓,更是無足牽掛,美麗的英雄傳說,對他們而言,真真是個無可挽回的錯誤。武俠小說,多得是美麗的傳說,卻很少有人書寫其中荒誕而悽慘的錯誤。
《庖人誌》是非常另類的武俠小說。「庖人」者,廚師也。歷來武俠小說以引車賣漿者流為主角的不是沒有,如古龍《三少爺的劍》寫在妓院裡打雜的「沒有用的阿吉」、于東樓《短刀行》寫揚州名廚師小孟、秦紅《戒刀》寫剃頭師傅去無終,都是「小隱隱於市」的大英雄,未來的江湖,正有待他們去開創建設。但《庖人誌》中的廚師阿瑞卻不一樣。他的身世連自己都不明白,也從來沒想過狹窄的廚房之外,還會有怎樣的一個世界。他是青城「叛徒」,武功小有根柢,廚藝刀工很是過得去,但距「庖丁解牛」的境界,還相差著一大截。他隱居於市集,廚房的世界就是他唯一的世界。可廚房世界本就是現實世界中的一環,當鑣頭司徒徹從外面廳堂被打入廚房的那一刻,兩個世界便合為一體,阿瑞就不得不重出江湖。
然而,這是個怎樣的世界呢?
(二)
明末時期,朝中有閹宦弄權、黨派相爭,地方有流寇作亂、烽煙四起;而清人虎視耽耽、屢開邊釁,國敗家亡,危在旦夕。這本就是寫草莽群雄奮發崛起的最佳時局。金庸的《碧血劍》以這一時代背景,塑造出袁承志這樣的英雄;梁羽生則在一系列的小說中塑造了「天山派」的志士。台灣的武俠小說,由於政治忌諱,「去歷史化」的輕易放過了這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正不能不說是一樁最大的遺憾。儘管在書寫袁承志和天山群雄的過程中,金、梁二人皆會有不同程度的觸及到戰亂之際哀哀生民的苦難與折磨,但英雄志士之痌瘝在抱,難免還是以居高臨下之姿,視民如傷,而未見得真能體會到「民傷」若何。苦難生民的哀戚,究竟仍與英雄了不相涉。以此而言,《庖人誌》不僅是台灣罕見的以亂世為舞台的武俠小說,將閹宦、流賊、官軍之荼毒百姓,覶縷述出;更難得的是,以一般尋常百姓、一般普遍人性為摹寫重點,寫出了在此一板蕩的時局中,苦難洊臻的悲哀。
《庖人誌》中唯一可稱得上是英雄的,只有阿瑞一人。可阿瑞一點都不想做英雄。龍蛇起陸,英雄得志,這不是《庖人誌》的主題。阿瑞是個平凡而單純的小人物,他無意趁亂崛起,更無心建功樹名,只是為了反對住持朱九淵與張獻忠的通同一氣,受到迫害,而逃隱於廣東佛山一味堂當個廚師。當鄭公公挾著閹宦的威權,逼得他不得不出來一戰時,「他終於明白,他此時此刻,不為過去,不為將來,不為馬老師傅,也不為龔師傅,亦不為廣西老布摩或威遠鑣局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人物」,「他只為當下此刻的正義而戰」!什麼是「當下此刻的正義」?這豈是所謂放諸四海皆準的「正義」?亦不過是卑微地欲維護自我一己的身家性命而已。因此,就在眾人一團混戰的時候,突然傳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皇帝自縊煤山的惡耗,一切紛爭都告終止,國已破、家已亡,爭名爭利爭意氣,還有什麼意義?如何在亂世中茍延性命,並於其中攫得若干利益,才是最實際的。
阿瑞平生無大志,事實上連被目為叛徒的「冤情」都無須洗雪,在亂世之中,人人都是為自己、為家人、為親友而活,便縱有一些欺詐、奸巧、無恥的勾當,與鋪天蓋地而來的戰禍相形之下,簡直等如雞毛蒜皮,無足深究了。朱九淵和鄭公公是書裡「奸惡」的代表,為了掩飾不名譽的私通,朱九淵狠心地欲置翠杏於死地,並企圖鏟除阿瑞這孽種,更異想天開的想登基當皇帝,惡固是惡矣,卻只令人感到可憫可笑,青城山有幾多兵力,足以與流寇、清兵分庭抗禮?鄭公公早年被童伴欺辱去勢,入宮掌握權勢之後,先是展開屠村的報復,隨後就帶著二、三十個護衛,饑不擇食的妄想擁立,奸亦奸矣,卻等如蚍蜉撼樹,根本無礙於大局,只顯得荒謬無謂而已。大局如此,渺小的個人究竟能起如何的作用?一顆小石子,投入於波濤洶湧的大海中,是連一絲絲的漣漪都激盪不起的。阿瑞找到了生母、認了外祖、救了彩衣,隱避在深山的岩穴中,「他心底湧起一股溫暖,流遍周身,驅走了山林潮濕的寒意」,他明知不可能,但「仍然希望,這一刻將是永恆」,這是多卑微的希冀,多無奈的「英雄」!
《庖人誌》寫的不是江湖霸業,不是武林叱吒,莽莽亂世,哀哀百姓,深沉的描繪出在天崩地裂的時勢中,人的無奈,人的不得已,是既真切又感人的。
(三)
自金庸、古龍兩大名家牢籠百家之後,武俠小說似乎已經進入了無可突破的瓶頸階段,新進作家無不絞盡腦汁,求新求變,試圖打開此一停滯不前的僵局。黃易從科幻入手,變之以玄幻;奇儒援佛理寫武俠,力求禪悟;溫瑞安則變換文字,以奇譎為戲,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但皆是從取材上、文字上入手,很少有作者從「敘事」的手法與視角上改弦更張,為武俠小說找到新的出路。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的首位得主吳龍川是唯一採取不同敘事手法經營的作家,《找死拳法》別開生面的新嘗試,是很具有創意的,但學術味太強,讀者不易卒讀,武俠的生路,究竟還是未能打開。《庖人誌》的出現,應該是令人驚豔的一次突破。
張草學醫出身,對易學、老莊、陰陽五行之說,別有心得;筆鋒銳利,曾在科幻小說創作中廣獲好評。深厚的國學根柢,使他在轉向創寫武俠時,得力更多,在〈弈士志〉中,寫符十二公的奇門遁甲,於陣法變幻中,理致井然,頗具司馬翎的神髓;《十牛圖》的糅合禪境與武學,也令人眼界頓開。但全書最引人矚目的還是整個敘事手法的突破。
《庖人誌》分〈庖人〉、〈山伕〉、〈中官〉、〈弈士〉、〈阿母〉、〈桑女〉六個章節,儘管還是以第三人稱全知的手法敘述故事,但能以敘事時間的交錯手法,分別以這六節中的主要人物展開整體情節的架構,深入的描繪了其中主要人物的形象與思維,故事時間是在明朝天啟年間到崇禎十七年八月,但在主敘事的崇禎十七年間,分別插入了阿瑞母親翠杏的經歷、閹宦鄭公公的生平,將明末整個朝政與社會的亂象,勾勒得鮮明而生動,可謂是相當新穎而成功的嘗試。尤其難得是,作者筆觸的重心,不純在「英雄」,而藉若干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挑伕、弈士、桑女,串連起整個故事,就連鄭公公,也讓讀者可以細細追摹其內心思想的變化過程,相當寫實而動人。儘管在視角的轉化、運用上,《庖人誌》還未完全能掌握透徹,尋母的繡姑,最終也嫌沒有交代,但本人相信,這將是一個極具意義的開始。
武俠小說,也許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但讀了《庖人誌》,倒教我有幾分「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喜悅。
也許,武俠的春天也不會太遠了?
林保淳序於說劍齋二○○九年十月
後記:九年一夢庖人誌
曾經,聯合報的文學獎每年換題目,二○○一年的題目是「武俠」。
還記得,一九九四年未出版小說時,曾將《雲空行》投稿某大報副刊(姑忘中國時報抑或聯合報了),結果被原封不動的退回。寫作的人當然想弄個明白,於是去電報社,詢問退稿的原因,以及有何改進的空間。
結果答案是:「我們不收武俠小說。」
「咦?」我楞了一下,「我那篇不是武俠小說,是宋朝的道士……」
對方也不多說:「總之我們不收武俠小說。」
我有一種被人未審先判的感覺,寫《雲空行》時,主題在中國古籍中的妖異紀事,刻意不寫武打,只有極少數篇幅涉及武打,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看見故事背景放在古代,就叫武俠小說了?
所以,當我看見他們居然會舉辦武俠小說比賽時,便想寫一篇去湊熱鬧,這一次不但要通篇武打,而且絕無新意,盡用以前的人寫過的元素,哦不,我看膩了爭秘笈、爭寶物、爭武林盟主、爭天下第一的內容,所以,帶有反諷意味的,就爭一個粗糙的神像吧,那是廣西土族的祖神像,一般人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但卻是他們重要的信仰之物呢。
於是,我日夜趕稿,炎夏七月,趕在截稿之日,抱了手提電腦到在板橋工作的牙醫診所,一沒病人就狂寫,中午休息時回家去列印,請老婆幫忙寄出。
結果,入圍評語是:沒有新意,點子多是別人寫過的,(十分贊成)而且,爭個看來沒用的神像幹嘛?(故事中交待得很清楚,是宮中娘娘要收集的)
該屆冠軍作品是以現代城市武俠為題的作品,恰好評審也剛出了一部以現代城市武俠為題的作品。(說真的,那位評審的作品我讀得津津有味,除了不停跟女人纏綿的那段之外)
次年四月,我那篇入圍作品要在北美世界日報刊出,我又再修改了一次,以修補當時趕稿匆忙未盡之處。(往後數年,<庖人誌>四易其稿,方為今日面貌)那一年稍後,我離開待了十一年的台灣,回到馬來西亞。
* * * * *
我以前一直在想:錦衣衛跟太監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常常寫他們狼狽為奸?
為什麼武俠小說的男女主角沒有收入,還能四處游蕩,浪跡江湖?
為什麼電視劇中的武俠人物老是裝扮怪異,他們能走在街上見人嗎?
那個年代的女孩子適合行走江湖嗎,豈不十分危險?
他們怎麼解決吃飯和大小二便問題,怎麼故事中提都沒提?
我讀過的近代武俠小說,其人物都不是社會上正正常常的人物,他們成群結黨、用武力解決問題,那跟黑社會有何兩樣?
反觀武俠小說鼻祖,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寫的<刺客列傳>及<遊俠列傳>,乃至於唐代《虯髯客傳》、明代《水滸傳》及歷代筆記小說,其武俠人物皆有各自的職業,或屠夫,或軍人、小販、工匠等,只不過其共同點是,以武術行俠義之事。
二○○一年寫<庖人誌>時,已經設下了一個模式:故事中要出現多種職業的人,他們的共同點就是懂得武藝。
寫完<庖人誌>之後,這個故事在我腦中糾?多年,像是一首未譜完的曲子,只不過寫了序曲而已,尚有許多動機和樂段未曾發展……直到完成了《諸神滅亡》和《明日滅亡》,將「滅亡三部曲」結束之後,我才在二○○五年二月開始寫續篇<山伕誌>,但是,中間不斷遇上瓶頸,寫寫停停,短短兩萬多字,竟寫了一整年,到次年一月才完成。
之後,很想寫一寫鄭公公的故事,一時靈感如泉,緊接著花了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中官誌>。因此這一篇雖然最為複雜,也最為流暢。
乘著<中官誌>一鼓作氣的餘勢,二○○六年四月,我馬上著手寫<弈士誌>,主題是「都江堰保衛戰」。沒想到,都江堰的地理、歷史資料是如此稀少,故事進行到此,轉折又是如此困難,中間還曾經失控,越寫越長,完全可以開展出另外一部長篇故事。後來我及時煞車、修改,磋磨兩年,竟寫到二○○八年六月才收尾!
<阿母誌>的題目是跟<弈士誌>同時訂下的,我一直想寫阿瑞的來歷,直到完成<弈士誌>,又花了半年,才在二○○九年一月寫完。
多年前告訴過皇冠出版社的主編春旭,我在寫武俠,她聽了就面露擔心貌:「武俠嗎?不好賣呢。」寫了五篇之後,乘著二月訪台參觀國際書展,我將原稿交給她看看,也交給皇冠退休了的陳主編(發掘我處女作《雲空行》的恩人)以及平雲先生看看,結果他們的意見一致:「還有第六篇嗎?」
「有,籌備中。」
「你會寫彩衣吧?」
他們都知道,我很少寫男女之情,因為我會覺得愛情是個人十分私密的一部分,下筆時會有在大眾面前赤裸裸的感覺,令我退卻。
「會,其實我也一直想寫彩衣。」
彩衣,這位五年前在<山伕誌>中驚鴻一瞥的人物,這趟我花了五個月為她立傳,是為<桑女誌>。
* * * * *
前面說過<弈士誌>在漫長的兩年書寫中曾經失控,並且刪掉一大段,而這些被刪掉的部分,則成了下一部小說的主題。
那是一段十分恐怖的歷史,也是阿瑞等人必須去面對的可怕未來。
我希望,這一次我不會再用個九年去寫第二部。
看倌們,欲知後事如何,留待下一部《蜀道難》為您分解。
張草二○○九年十月中旬於亞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