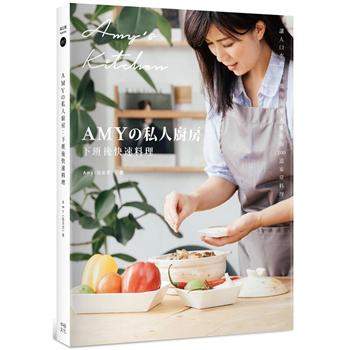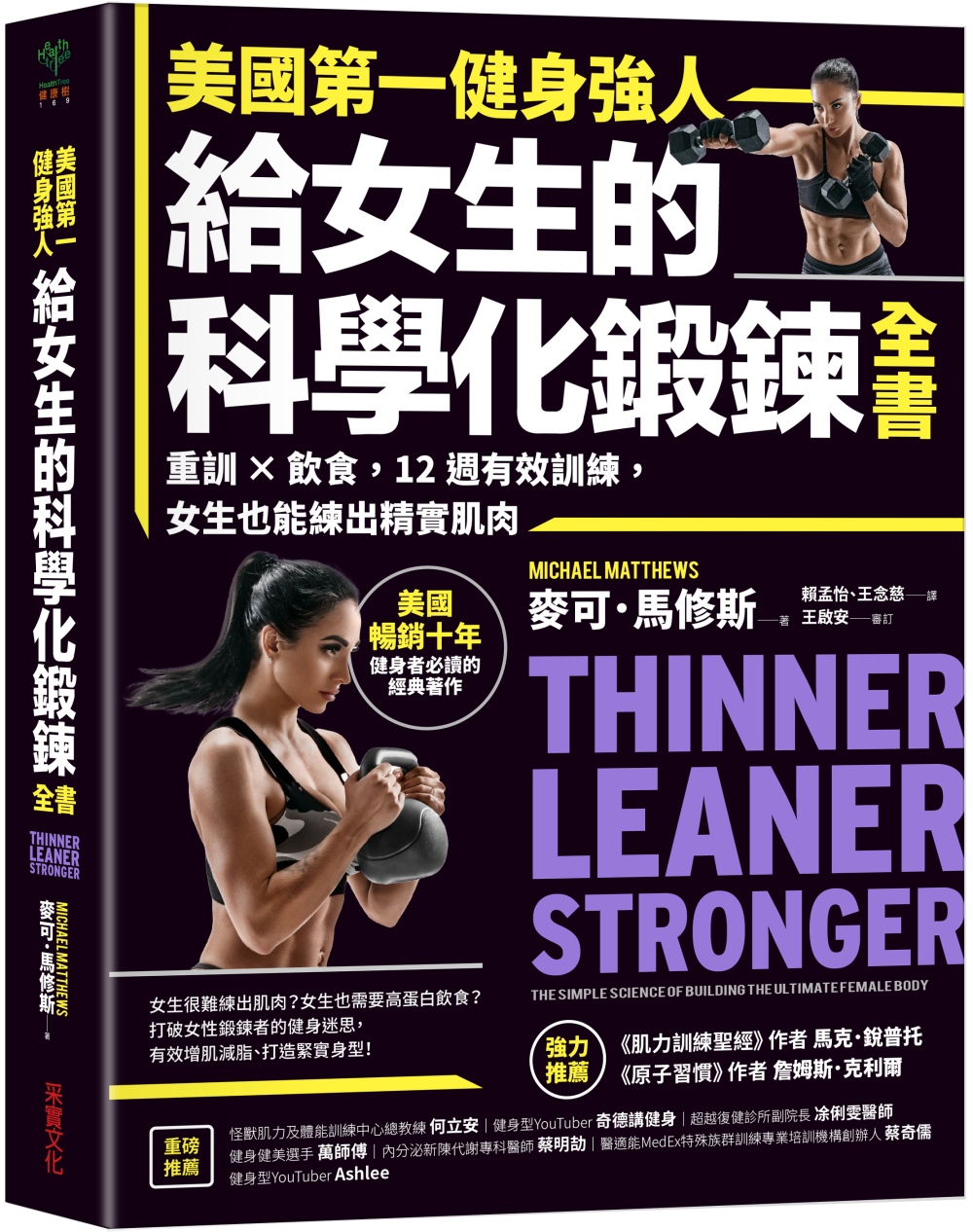保羅‧奧斯特與你的神祕連動遊戲!展現華麗說書技巧的夢幻傑作!
遺忘過去,卸下身分,剝除關係。
直到我們一片蒼白,直到我們都變成「無名氏」,直到我們大聲探問「我是誰?」
一個出不去的房間,
一個遺忘過去的人,
一個愛與責任的謎團,
一個永不結束的故事……
故事開始了嗎?他悠悠醒來,發現自己被關在一個房間,單調寂靜,沒有多餘的家具和擺設,除了書桌上靜靜躺著的四疊手稿和三十六張照片。
我是誰?我來自哪裡?他遺失身分、遺忘過去,人們稱他「無名氏先生」。他迫切地想從手稿與照片中找到蛛絲馬跡,找到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聯。然而如同他的身分一樣無解的是,手稿上記載了不可思議的故事,卻在最緊要的關頭戛然而止。而照片裡多是他不認識的人,卻有某些熟悉的面孔讓他心中生起沉重的罪惡感。
不時有人前來探視,或關心無名氏先生,或幫助他指認照片中的人。房裡的時光悠長緩慢,無名氏先生的記憶時而清明、時而恍惚。有幾個時刻,他覺得自己幾乎能捕捉與這些拜訪者或影中人的生命交集,卻又在下個瞬間,茫茫然頓失記憶的脈絡。
直到他翻開最後一份手稿《書房裡的旅人》,映入眼簾的字字句句,竟是如斯熟悉,熟悉得令人驚愕……而故事就此結束了嗎?故事也許才正要開始。
當你翻開這本書,便進入了蒼白的房間,便無可自拔地投身至一則無休無止的故事。膠著的現況、失焦的回憶、游離的身分,無名氏先生所面臨的難題反映出人際網絡中每一個人的迷惘與徬徨。而《紐約三部曲》、《幻影書》等舊作主角重登故事舞臺,不僅讓書迷拍案叫絕,更蘊含著作者匠心獨運的巧思:我們和書中人一起在故事裡翻滾、遊蕩,如同我們被拋入世界,就此存活下去。
作者簡介:
保羅‧奧斯特 Paul Auster
集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譯者、電影導演等多重身分於一身,是村上春樹最喜愛並親筆翻譯其作品的美國當代大師級作家。
一九四七年生於新澤西州的紐渥克市。在哥倫比亞大學唸英文暨比較文學系,並獲同校碩士學位。年輕時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不斷嘗試各種工作,甚至曾參加舞團的排練,只為了「觀看男男女女在空間中移動讓他充滿了陶醉感」。
他早年的創作深受法國詩人及劇作家的影響,《紐約三部曲》則是他重新回歸美國文學傳統的轉捩點。他曾獲美國文學與藝術學院頒發的「莫頓•道文•薩伯獎」,以《機緣樂章》獲國際筆會「福克納文學獎」提名,並以《巨獸》榮獲法國文壇四大文學獎之一的「麥迪西獎」。
奧斯特的小說一貫以豐沛的想像空間,對自我與他者、孤獨與社會、心靈與物質進行沉思和反芻,充滿了智慧與迷人的丰采。其他作品包括回憶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評論集《饑渴的藝術》、詩集《煙滅》、小說《月宮》、《在地圖結束的地方》、《昏頭先生》、《幻影書》、《神諭之夜》、《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以及《黑暗中的人》及《無形之物》(皆為暫譯名,皇冠將陸續出版)。
一九九○年代起,奧斯特積極參與電影工作,除為華裔名導演王穎編寫「煙」的劇本(「煙」曾榮獲柏林影展銀熊獎、國際影評人獎及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並與王穎合導了「面有憂色」,以及獨立執導「綠寶機密」(Lulu on the Bridge),深受稱許。
目前他與妻兒定居於紐約布魯克林區。
譯者簡介:
趙丕慧
一九六四年生。輔仁大學英文碩士,現任教於朝陽科大。譯有《幻影書》、《戰地琴人》、《少年Pi的奇幻漂流》、《穿條紋衣的男孩》、《珥瑪的351本書》與《贖罪》等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媒體好評︰
奧斯特的說書技巧之佳令人畏懼!──蘇格蘭論壇報
奧斯特是不折不扣的小說大師!──哈波時尚雜誌
充滿自信之作!──蘇格蘭人報
他的書迷將迫不及待一睹為快!──衛報
最小的迷宮
【知名作家】張惠菁
保羅•奧斯特擅長造迷宮。
並且他的迷宮有越來越小的趨勢。從《紐約三部曲》、《月宮》開始算,這兩部以紐約曼哈頓為迷宮範圍。到《神諭之夜》,基本上已不出布魯克林的一段街區。至於《書房裡的旅人》,這趟旅程始終在一個房間裡,一步也沒走出去。
空間範圍最小的《書房裡的旅人》,和保羅•奧斯特先前的作品連繫甚深。很像是一間密室入口,通往地下隧道,隧道連結了奧斯特所有作品。
《書房裡的旅人》有個「記憶拼圖」式的開頭。
一位身分不明的老人,既像囚犯,又像房客,也可能是個病人。他好像有記憶上的障礙,身上壓著來自過去的重負。他好像在害怕想起一些事,但總會有人跑來要他負責。他在使用藥物。按時送餐送藥來的人說那是「治療」。但這「治療」似乎不是為了幫助他把記憶串連起來;正好相反,是為了打散他的記憶。
奧斯特總有辦法隨時就地起迷宮,召雲喚霧,動員日常的家具、書本、環境,一下子布置成謎團。老人很被動,在這房裡他像是被迫、被禁止、被規範的。到後來我們才發現這種生活好像是老人自己的選擇。有時候,人會希望自己是被迫、是沒有選擇的。絞盡腦汁作下安排,讓自己看起來沒有選擇,不知所措。
老人為自己造了一座無形的迷宮。記不得自己是誰,弄不清他創造的角色,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遭遇。時間斷裂。迷宮內外,幻影幢幢。他在裡頭摸索徘徊,被逼到沒辦法了,忽然口述出一段連貫的情節來,醫生趕緊抄下。這些情節就是老人的下一本書。
他基本上是一頭故事乳牛。按時吃藥,按時被「醫生」催情節。不過來找他的不只醫生,還有他從前的角色們。沒錯,這是個權力互換的狀況。說故事人反過來被故事裡的角色公審。
角色跑出故事外,反過來找上作者的門,這情節不是第一次發生,至少有電影「墨水心」、「口白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小說《天大好事》也可以算上一筆。不過奧斯特的迷宮,絕對是其中最冷酷的。
在奧斯特的迷宮裡──這是老人自建的迷宮,也是奧斯特為他建的迷宮──說故事人失憶失能,故事散架,角色們都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了。他們的經歷沒有目標、沒有傳奇,只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只有苦難。小說裡大時代兒女一眨眼就過去的十年,改用斗室裡的時鐘來計算分秒,怎麼可能不漫長?蠻荒、邊境,都不是浪漫的未知之地了,只有苦刑犯會被流放到那裡。於是書裡的人物都回來了,來跟作者算帳。
可是,時間變漫長,蠻荒變危險,或許只是因為作者老了,老到連房門都不想跨出去?
說到底,人物角色還是從作者身上生出來的。如果作者年輕的時候不介意出門旅行,會浪漫地想像投入一場大事業、大冒險,他創造出來的人物,或許也會充滿從他筆間流洩出的激情。當作家自己變宅男,那些被他幾行字寫得有去無回、浪擲一生的人物們也困惑了,想回家,想不起當初為何出門,想清算這一生究竟有何意義。
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神學都有過這樣的說法:個別的人類身上,存在著「神性的流出」。如此說來,這部小說寫的莫非是一種「神性倦怠」的狀態?在作家之上,如有一個造物者、超越個體性的存在,倦怠的源頭或許是祂,從祂開始,神性的流出開始乾涸。作家首當其衝,他的故事像旱季的河床。沒有了故事的流動,角色只是河床上的石礫。意義?那是三小?
老人選擇宅起來。藥物、圍牆,打散的記憶,老人的房間、奧斯特的迷宮,那是個機遇無處容身的地方。謎團包覆一切,不會有意外闖進來,不會像角色們的生命曾被作者任意書寫。但書寫也是賦予,他曾經賦予過意義。但現在,他,他的角色(他們),或許還有他背後的大老闆(祂),都他們害怕、怪罪這賦予。
奧斯特最小的迷宮,也是有史以來最難的迷宮。因為它困住的人並不想出去。
張惠菁
2010年9月20日於台北家中
名人推薦:媒體好評︰
奧斯特的說書技巧之佳令人畏懼!──蘇格蘭論壇報
奧斯特是不折不扣的小說大師!──哈波時尚雜誌
充滿自信之作!──蘇格蘭人報
他的書迷將迫不及待一睹為快!──衛報
最小的迷宮
【知名作家】張惠菁
保羅•奧斯特擅長造迷宮。
並且他的迷宮有越來越小的趨勢。從《紐約三部曲》、《月宮》開始算,這兩部以紐約曼哈頓為迷宮範圍。到《神諭之夜》,基本上已不出布魯克林的一段街區。至於《書房裡的旅人》,這趟旅程始終在一個房間裡,一步也沒走出去。
空間範圍最小的《書房裡的旅人》,和保羅•奧斯特先...
章節試閱
老人坐在窄床床沿,雙手置膝,掌心朝上,低垂著頭,瞪著地板,絲毫不覺上方有架攝影機。每隔一秒快門就喀嗒一聲,與地球自轉一周同步,攝製出八萬六千四百張靜止的畫面。即使他知道自己被監視了,也沒有什麼差別。他的心思不在這裡,而是擱淺在腦海中的想像世界,絞盡腦汁想要解開糾纏著他不放的問題。
他是誰?在這裡做什麼?是幾時到的?又要待多久?運氣好的話,時間會為我們揭開謎底。目前,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是仔細研究這許多的照片,盡量不要太早下定論。
房間裡有不少東西,而且每樣東西的表面都貼上了白色膠帶,上頭都用粗體字寫了字,比方說床頭几上的字是「桌子」,檯燈上的字是「檯燈」,即使是不能歸納為物品的牆壁都貼了一張寫著「牆壁」的膠帶。老人抬頭看了一會兒,看見了牆,看見了牆上的膠帶,輕聲唸出了「牆壁」兩個字。但我們不清楚他究竟是把膠帶上的字唸了出來,還是正巧說到了牆壁。說不定他學過的字早就已經都忘了,但是他還知道每樣東西的稱呼;也可能情況正好相反,他已經喪失了識別物體的能力,卻還認識字。
他穿著藍黃色條紋棉睡衣,腳上穿著皮拖鞋。他並不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方。沒錯,他是在房間裡,但是房間又是在哪棟建築物裡,是住家?是醫院?還是監獄?他想不起自己在這裡多久了,也不知道他是因為什麼緣故來到這裡的。說不定他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裡,可能打從他出生開始就一直住在這裡。他只知道他的心中充滿了無法消解的罪惡感,但同時他又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冤屈。
房間有一扇窗,但是百葉窗放了下來,他記得他還沒看過窗外。還有房門也是,門把是白磁的。他是被鎖在房裡呢,還是他可以自由來去?他仍未去找出個究竟,因為正如第一段說過,他的心思不在這裡,而是飄浮在過去,在聚集在他腦海中的鬼魅之間遊蕩,苦苦追尋糾纏著他不放的問題答案。
照片不會說謊,卻也無法道盡完整的故事。照片只不過是記錄過去的時間,是外在的證據。比方說,從微微失焦的黑白照片中就很難斷定老人的年紀,唯一能夠說得很肯定的是他年紀不小了,可是「老」這個字很有彈性,六十到一百歲的人都可以說老,因此,我們就不使用「老人」這個稱呼了,改用無名氏先生。目前,他究竟叫什麼名字並不是頂重要。
無名氏先生終於離開床舖站了起來,他略停了一下,穩住身形,隨即趿拉著腳步走向房間另一頭的書桌。他覺得很累,彷彿剛剛從斷斷續續的短暫睡眠中清醒,他的鞋跟擦過沒有地毯的木頭地板,讓他想起了砂紙的聲音。房間之外遙遠的地方,距離房間所在的建築物遙遠的地方,他隱約聽見了鳥叫聲──可能是烏鴉,也可能是海鷗,他分辨不出來。
無名氏先生彎身坐進了書桌前的椅子裡,椅子舒服得不得了,他斷定是用柔軟的棕皮做的,椅臂很寬,手肘和前臂可以放心的架上去,此外還有看不見的彈簧機制,讓他可以隨意地前後搖晃,所以他一坐下就忍不住搖晃了起來。前後搖晃產生了一種撫慰的效果,無名氏先生隨興愉快地搖擺著,同時想起了小時候房間裡的搖擺木馬,接著他開始重溫他從前騎著木馬跑過的想像旅程。那匹木馬叫小白,而在年幼的無名氏先生心目中,它並不是一塊漆上白漆的木頭,而是有血有肉的東西,是一匹真正的駿馬。
暫時回顧幼年時光之後,焦慮感又湧上了無名氏先生的喉嚨。他用疲憊的聲音大聲開口說:「我不能讓它發生。」說完,他俯身去檢查桃花心木書桌上擺得整整齊齊的一疊文件照片。他先拿起照片。一共是三十六張黑白照,照片上有各種年齡、不同人種的男男女女。最上面的一張照片是一名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黑髮剪得很短,凝視鏡頭的那雙眼中有濃濃的憂色。她站在某座城市的戶外,不知是義大利還是法國的城市,因為她剛好站在一座中古世紀教堂的前面,又因為這名女子披著圍巾穿著羊毛大衣,所以可以合理的假設照片是在冬天拍的。無名氏先生注視著女子的眼睛,苦苦思索她是誰,過了二十秒左右,他聽見自己喃喃說出「安娜」這名字,一股濃烈的愛意貫穿他全身。他不禁懷疑這個安娜會不會是他娶的人,又會不會是他的女兒?心裡才剛這麼想,又一陣罪惡感猛地襲上心頭,他當下知道安娜死了。更糟的是,他懷疑安娜的死他脫不了關係,他告訴自己很可能就是親自動手殺了她的人。
無名氏先生痛苦呻吟。看照片讓他情緒擾攘,所以他把照片推開,轉而注意那疊文件。總共有四疊,每一疊大約六吋高。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他伸手就去拿左邊最遠那疊文件的頭一份。上頭的筆跡是用粗體字寫的,和白色膠帶上的類似,內容如下:
從最遙遠的太空往下看,地球只不過是塵粒那麼大,下次你寫下「人類」這兩個字時千萬別忘了。
從他臉上浮現出的嫌惡表情來看,我們可以很放心的說無名氏先生並沒有失去閱讀的能力。但是是誰寫下這些文字的,卻仍是未定之數。
無名氏先生又伸手去拿這一疊的下一份文件,發現那是份打字稿。第一段說的是:
我一開口述說我的故事,就被他們打倒在地,頭也被踹了幾下。等我爬了起來,繼續往下說,有一個人又摑了我一耳光,另一個人一拳擊中我的肚子,我又被打趴在地上。我費了一番手腳才站起來,但就在我張口打算再次述說我的故事時,上校揪住我,把我往牆上撞,這一撞把我撞昏了過去。
接下來還有兩段,但在無名氏先生往下讀之前,電話響了。電話是黑色轉盤式的,上個世紀四○年代末期或五○年代早期的產品,因為電話放在床頭几上,無名氏先生不得不離開柔軟的皮椅,拖著腳走向房間另一頭。第四聲鈴響時他拿起了電話。
「喂。」無名氏先生說。
「無名氏先生嗎?」電話那頭的人說。
「你說是就是吧。」
「你確定嗎?我可擔不起弄錯的風險。」
「我什麼都不確定。要是你要叫我無名氏先生,我也欣然同意。你又是誰呢?」
「詹姆斯。」
「我不認識什麼詹姆斯。」
「詹姆斯.P.弗拉德。」
「說清楚一點。」
「我昨天來找過你,我們談了兩個鐘頭。」
「哦,對了,那個警察。」
「退休警察。」
「對,退休警察。有什麼指教嗎?」
「我想再來看你。」
「談過一次難道還不夠嗎?」
「倒也不是。我知道我不過是個小角色,可是他們說我可以見你兩次。」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見也不行。」
「恐怕是這樣。不過要是你不願意的話,我們不用在房間裡談。我們可以出去,坐在公園裡談,這樣可好?」
「我沒有別的衣服穿,我現在穿的是睡衣和拖鞋。」
「到衣櫃看看,你要的衣服裡頭都有。」
「衣櫃,對了。謝謝。」
「你吃過早餐了嗎,無名氏先生?」
「應該沒有。我可以吃飯嗎?」
「一天三餐。現在時間還早,不過安娜應該馬上就會過去。」
「安娜?你說安娜?」
「她是負責照顧你的人。」
「我還以為她已經死了。」
「哪兒的話。」
「也許她不是我說的安娜。」
「不可能。在這件事裡頭她是唯一一個站在你那邊的人。」
「其他人呢?」
「姑且這麼說吧,很多人是積怨難消。」
有一點要加以說明,除了攝影機之外,牆上還嵌了一具麥克風,無名氏先生發出的每一種聲音都會被一台高敏感度的數位錄音機給複製保存下來。因此即便是最小的一聲呻吟、最輕的抽鼻聲、最微弱的咳嗽、最微不足道的一個屁聲也都是不可疏忽的一部分。當然,這一份聲音資料也涵蓋了無名氏先生所發出的呢喃、話聲、吼叫,以及詹姆斯.P.弗拉德所打來的電話。電話最後是以無名氏先生無可奈何的同意讓退休警察上午來找他為結束。掛上電話後,無名氏先生坐在窄床床沿,又恢復了這份紀錄一開始時的姿勢:雙手置膝,掌心朝上,低垂著頭,瞪著地板。他在沉思是否該站起來,到衣櫃去翻找弗拉德提到的衣服,如果真有衣櫃的話,他是否該換下睡衣,穿上別的衣服,當然這是假設這個衣櫃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不過無名氏先生一點也不急著去忙這種俗務,他想回頭去讀那份電話響起前他看到的打字稿,於是他從床沿站起來,顫巍巍的朝房間另一頭跨出一步,不料卻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暈眩。他明白要是他繼續站著,他一定會跌倒,但是他沒有回去坐在床上,等待暈眩感退去,而是右手按住牆壁,全身重量就靠右手支撐,緩緩向下降,雙膝著地後,他上半身前俯,兩手按住地板,就這樣手腳並用,爬向了書桌。
費了一番力氣爬上皮椅後,他前後搖晃了好幾分鐘,穩住自己的神經。儘管吃了一番辛苦才爬過來,他卻明白他害怕去讀那份打字稿。為什麼這種恐懼會淹沒他,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過就是文字罷了,他告訴自己,什麼時候文字又有了把人嚇得半死的力量了?「沒事。」他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嘟囔,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又扯開喉嚨大聲尖叫說:「沒事!」
也不知為了什麼,這一聲莫名其妙的大吼竟然給了他接下去看的勇氣。他做了個深呼吸,眼睛盯著面前的文字,讀了下面兩段:
他們一直把我關在這房間裡。根據我的猜測,這不是普通的牢房,而且也不像是軍營或什麼地方防衛隊的拘留所。這裡很小,別無長物,大約是十二呎寬、十五呎長,從房間簡單的設計來看(泥土地面,厚實的石牆),我懷疑這裡曾是儲存食物補給的庫房,有可能是堆麵粉和穀類的地方。西面牆上有一扇加裝了鐵柵的窗戶,但是離地太高,我沒辦法攀上去。我睡在角落的稻草墊上,一天有兩餐可吃:早上是冷麥片粥,晚上是硬麵包和不冷不熱的湯。根據我的計算,我被關了四十七晚,不過我有可能算錯了。關進來的第一天,我不時被毒打,因為我記不得自己昏迷了多少次,也不知道每次昏迷持續多久,所以我很可能算著算著就混淆了,遺漏了某一次的日出或某一次的日落。
我的窗外就是沙漠。每次風從西邊吹過來,我就會嗅到鼠尾草和杜松的味道,這片乾燥土地上飄來最細微的味道。我在沙漠裡一個人住了將近四個月,自在的從一個地方遊蕩到另一個地方,餐風宿露,體驗過各種天氣;從開闊的大地局限到這間小小的牢房中,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我可以忍受被迫的獨居,可以忍受沒有人說話,接觸不到人,可是我非常渴望空氣和光線,而且我每天都巴望著能有什麼東西可以看,而不是只能看著這些粗糙不平的石牆。偶爾會有士兵從我窗下走過,我能聽見他們的靴子踩著地面,偶爾迸出聲音,馬匹和馬車在可望而不可及的白日中響動。這裡是阿提馬的營區:聯合政府的最西邊,位於已知世界邊緣的一個點。這裡距離首都兩千多哩,俯瞰地圖上並未標示的遼闊外疆。法律規定任何人都不准跨界,但是我跨界了,因為我是聽命行事,而如今我回來報告了。他們或許會聽,或許會當耳邊風,接著我就會被帶到外面去槍斃。現在我已經相當肯定會是這種結局了。重要的是別欺騙自己,重要的是去抗拒希望的誘惑。等他們終於把我帶到牆邊,用來福槍瞄準我,我唯一的要求會是讓他們拿掉我的蒙眼巾。我倒不是想要看清楚殺死我的是什麼人,而是想要最後一次看看天空。這就是現在我想要的東西,我想站在戶外,望著碧藍藍的天空,最後一次凝視那浩瀚的無垠。
無論實情如何,房門反正是打開了,一名嬌小的女子走進來,看不出來她多大年紀──可能是介於四十五到六十之間,無名氏先生想,可是很難斷定。她的灰髮剪得很短,身穿深藍色長褲、淺藍色棉衫,而且她一進房間就對無名氏先生微笑。這一笑融合了溫柔和感情,讓他的恐懼一掃而空,也讓他的心緒平靜了下來。他不知道這名女子是誰,但是他很高興見到她。
「昨晚睡得好嗎?」女子問道。
「不知道。」無名氏先生說。「說真的,我根本不記得有沒有睡覺。」
「很好,這表示治療有效。」
無名氏先生並沒有針對這句謎語般的話回應,反而默默打量她幾分鐘,隨後開口問:「請原諒我沒禮貌,可是妳不會就是安娜吧?」
女子又一次綻開溫柔多情的微笑。「我很高興你還記得。」她說。「昨天你還怎麼都記不住呢。」
突然間變得既浮躁又迷惑,無名氏先生轉動椅子,面向書桌,從那疊黑白照片上拿了那張年輕女子的相片。他還沒能轉過去看那個名字叫安娜的女人,她就已經站到他身邊來,一手輕放在他的右肩上,也低頭看著照片。
「如果妳叫安娜,」無名氏先生問,聲音微微激動,「那這是誰?她也是安娜,是不是?」
「對。」女子說道,仔細端詳著照片,彷彿是帶著反感又懷舊的心情,同時卻又與之矛盾的情緒在回憶。「她是安娜,我也是安娜,這是我的照片。」
「可是,」無名氏先生結結巴巴的說,「可是……照片裡的女孩很年輕,而妳……妳都有白頭髮了。」
「歲月不饒人啊,無名氏先生。」安娜說。「你了解歲月是什麼意思吧,是不是?照片上是三十五年前的我。」
無名氏先生還沒來得及反應,安娜已經把她年輕時的照片放回那疊相片上了。
「你的早餐快冷了。」她說,話剛說完她就離開了房間,但是不一會兒又回來了,推來了一輛不鏽鋼餐車,上頭有一盤食物。她把餐車推到床邊。
早餐有一杯柳橙汁、一片奶油吐司、一只白色小碗盛著兩個水煮荷包蛋、一壺伯爵茶。
「我是怎麼了?」無名氏先生問道。「生病了嗎?」
「沒有。」安娜說。「吃藥只不過是治療的一部分。」
「我不覺得有病,也許有點累、有點暈眩,就只有這樣。以我的年紀來說,並不算是什麼嚴重的毛病。」
「把藥吃了,無名氏先生。吃完藥你就可以吃早餐了,我相信你一定很餓了。」
「可是我不想吃藥。」無名氏先生答道,硬是不讓步。「既然我沒生病,我就不要吃這些可惡的藥丸。」
安娜雖然聽見了無名氏先生粗魯不客氣的話,卻沒有疾言厲色,反而彎腰親吻他的額頭。「親愛的無名氏先生,」她說,「我了解你的感受,可是你答應過會每天按時吃藥,我們講好了的。要是你不吃藥,治療就不會有效了。」
「我答應過?」無名氏先生說。「我怎麼知道妳不是在騙我?」
「因為說話的是我,安娜,我從來就沒有騙過你。我太愛你了,不會欺騙你。」
「愛」這個字軟化了無名氏先生的鐵石心腸,衝動之下他決定要讓步。「好吧,」他說,「我會吃藥,可是妳得要再親我一次。同意嗎?不過這一次得是貨真價實的吻,吻在嘴上。」
安娜微笑,接著再次彎腰,不偏不倚吻在他唇上,吻了足足三秒鐘,並不是蜻蜓點水,即使沒有用上舌頭,這種親密的接觸也讓無名氏先生的身體竄過一陣興奮。等安娜挺直腰的時候,他已經拿起藥丸在吞了。
這時兩人並肩坐在床沿,餐車在他們面前,無名氏先生喝下柳橙汁,咬了口吐司,又啜了口茶,安娜用左手輕輕幫他按摩背部,低聲哼著一首歌,他聽不出是哪首歌,但他知道這首歌他很熟,至少以前很熟。接著他開始對付水煮荷包蛋,用湯匙戳開一個蛋黃,舀起了一匙蛋黃和蛋白,往嘴裡送,可是就在這時他卻發現自己的手在發抖,他迷惑極了。這不僅是輕微的顫抖,而是明顯的驟發性抽搐,他完全無力控制。在湯匙離開碗六吋時,他抽搐得太過嚴重,大半的蛋黃蛋白都撒在托盤上了。
「要不要我餵你吃?」安娜問道。
「我是怎麼了?」
「別擔心。」她答道,拍拍他的背,想要安慰他。「這只是吃了藥的自然反應,過幾分鐘就沒事了。」
滿了鬼魅般生物和破碎記憶的迷霧國度中,搜索枯腸要找到糾纏著他不放的問題答案。
老人坐在窄床床沿,雙手置膝,掌心朝上,低垂著頭,瞪著地板,絲毫不覺上方有架攝影機。每隔一秒快門就喀嗒一聲,與地球自轉一周同步,攝製出八萬六千四百張靜止的畫面。即使他知道自己被監視了,也沒有什麼差別。他的心思不在這裡,而是擱淺在腦海中的想像世界,絞盡腦汁想要解開糾纏著他不放的問題。
他是誰?在這裡做什麼?是幾時到的?又要待多久?運氣好的話,時間會為我們揭開謎底。目前,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是仔細研究這許多的照片,盡量不要太早下定論。
房間裡有不少東西,而且每樣東西的表面都貼上了白色膠帶,上頭都用粗體字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