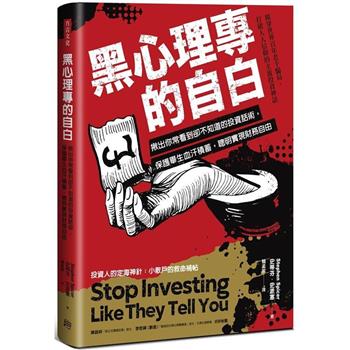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文壇才女最新好評力作!
達達的馬蹄無情地輾過成長中的少女肉身,
使她們懂得了情是什麼,世故的代價是什麼……
【名作家】鍾文音◎專文導讀
我們在危顫的繩索上漫舞,
小心翼翼不墜下腳底的深谷。
支撐著勇氣與堅持的,
是你為我們書寫的純真……
十八世紀末,動盪的風暴騷亂著整個歐洲。法國正舉起革命的大旗,而英國喬治王朝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就在這人心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凱勒維家族的大家長湯瑪斯為了生計,決定舉家搬遷到倫敦,投靠馬戲團,以木工糊口。但他卻沒想到,這次搬家的決定,也將為他的孩子帶來如同馬戲表演般高潮迭起的人生。
湯瑪斯的小兒子傑姆,一到倫敦就對古靈精怪的鄰家女孩梅格懷著微妙的情愫。他們常常一起去拜訪住在附近的威廉.布萊克先生,風趣幽默的布萊克先生以印刷維生,也是一名詩人,他會唸他寫的詩給不太識字的傑姆和梅格聽,並且引導他們純真的心靈,去看這廣大又複雜的世界。
然而,法國大革命的火焰越燒越猛,倫敦街頭擁護王權的勢力也愈演愈烈。堅持獨立思考與開放心靈的布萊克拒絕為「擁王」的言論背書,也使他被視為異端分子,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脅!傑姆與梅格決定離開混亂的倫敦,但等在他們前面的,有衝突、有和平、有美好,也有醜陋,而他們也將在這個燃燒的時代裡,從純真的孩子,逐漸轉為世故的大人……
繼一鳴驚人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後,擅長為文學、藝術與歷史翻案的文壇才女崔西.雪佛蘭,再次透過一對少年男女的成長,細膩呈現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動亂下,社會的氛圍與人心的變遷,並將被譽為「人類靈魂的揭密者」的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的經典詩作,巧妙地融入情節中,配合雪佛蘭溫婉卻力道十足的筆觸,使《純真之書》不僅是動人的小說傑作,更宛如一部大時代的人性浮生錄!
作者簡介:
崔西.雪佛蘭(Tracy Chevalier)
一九六二年出生於美國首府華盛頓,一九八四年遷居英國。一九九四年她獲得英國東安哥拉大學創意寫作碩士學位。
崔西的作品一貫以舊時代女性試圖突破環境限制、改變自身命運為主題,細膩敏銳,深刻動人。她的處女作《純藍》即為她贏得了「W.H.史密斯文學獎」的年度最佳新人獎,而《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則是她備受讚譽的代表作,全球熱賣直逼三百四十萬冊,並被改編拍成電影,贏得奧斯卡獎提名,既叫好又叫座。她另著有《天使不想睡》、《情人與獨角獸》。
崔西目前與丈夫及兒子定居於倫敦。
譯者簡介:
林立仁
1972年生於台北。英國薩里大學企管研究所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工作,譯有《日落之後》、《夢想教室》、《血宴》等書。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好評推薦︰
一本充滿生命複雜度的小說……崔西‧雪佛蘭筆觸細膩,擅於捕捉舊日年代的場景、氣味和聲音。──【芝加哥太陽報】
崔西‧雪佛蘭做了罕見的人物安排,鮮活地描寫各個人物,讓讀者可以輕鬆愉悅地閱讀書中故事。──【圖書館期刊】
崔西‧雪佛蘭是描述細節和描繪畫面的高手!──【泰晤士報】
崔西‧雪佛蘭是才華洋溢的作家!──【每日郵報】
崔西‧雪佛蘭筆下描繪的青少年生命力十分生動細膩……在威廉‧布萊克二百五十週年誕辰紀念前夕,假如她成功地將布萊克介紹給新世代的青少年認識,那麼也算是達成了非凡的成就!──【波士頓環球報】
一場視覺饗宴!──【泰晤士報】
崔西‧雪佛蘭最擅長把昔日時光的日常生活描寫得栩栩如生!──【《ELLE》雜誌】
十八世紀倫敦的粗陋與優雅如同不和諧音般地從書頁中流洩而出。──【《書單》雜誌】
精彩生動地描繪出十八世紀的倫敦!──【《暫停》雜誌倫敦版】
崔西‧雪佛蘭喚回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倫敦勞工生活氣味。──【娛樂週刊】
媒體推薦:好評推薦︰
一本充滿生命複雜度的小說……崔西‧雪佛蘭筆觸細膩,擅於捕捉舊日年代的場景、氣味和聲音。──【芝加哥太陽報】
崔西‧雪佛蘭做了罕見的人物安排,鮮活地描寫各個人物,讓讀者可以輕鬆愉悅地閱讀書中故事。──【圖書館期刊】
崔西‧雪佛蘭是描述細節和描繪畫面的高手!──【泰晤士報】
崔西‧雪佛蘭是才華洋溢的作家!──【每日郵報】
崔西‧雪佛蘭筆下描繪的青少年生命力十分生動細膩……在威廉‧布萊克二百五十週年誕辰紀念前夕,假如她成功地將布萊克介紹給新世代的青少年認識,那麼也算是達成了非凡的成就!...
章節試閱
一七九二年,三月
第一部
一
在熙熙攘攘的倫敦街道上,坐在一輛停於路邊的貨車裡,車上堆滿全家的家當,毫無遮掩展現在好奇的路人眼前,算得上丟臉的事。傑姆‧凱勒維坐在一張高聳的溫莎椅旁,那張溫莎椅是他父親幾年前替家裡做的。一名路人公然探看貨車上的物品,傑姆只是怔怔望著那人。驀然間看見這麼多陌生人,同時又暴露在這麼多陌生人的視線與打量下,傑姆感到不自在。在他老家多塞特郡村子裡,出現一位外地人就算得上大事一件,可以讓村民討論個好幾天。傑姆把身體往各類家當裡縮,盡量不讓自己引人側目。他體格瘦長結實,臉面狹長,藍色眼眸,眼窩甚深,一頭沙金色鬈髮垂至耳下,長相並不惹人注意,路人多半只往貨車上的家當瞧,難得看他幾眼。路過一對男女甚至停下腳步,伸手把貨車上的物品拿起來看,彷彿站在滿滿一車洋梨前頭,挑揀看看哪顆最成熟。車上一只袋子破了個口,一件睡衣的摺邊冒了出來,那女子便伸出手指觸摸。那男子拿起湯瑪斯‧凱勒維的一把鋸子,測試鋸齒是否鋒利。即便傑姆大喊一聲:「嘿!」,那男子依然故我,慢條斯理地放下鋸子。
貨車上除了裝載許多椅子外,大部分物品都是傑姆的父親的生財工具。傑姆的父親專門製作溫莎椅,工作器具包括:用來折彎木料以製作扶手和椅背的木箍、用來旋轉椅腳的車床組裝部件、以及各種各樣的鋸子、斧頭、鑿子、螺旋鑽。湯瑪斯‧凱勒維的這些工具佔據貨車太多空間,以致從蓽托川畔村前往倫敦的一星期路程中,凱勒維家族的成員必須輪流下車跟隨貨車步行。
載送凱勒維家族的貨車停在艾斯雷馬戲場前,貨車由史瑪特先生駕駛,他雖是蓽托谷在地人,卻充滿探險精神。湯瑪斯只約略知道該去哪裡找菲力浦‧艾斯雷這個人,但對於倫敦究竟有多大則毫無所悉,還以為倫敦就跟多徹斯特鎮差不了多少,只要站在鎮中央,就可以瞧見艾斯雷馬戲團所演出的馬戲場。幸而艾斯雷馬戲團在倫敦素負盛名,他們問了幾次路就來到西敏橋頭一座偌大的建築物前。那座建築物呈圓形,圓錐形木造屋頂尖尖拔起,正門處矗立著四根裝飾用圓柱,屋頂插著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子,一面以紅字寫著「艾斯雷」,另一面以黑字寫著「馬戲場」。
傑姆盡量不去理會好奇的旁觀路人,雙眼凝視路旁一條大河和西敏橋。剛才史瑪特先生決定去那條大河邊上逛逛,口中說:「我去瞧瞧倫敦長什麼樣子。」西敏橋的拱型橋身跨越河水,遠遠可見橋的另一頭是座由許多方塔組成的大型建築物與西敏寺的尖塔。傑姆在多塞特郡見過的河只有弗蘭姆河和蓽托河,弗蘭姆河約有鄉間小路那麼寬,蓽托河更是一躍便能跨過,和眼前的泰晤士河根本無法相比。泰晤士河河面寬廣,波瀾壯闊,棕綠色河水隨著遠處海潮的牽引起起伏伏。河面與橋面上交通繁忙,泰晤士河上有各種船隻往來,西敏橋上則有四輪馬車、貨車、行人絡繹不絕。傑姆從沒見過這麼多人,即使多徹斯特鎮的市集日也沒這麼多人。由於眼前活動中的物體太多,只看得他眼花撩亂,難以仔細辨識。
傑姆雖然和史瑪特先生一樣興起下車去河畔逛逛的念頭,卻不敢離開玫希和母親身邊。玫希‧凱勒維一臉迷惘,左顧右盼,手拿一條手帕直往臉上搧。「老天,三月天怎麼會這麼熱。」她說:「在我們老家沒這麼熱的,傑姆你說對不對?」
「明天一定會涼快下來。」傑姆肯定地說。玫希雖然比他年長兩歲,但他總把玫希當妹妹看待,認為玫希需要他的保護,以免這個多變的世界傷害到她,儘管在蓽托谷並沒有什麼危險可言。不過來到倫敦,他要保護玫希的任務便顯得更加艱鉅。
安‧凱勒維和傑姆一樣望著泰晤士河,視線落在一艘小船上正用力划槳的男童身上。那男童對面坐著一隻狗,那隻狗因為天氣炎熱而張嘴不住喘氣。船上載的除了那個男童外就只有那隻狗。傑姆知道母親的視線隨著那男童移動時,心裡想著的是他哥哥湯米。湯米愛狗,身後總有村裡一隻狗跟著他。
湯米‧凱勒維面容俊俏,愛做白日夢,常令父母不知如何是好。湯米從小就看得出不是塊能成為椅匠的料,他對木料和木料可製成的物品絲毫不感興趣,對於父親教他使用的製椅工具也興趣缺缺。他會拿著螺旋鑽,轉著轉著轉到一半就停下來,或在車床旋轉時放任車床越轉越慢,望著柴火或不遠不近處發呆。他這種性格是從父親那兒遺傳來的,只是並未遺傳到再次把注意力收回到工作上的能力。
儘管湯米有這麼一個缺乏工作能力的性格,而且這種性格通常會讓安瞧不起,但安卻特別鍾愛湯米這個兒子,連她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也許她覺得湯米比較欠缺能力,所以也比較需要她吧。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安喜歡有湯米陪伴,只有湯米可以令她開懷大笑,然而自從六個星期前,她在自家後院發現湯米陳屍在洋梨樹下後,她的笑聲便隨之死去。那天湯米爬到一棵洋梨樹上,一定是想去摘樹上僅剩的一顆洋梨。那顆洋梨正好長在難以搆到之處,一整個冬天都在挑逗他們一家人,儘管他們都知道那顆洋梨暴露在寒冬中,應該早就走味了。湯米爬上樹枝,不料樹枝斷折,使他跌落地面,摔斷頸骨。每當想起湯米,安總覺得胸口如有椎擊。這時,安望著小船上的男童和狗,胸口再次感到椎心之痛,即使是初次造訪倫敦的新奇感也無法抵銷這種苦痛。
二
湯瑪斯往馬戲場正門走去,經過正門前方那四根高大的圓柱時,只覺得自己非常渺小,心下不禁膽怯起來。他個頭小,身形瘦,留著一頭濃密鬈髮,有如(犭+更)犬身上的捲毛,頭髮剪得極短,幾乎貼著頭皮。馬戲場正門相當宏偉,相襯之下,他的存在顯得微不足道。他把家人留在外頭街上,走進正門,卻發現大廳幽暗無人。耳中聽得沉重的馬蹄聲和尖銳的馬鞭聲從一處通道傳來,他循聲而去,走進表演廳。只見表演廳內是一排排長椅,他在長椅間停下腳步,目瞪口呆望著表演圈。表演圈內有幾匹馬正放蹄奔馳,馬上的騎師卻非安坐在馬鞍上,而是直挺挺站立著。表演圈中央站著一名年輕男子,手中馬鞭揮得噼啪作響,口中呼喝著前進方向。一個月前,湯瑪斯在多徹斯特鎮曾看過相同的騎術特技,如今再看,依然看得他瞠目結舌,驚詫於那幾名騎師竟能再次使出相同特技。一次的成功或許可說是僥倖得手,兩次的成功顯然是真有本事。
表演圈周圍環繞著許多包廂和一個貴賓席,以木材架構而成,裡頭設有椅子可坐,也有空間可以站立。表演圈正上方垂掛著一盞大吊燈,共有三層,以馬車車輪製成。高高的圓形屋頂開著百葉窗,讓陽光灑落進來。
湯瑪斯並未望著那些騎師太久,正當他呆立於長椅間,一名男子走來問他有何貴幹。
「我想來見艾斯雷先生,不知他肯不肯見我?」湯瑪斯答道。
前來和湯瑪斯說話的男子是艾斯雷的助理,名喚約翰‧福斯。他唇上蓄著兩撇長長的八字鬍,眼皮看起來十分沉重,平常他的眼皮都半垂著,只在表演場上發生慘事時才會完全張開。在艾斯雷身為馬戲巨擘的漫長生涯中,至今他的馬戲團已發生過幾件慘事,未來還會再發生幾件。對福斯來說,湯瑪斯的突然出現稱不上慘事一樁,因此福斯的眼皮依然半垂,木無表情地瞧著眼前這來自多塞特郡的男子。有人求見艾斯雷是常有的事,福斯早就習以為常。福斯擁有過人的記憶力,相當勝任助理這份工作,此時他立刻記起上個月曾在多徹斯特鎮見過湯瑪斯。「到外頭去吧,」福斯說:「說不定他晚點會見你。」
福斯無精打采的眼神和意興闌珊的回答,讓湯瑪斯大惑不解,但湯瑪斯還是退了出去,回到馬車上的家人身邊。為了把一家人帶來倫敦,湯瑪斯已經用盡盤纏,眼下已無處可去。
凱勒維家族世世代代定居於多塞特郡蓽托谷,以製椅維生,算來已有好幾個世紀,沒人料得到,到了湯瑪斯這代,凱勒維家族竟會舉家遷往倫敦,而最感意外的莫過於湯瑪斯自己。在遇見艾斯雷之前,湯瑪斯一直過著平凡的生活。他的製椅技術傳承自父親,父親去世後他便繼承製椅工坊。他的妻子是父親的伐木匠摯友的女兒,他和妻子之間除了笨拙的床笫之事外,就和兄妹沒兩樣。他們夫婦都是從小在蓽托川畔村長大的,婚後也一直住在村裡。兩人生了三個兒子,山姆、湯米、傑姆,還有個女兒玫希。湯瑪斯一星期有兩天晚上會去五鐘酒館喝酒,每星期日固定上教堂,每個月固定上多徹斯特鎮一次。他沒去過距離蓽托川畔村十二哩外的海邊,也從未表示有興趣花個幾天路程,前去參觀位於威爾斯市或沙利斯伯立或溫徹斯特的教堂,或是前往浦爾鎮或布里斯托或倫敦,不像酒館裡其他人偶爾會把這種願望拿出來說。他去多徹斯特鎮純粹為了工作,只要接了製椅委託、買了木料,便打道回府。他寧可走夜路回家,也不喜歡在多徹斯特鎮的客店留宿,花錢買醉把錢用光。相較之下,他覺得走夜路來得安全多了。他為人親切,在酒館裡說話從不大聲。對他來說,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在車床上旋動椅腳,或是專心在木料上刻出細小溝槽或弧面,有時他甚至會忘記自己正在做椅子,只是靜靜欣賞木材的紋理、色澤和質地。
這便是湯瑪斯原本的生活,也是他原本被期望去過的生活,直到一七九二年二月,這種生活才告中斷。那時艾斯雷的馬術特技隊在多徹斯特鎮表演數日,正好是湯米摔落洋梨樹後兩個星期。艾斯雷馬戲團結束了英格蘭西南部冬季巡迴表演,從都柏林和利物浦返回倫敦,順道停留多徹斯特鎮。儘管艾斯雷馬戲團透過《西部快郵》這份報紙做了大肆宣傳,張貼海報、分發傳單、廣為宣告,但湯瑪斯照例前往多徹斯特鎮那天,絲毫不知艾斯雷馬戲團到了鎮上。他駕著貨車和傑姆一同運送八張高背溫莎椅前往多徹斯特鎮,傑姆正在學習製椅這門生意,如同湯瑪斯一樣繼承父親衣缽。
傑姆幫忙從貨車上搬下椅子,然後觀看父親在言談舉止中如何對買主不失禮數,同時充滿自信,這是製椅這行必備的應對態度。交易完成後,買主十分滿意,多給了一枚克朗,湯瑪斯收進口袋。「爸,」這時傑姆開口:「我們可以去看海嗎?」多徹斯特鎮南部一座山丘可以看見五哩外的海洋,傑姆曾在那座山丘上看過幾次海,很希望有天能真正去海邊。他常站在蓽托谷谷頂的草原向南遠眺,暗自希望阻隔在中間的層層丘陵突然移位,讓他看一眼那條延伸至世界各個角落的湛藍水平線。
「不行,我們最好回家了。」湯瑪斯無意識地回答,卻瞥見傑姆臉上的神色頓時黯淡下來,猶如窗帘給拉了起來。湯瑪斯隨即後悔自己如此回答,同時憶起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短暫時光,熱切地想看、想接觸新事物,想脫離一成不變的慣例。後來隨著年齡增長,他必須扛起家庭的擔子,只好把心收回,接受現實,在蓽托川畔村過著安分守己的生活。有天,傑姆也必須接受現實,長大成人就是這麼回事,然而此時湯瑪斯卻對傑姆感到不捨。
湯瑪斯並未多說什麼。兩人駕車經過鎮郊瓦爾河畔時,見青草地上矗立著一座圓形木造建築,屋頂以帆布蓬搭成,一名男子站在路旁拋耍火炬,吸引客人。湯瑪斯摸摸口袋裡那枚買主多給的一枚克朗,撥轉馬頭,駛向青草地上。這是他生平頭一次做出意料之外的舉動,他覺得心中某個地方似乎稍微鬆動了,猶似早春池塘的寒冰迸出一道裂縫。
那天晚上湯瑪斯和傑姆回到家裡,大談他們見到的雜技表演,以及他們和艾斯雷本人碰面的經過,這讓湯瑪斯比較可以面對安的嚴厲眼色。安的眼神似乎在譴責他,兒子屍骨未寒,你竟敢跑去享樂?「他說我可以去倫敦替他工作,」湯瑪斯對安說:「我們可以展開新生活,遠離……」話說到這裡卻未說完,也不必說完,他們夫妻倆同時想到湯米在蓽托川畔村墓園的墳墩。
但安的回答卻令湯瑪斯驚詫萬分。湯瑪斯其實並未認真考慮要去倫敦替艾斯雷工作這件事,沒想到安竟直視他的雙眼,點頭說:「好,我們就去倫敦。」
三
凱勒維一家人在貨車上等了半小時,就見到了艾斯雷本人。艾斯雷除了是馬戲團老闆、特技表演設計者,也是流言蜚語的主角、奇才異能之士的磁石、地主、當地店家的老主顧,總之是個五顏六色的誇張人物。他身穿一件紅色外套,那是多年前他擔任騎兵隊隊員的制服,像是巴不得人人知曉此事。外套滾金邊,配上金釦子,但只扣了領口的釦子,露出渾圓的肚腩包裹在扣上釦子的白色背心裡。褲子同為白色,足蹬一雙長靴,靴上的皸裂紋蔓延至膝部。他全身上下只有一樣衣物和尋常百姓一樣,便是頭上那頂黑色大禮帽。只見他不停舉帽,向他認識的以及想認識的女士致意,福斯則在他身後亦步亦趨。艾斯雷快步走下馬戲場階梯,邁開步伐來到貨車前,舉帽向安致意,伸手和湯瑪斯握了握,又對傑姆和玫希點點頭,高聲說:「歡迎,歡迎!」話聲豪爽歡快。「很高興再見到你!來倫敦的路上想必你們一定欣賞了美麗的風景,你們是從得文郡來的吧?」
「是多徹斯特鎮,」湯瑪斯更正:「我們住在多徹斯特鎮附近。」
「對,多徹斯特鎮,很不錯的城鎮。你是在多徹斯特鎮做桶子是不是?」
「椅子。」福斯在旁低聲提醒。這就是他老跟在艾斯雷身邊的原因,為的是給予老闆適時提醒。
「啊,對,椅子。有什麼我能為你們效勞的嗎?先生,女士?」艾斯雷向安點點頭,隨即不自在了起來。安在貨車上坐得直挺挺,一雙眼睛牢牢盯著步上西敏橋的史瑪特先生,緊閉的嘴唇猶如抽繩袋袋口,全身上下每一吋部位都明白表示自己不想待在這地方,也不想和艾斯雷有任何瓜葛。這就是艾斯雷之所以感到不自在的緣故,他名頭響亮,不知有多少人想蒙他青睞,但這也養大了他的胃口。眼前竟然有人對他不理不睬,令他立刻想獲得安的注意力。「告訴我,你們需要什麼,我就給你們什麼!」艾斯雷手臂一揮,補上一句,只是安的眼光仍舊留在史瑪特先生身上,完全沒留意艾斯雷的動作。
自從貨車離開凱勒維家族位於多徹斯特鎮的小屋那一刻起,安就開始懊悔。過去一星期來,貨車行駛在早春的泥路上,隨著車子離倫敦越來越近,她內心的懊悔也越來越深。原本她希望來到倫敦可以讓自己忘卻湯米的死,但此時她坐在馬戲場前的貨車裡,對艾斯雷視若無睹,心裡清楚知道自己並未忘記湯米,甚至心裡想的全都是湯米,而且身處倫敦的事實不斷使她記起自己想逃離的是什麼。不過她寧可把自己的不幸全都怪罪在丈夫和艾斯雷身上,也不願思及湯米為什麼那麼傻,要爬上那顆洋梨樹。
「艾斯雷先生,」湯瑪斯開口說:「上次你邀請我來倫敦,現在我很高興接受你的邀請。」
「有嗎?」艾斯雷望向福斯,問道:「福斯,我邀請過他嗎?」
福斯點頭說:「有的,艾斯雷先生。」
「哦,艾斯雷先生,難道你不記得了嗎?」玫希傾身向前,高聲說:「我爸什麼都告訴我們了,他說他跟傑姆去看你們的表演,有個人拿了把椅子在馬背上耍特技,結果椅子折斷了,我爸當場就幫你把椅子修好了。還有,你跟我爸聊了些木頭和家具的事,你以前當過家具木匠,對不對?」
「噓,玫希,」安把視線從西敏橋上收回,轉過頭插嘴說:「人家可不想聽這些事。」
艾斯雷凝視眼前這個纖瘦的鄉下小姑娘,坐在貨車上繪聲繪影講了這麼一段故事,當場輕聲笑說:「小姑娘,聽妳這麼一說,我倒是想起來有過這麼回事,可是這跟你們來到這裡有什麼關係?」
「你跟我爸說,只要他願意,就可以來倫敦找你,你會幫他安排工作。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來倫敦,現在也才會在這裡。」
「原來如此,玫希,你們一家人都來了。」艾斯雷望向傑姆,估量傑姆大約十二歲,很適合在馬戲團裡打雜幫忙,便問道:「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傑姆。」
「小傑姆,你旁邊那些是什麼椅子?」
「是溫莎椅,都是我爸做的。」
「很漂亮,很漂亮。傑姆,你可以幫我做幾把溫莎椅嗎?」
「當然可以,艾斯雷先生。」湯瑪斯說。
艾斯雷的眼光飄移到安身上,說道:「那我就跟你們訂一打椅子。」
安聽見艾斯雷一口氣訂這麼多張椅子,不禁全身僵直,但儘管如此,仍舊正眼也沒瞧他一下。
「福斯,現在我們有哪些房子沒人住?」艾斯雷傲然問道,他在蘭貝斯區擁有為數可觀的房產。蘭貝斯區在艾斯雷馬戲場附近,位於倫敦市區對面,就在西敏橋另一頭。
福斯嘴唇略張,唇上兩撇八字鬍跟著抖了抖說:「只有裴罕小姐的海克力斯樓有空房,可是她向來親自挑選房客。」
「沒關係,她會挑中凱勒維這家人,他們會是好房客。福斯,你現在就帶他們過去,順便叫幾個小夥計過去幫忙搬行李。」艾斯雷再次舉帽向安致意,又和湯瑪斯握了握手說:「你們如果有什麼需要,儘管跟福斯說就行了,歡迎來到蘭貝斯!」
一七九二年,三月
第一部
一
在熙熙攘攘的倫敦街道上,坐在一輛停於路邊的貨車裡,車上堆滿全家的家當,毫無遮掩展現在好奇的路人眼前,算得上丟臉的事。傑姆‧凱勒維坐在一張高聳的溫莎椅旁,那張溫莎椅是他父親幾年前替家裡做的。一名路人公然探看貨車上的物品,傑姆只是怔怔望著那人。驀然間看見這麼多陌生人,同時又暴露在這麼多陌生人的視線與打量下,傑姆感到不自在。在他老家多塞特郡村子裡,出現一位外地人就算得上大事一件,可以讓村民討論個好幾天。傑姆把身體往各類家當裡縮,盡量不讓自己引人側目。他體格瘦長結實,臉面狹長...
推薦序
成長之歌 ----由純真走向世故的幻滅與超然
@(作家)鍾文音
我一直喜歡少男少女的成長或冒險故事,因為那是走向世故後我們所失去的某種純真野性……。
提起崔西.雪佛蘭,也許中文讀者未必認識,不過提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一書,大概就有印象,至少有機會看過改編的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以荷蘭十七世紀畫家維梅爾同名畫作裡的模特兒為主角,竟致演繹出一本動人且因之瞅著心的惆悵故事,敘述文字富含如油畫般濃烈的視覺與繪畫感,以小說還原歷史,魅力十足;題材以小見大,創意處處。
雪佛蘭這回把小說新作《純真之書》「原名《Burning Bright》」定調在十八世紀的倫敦,同樣擷取歷史謎樣人物為主軸,這次登場的人物是兼具印刷工、詩人與激進份子的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所以首先得對威廉布萊克有些輪廓的認識或許比較容易進入本書的核心。威廉布萊克(1757--1827)是英國備受爭議又具開創性的詩人、畫家和版畫家。他的一生中有許多事蹟甚至是無法具體定位的,布萊克被認為在詩歌和視覺藝術上開啟了歐洲浪漫主義時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曾在其「預言詩」裡大量使用詩歌體英語(雪佛蘭在這本書裡也大量延用)。在其視覺藝術的成就上,甚至有藝術評論家認為布萊克是英國最偉大的藝術家,倫敦是他的整個生命舞台,他的作品具有多樣化的象徵性和豐富的語言,後代評論家對他仍是高度評價,認為他的作品最大特色即是是注入了哲學和神秘性。他曾寫過《上帝之身》(the body of God,《人類的生存本身》(Human existence itself)等著作,對英國人而言布萊克是歷史上象徵理想和抱負的謎樣啟示性人物。布萊克的特殊經歷使他在歷史上難以歸類,「一個不搶先前人,也無法被歸類為同時代的人。」所以他是一個獨立於時代之上的人。
雪佛蘭以他為故事核心,等於他是少年少女的心靈導師,也是整本書的重量之所在。
小說的故事時間僅僅發生約一年時光:從一七九二年三月到一七九三年七月,這一年對書中許多的少男少女而言卻是一個「成年禮」的年份,他們被迫在純真與世故之間徘徊,進而迎擊際遇,一年如斯漫長。
扮演少男少女心靈成長指引人物即是布萊克,也是他將「純真與世故之歌」這兩本書送給書中的兩個主角:傑姆與梅格。
故事從少年「傑姆」隨著木匠父親湯瑪斯全家離開老家來到倫敦開始敘述,湯瑪斯回憶起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熱切想接觸新事物的短暫時光,此時巧遇艾斯雷馬戲團來到小鎮表演,團主艾斯雷邀請湯瑪斯到倫敦,艾斯雷隨意誇口承諾湯瑪斯抵達倫敦後可以幫他們安排生路。這讓湯瑪斯黑暗的心頓時燃亮了,因為不久前他的孩子湯米為了摘梨子而從樹上高處墜落致死,妻子安一直沈浸在悲傷裡,離開傷心地,前往倫敦像是他們快溺斃的生活浮木。於是湯瑪斯全家就這樣出發前往大城市了,離開了世代打造「木椅」的老家。
然而前往倫敦的路途,安就後悔了,她發現離開並無法去除她對愛子湯米的懷念。同時抵達倫敦見了艾斯雷後,她對這個馬戲團這個男主人的霸氣等行徑感到嫌惡,臉上始終冷漠。那裡知道安的表情卻擊中了艾斯雷的好奇心思,他想這裡人人對他處處逢迎,而眼前這個女人卻極其冷淡,他頓時發生了興趣,於是幫原本在他腦中搜尋不到這家人名字的求助者安排住到海克力斯樓十二號。
就這樣,少年少女的冒險故事就在此展開了。
總是注意海克力斯樓搬來新房客的少女梅格登場,這個滿腦子鬼靈精與小聰明少女很快地就對男孩傑姆產生好感,接著他們遇見了鄰居布萊克,走入了布萊克印刷「書」的世界,布萊克給他們兩本書,分別是《純真之歌》與《世故之歌》,布萊克讓他們認識了世界的對立面與統合面,他們在心中想著許多事物的對立面,比如鄉下與城裡是對立,純真對立於世故?傑姆與梅格這麼想著。但布萊克卻說:假如純真是河的這岸,世故是河的那岸……「那麼河的中間是什麼?」
成長中的孩子又問布萊克為何要將西敏寺的雕像畫成「裸體」?「我畫的不是那尊雕像,我無法忍受實物素描……練習素描讓我學到很多,其中我學到的是,一旦你知道事物的表面,就不需要在那裡繼續流連,可以看向更深一層,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畫實物,因為太過侷限,扼殺了想像力。」
布萊克這段話,一直到小說的後來,梅格才搞懂,但付出了很大的成長代價。
原本以為小說會安排驚險的橋段是發生在艾斯雷與安之間,畸戀或者外遇之類的驚悚情節,恰好相反的是,小說很快就從成人的支線跳到少女主線---馬戲團的風流男人約翰企圖染指安的女兒玫希。和玫希要好的梅格洞悉約翰企圖,她一路要哥哥查理和她一起去察看約翰和玫希到底會做出什麼事來。他們兄妹兩就躲在稻草堆裡看著約翰退去玫希的衣物,兩人看得眼紅心跳卻無意要跳出來阻止的樣子(這裡似乎看出了梅格的世故面,她為何初始大舉正義之旗亦步亦趨地跟著,到了現場又為何卻眼睜睜地屈服於眼前施暴的男子,竟立在窗外跟著好奇觀看而沈默……),最後還是約翰發現外面有人在偷窺,兩人只好被迫出來面對玫希,梅格卻無力挽救胸衣已退到一半的玫希,約翰說玫希是自願的,怒指他們來破壞。被罵開的梅格一直在想著玫希的表情,她想自己究竟是對的還是錯的?於是她決定求救布萊克,由布萊克趕去阻止約翰。
小說在後段出現的高潮全環繞在梅格與玫希的情誼,梅格後來還變賣了以前查理搶來的銀匙(小說可惜在這裡模糊一帶:梅格殺過輕挑於她的男人。這時的她是世故還是純真?是為了心中的救贖抑或出於幫助眼前的好友?小說有許多可供思考的延伸介面),她買了驛票,護送半被迫半迷糊自願下而懷孕的玫希返回老家,這有如是少女版的《湯姆歷險記》,只是湯姆少男的尋寶記到了少女版則轉成了「未婚生子」的歷險種種。
要知道這小說的故事時間是十八世紀的倫敦,那時倫敦是什麼樣的大城市?法國大革命在倫敦對岸燃燒,革命者如火如荼挑釁當權者,斷頭臺上暴力血腥成河,街頭暗巷處處有妓女,酒館夜夜有買醉的沈淪者,而小說的主軸圍繞在馬戲團與一棟公寓,馬戲團即是一個城市「大隱喻」,海克力斯樓則是「浮世」人生進進出出的象徵,主宰與被主宰者,沈淪與清醒者都在其中仰息,強者弱者互為交構與對立,純真者被迫提早世故化,大城市永遠是成長的最佳催化劑,要堅強活下去,要看盡千帆浮沈才能建構自己的往後世界,其中在這個藏污納垢的世界能活得最好的人即屬梅格,她代表著具有雙重面向者往往是活得最好的人,這似乎是雪佛蘭的隱喻。而玫希則代表著「純真的幻想者」,她只是多次看約翰馬戲團的表演與他駕馭馬的樣子就被吸引了。而我以為少年傑姆則是兩邊都談不上的人,他表面看是純真的,但他沒有縱身一躍好讓自己成長的勇氣,不論身處倫敦或是和梅格的曖昧情愫他都是模糊且旁觀的,在小說裡也沒有太多深刻的描寫,他僅是在岸上看著這一切,他很像布萊克所說的那種「在河中間」的人。
我以為這本小說最妙的人物穿插是布萊克夫婦,因而小說裡也處處有「詩歌」唱頌,幾乎可以感覺雪佛蘭為小說鋪呈的「聲音與影像」魅力,也增添雪佛蘭一向在小說裡「謎樣」的情調,真實歷史人物與小說虛構情節的互為交融。
附帶一提,不蠻讀者的是我讀這本小說有自我投射,讀這本小說末段與結尾時簡直是驚叫連連,直呼好巧好巧。因為我也曾寫過類似這樣的成長小說。小說裡的「我」和一個高中少女好友蹺課,結果在那一日發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我」目睹了好友被男人強暴的現場和梅格目睹玫希的現場竟有著同樣驚險與誘惑等張力書寫。如果有興趣或可讀讀我的短篇小說:(想你是這樣的) 「收錄在《過去》一書,大田出版。」這可稱為台版南方的少女成長小說。
這也是為何我要推薦雪佛蘭這本好看的小說了。
同時「純真」與「世故」也一直是燃燒我內心黑暗的兩個拉扯面向,從而我學習到,燃燒是為了破暗,以指引明亮之所在。
小說結尾石破天驚的一叫是玫希迎接子宮那強烈收縮襲來的呼喚,梅格卻在眾人身後看著玫希這一幕,她知道她的任務完成了。
小說最出色的書寫是指出「純真與世故是多麼登對」,沒錯,僅只「純真」將讓人生陷於無聊與無知之境,僅只「世故」也易讓人生陷於過熟與冷酷之險。
很難單獨解析的成分,因為人一旦成長,意味著要被馴化,於是我們就要有準備流淚與獻祭肉身的可能了。但這本小說結尾是光亮的:歷經痛楚與羞辱性經驗的玫希彷彿有著光亮的未來,一種燃燒過後的明亮。如布萊克所言:「一旦你知道事物的表面,就不需要在那裡繼續流連,可以看向更深一層。」
簡單的故事情節,韻味深遠的霧中風景,十八世紀驛車的達達馬蹄無情地碾過成長中的少女肉身,使她們懂得了情是什麼,世故的代價是什麼了。小說以安安靜靜的語言流過殘酷成長之路的聳動情節。
看向更深一層。
有如看一幅古老的油畫般,無數的細節,一筆一畫,覆蓋再覆蓋,小說人物的肌里隨之豐厚,情節沒有悲情,僅像西敏橋下的河水悠悠。
一部十八世紀的老電影在我的腦海裡一格一格地放映著。
成長之歌 ----由純真走向世故的幻滅與超然
@(作家)鍾文音
我一直喜歡少男少女的成長或冒險故事,因為那是走向世故後我們所失去的某種純真野性……。
提起崔西.雪佛蘭,也許中文讀者未必認識,不過提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一書,大概就有印象,至少有機會看過改編的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以荷蘭十七世紀畫家維梅爾同名畫作裡的模特兒為主角,竟致演繹出一本動人且因之瞅著心的惆悵故事,敘述文字富含如油畫般濃烈的視覺與繪畫感,以小說還原歷史,魅力十足;題材以小見大,創意處處。
雪佛蘭這回把小說新作《純真之書》「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