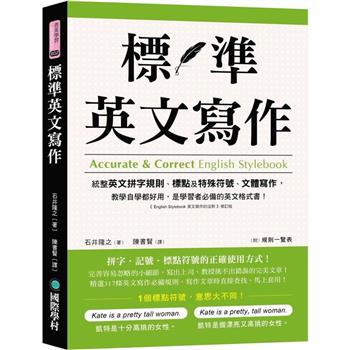如果妳愛上的不是「人」,
妳唯一能做的,就是成為愛人的「獵物」……
●最嚴酷的試煉,最兩難的愛情,最迷人的主角,統統都在《喚魔者》!
●亞馬遜書店讀者4.5顆星火熱推薦!
夜光猶如蜘蛛網,空氣閃閃發亮,
我在焚屋巷,在魔法的核心,在兩個世界的灰色地帶。
我分不清……你是迷魅的誘惑,還是恐怖的陷阱?
梅痛恨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她願意犧牲一切來讓自己變得不一樣,如此才能更接近那個迷人的危險份子……
在尼克一雙黝黑的瞳孔裡,梅望見迷霧的風暴,望見烈火焚燒的城市,即使震顫不已,仍然無法抗拒他足以毀滅一切的吸引力。但尼克身上流著惡魔的血液,根本不懂「愛」為何物。
而艾倫則是包覆危險核心的溫暖光暈,多年來他默默守護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弟,如今,他卻向梅表露愛意。然而梅很懷疑,艾倫要如何分散對弟弟的關注來守護她?
賽伯也許是梅脫離這一切的出口,他的外型酷似尼克,卻比他溫柔百倍,最重要的是,他跟梅一樣普通,都是人界的凡夫俗子。當賽伯對梅示好,她又怎能抗拒?
梅周旋在他們之間,卻漸漸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自從她從焚屋巷回來,命運就推著她一步步接近危險。當梅發現艾倫和賽伯其實各有各的盤算,她終於醒悟,自己是唯一能夠保護尼克的人。她要教他如何成為一個人類,而犧牲,則變成她示愛的手段……
作者簡介
莎拉.瑞絲.布列南Sarah Rees Brennan
土生土長的愛爾蘭人,在海邊長大。五歲時,莎拉想成為芭蕾舞者的夢想幻滅,開始跟祖父瞎掰她源源不絕的創意。七歲時,她已經寫出一個以小馬和忍者為主角的故事。當學校的老師想教她說流利的愛爾蘭語,她卻寧可在桌子底下偷偷讀書。這些書包括珍.奧斯汀、瑪格麗特.梅罕、安東尼.特洛普、羅賓.麥金莉、黛安娜.韋恩.瓊斯的作品。直到現在,她還是很喜歡這些書,並從中獲得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
大學畢業後,莎拉曾短暫居住在紐約。雖然她有攔下消防車搭便車的習慣,但她還是在這個城市生存了下來。她在英國攻讀創意寫作文學碩士時開始動筆寫作《喚魔者》首部曲《黑曜石的印記》,後來回到愛爾蘭,莎拉持續發展這個故事,並讓它成為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後不僅廣受讀者歡迎,更被製作《冥王星早餐》和《玩命911》的製片公司Parallel Films相中,計劃拍成電影,勢必將掀起一股「喚魔旋風」!
譯者簡介
楊佳蓉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現為自由譯者,背負文字橫越語言的洪流,在翻譯之海中載浮載沉。譯有《黑屋》(皇冠)、《馬雅預言書》系列(普天出版)、《早安,陌生人》、《下一頁,愛情》(三采文化)、《壁花姊妹秘密通信》(繆思)、《借物少女》系列(台灣角川)等書。
個人部落格:miaumiaumiau2.pixnet.net/blog


 2011/10/18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