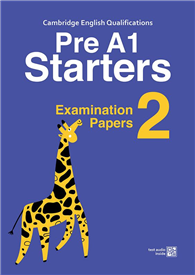榮獲法國文壇最高榮譽龔固爾文學獎!入圍衛普勒獎!
每一個字都是詩,
都將帶走你蓄積已久的憂鬱!
●「阿公帶我回家」電影原著作者最動人的代表作,即將搬上大銀幕!
●《追風箏的孩子》卡勒德.胡賽尼讀畢感動不已,主動寫信推薦!
那顆石頭將靜靜聆聽,
關於你的痛苦與憂傷,
關於你那無法言說的秘密心事……
小小的房間裡,女人默默照護著孱弱的丈夫。日升日落,她為他更換點滴、擦拭身體;日復一日,她隨著他的呼息而生活,幾乎要忘記自己。
這樣的日子不知道過了多久,丈夫甦醒的一天遙遙無期。筋疲力竭的女人終於發出抱怨:我受夠了!
男人一如往常,毫無反應,女人卻彷彿啟動了宣洩憤懣的樞紐,一發不可收拾。夢魘般的婚姻、不幸的童年、困厄的遭遇……隨著聲聲傾訴,女人逐漸釋放經年累月的苦痛。
於是她想起「耐心之石」的神話,那顆神奇的石頭,靜靜聆聽人們的不幸,如海綿般吸收所有秘密,直到它迸裂的那天,即是傾訴者解脫之日。
凝視著眼前的丈夫,女人震顫地微笑,她心愛的耐心之石原來就在眼前啊。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裡,她要喚出那個黑暗的自己,她要說出那些他一直以來都不知道的秘密……
一個美麗而暴烈的傳說,一個瀕臨崩潰的女人深埋心底的黑暗心事,阿提克.拉希米用美麗的文筆將它們串成《耐心之石》這部耀眼的小說,展演壓抑與釋放的華麗變奏,內斂深沉、跌宕曲折,字字句句透明而晶亮,微光般探照記憶的幽幽黑洞。而當我們被故事的結局深深震撼,才驚覺那些字句其實早已洗去我們不經意的悲傷與失落。
作者簡介
阿提克.拉希米 Atiq Rahimi
一九六二年生於阿富汗喀布爾,為了躲避蘇聯入侵,阿提克.拉希米逃亡至巴基斯坦,一年後,獲得庇護而移居法國。
阿提克進入索邦大學就讀,為了完成電影學位,他進入製片公司,替法國電視台製作了七部紀錄片與數支廣告。除了影像創作,阿提克也提筆寫作,但流亡異鄉的阿提克始終堅持要用母語波斯語創作,陸續完成了《土地與灰燼》、《夢與恐懼的一千個房間》、《想像中的歸鄉》等小說作品。阿提克並將《土地與灰燼》改編成電影「阿公帶我回家」,大受好評,獲得全球超過五十個影展邀請參展放映,一共囊括了二十五座獎項,更代表阿富汗角逐二○○五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入圍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耐心之石》是阿提克的第四本小說,也是他回到阿富汗之後的創作,並且是他首度以法文寫成的作品。文字簡潔細膩,短短篇幅卻承載了女性面臨的困境,每個字都充滿力道,每一句都驚心動魄,也因此一舉奪得二○○八年法國「龔固爾文學獎」!阿提克表示,他除了把《耐心之石》視為一部作品,同時也是對生命經驗的回顧。目前他正與法國名編劇尚─克洛德.卡里耶爾合作,著手將本書拍成電影。
譯者簡介
梁若瑜
東吳大學心理系畢業。以翻譯為職,以文字為樂。譯有《然後呢…》、《你會在嗎?》、《因為我愛你》、《我回來尋覓你》、《我怎能沒有你?》、《紙女孩》、《某夜,月未升…》、《找死專賣店》、《機械心》、《如今妳的世界永遠是黑夜》、《艾可說故事》、《那隻見過上帝的狗》、《韃靼荒漠》、《做你自己》、《管他的,就去做吧!》、《綠色企業力》等。
批評指教請來信:escador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