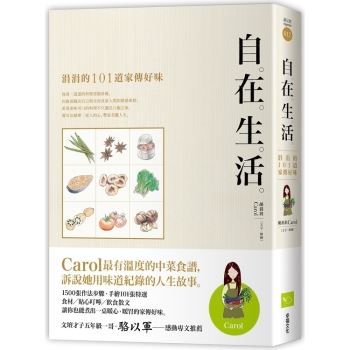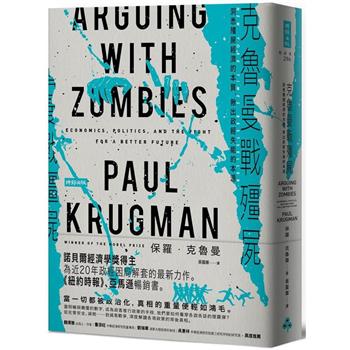●亞馬遜書店讀者4顆星絕讚好評!
距離我發瘋,還有6天又4個小時,
在那之前,我來得及談一場戀愛,或者拿自己的性命當賭注嗎?
艾芙一直都很清楚,她不是童話裡的灰姑娘,沒有神仙教母會幫她一把,更沒有王子會騎著駿馬帶她走。
在科學與理性至上的鋼鐵之國,艾芙只是一個惹人嫌惡的存在。他們全家都帶著遺傳性的壞死病毒,隱隱湧動,直到十六歲,病毒會啃噬僅存的理智,她會跟哥哥一樣發病、失控,幹出無可預料的瘋狂之舉。
十六歲前夕,艾芙焦心難安,卻在此時收到失蹤的哥哥捎來的祕密訊息:「找出女巫字母,救妳自己。」這封信讓艾芙燃起一線希望,也許能找到哥哥,也許能讓自己免於發瘋的命運。
在好友卡爾和領路人狄恩的幫助下,艾芙終於找到女巫字母。但裡頭埋藏的訊息卻讓她無法置信:魔法是真實存在的。與此同時,溫柔的狄恩讓艾芙越來越心動。她絲毫未覺,一雙不懷好意的目光始終凝視著她,一個駭人的詭計正逐步逼近她。當魔法與愛情同時覺醒,女巫字母所引發的黑暗風暴,將覆水難收……
作者簡介
凱特琳.姬德莉琪 Caitlin Kittredge
凱特琳一直都很熱中於歷史和恐怖電影,那是她最豐沛的創作來源。她筆下的小說,壞事總是發生在大好人身上。不過沒關係,那些不怎麼善良的人向來是她的最愛。
今年才二十六歲的凱特琳,已經出版過兩套給大人看的暢銷奇幻小說:《夜曲城市》和《黑暗倫敦大冒險》,而《毒物少女》則是她第一套為年輕讀者所寫的書,想像力十足的架構、高潮迭起的劇情和迷人萬分的角色性格,果然一推出就大受歡迎。
目前凱特琳和兩隻貓、相機,以及好多好多的書,住在美國麻薩諸塞州西部一座斑駁的維多利亞式宅邸中。她沒寫作的時候,就拍拍照,編造「另一種可能」版本的歷史故事,或者……試試會嚇壞人的新髮色。
譯者簡介
黃意然
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傳播學系碩士。在竹科IC設計公司當了七年的PM後,決定投回藝文的懷抱,現為專職譯者,近期譯作有《危險甜心》、《愛猶瑪卡名單》、《勇氣之歌》、《深潛競爭策略》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