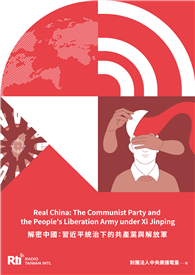原班人羊大集合!《綿羊偵探團》第2彈來囉!
德國狂銷50萬冊!佔領文學排行榜長達40週!
喂!雖然我們長得很可愛,而且又一臉好欺負,
但並不代表誰都可以任意宰掉我們好嗎?
森林裡,沒有花香,沒有和風,
只有一匹不為羊知的狼,和一個羊羊聞之色變的恐怖祕密……
這裡很冷,這裡很灰,這裡很荒涼。
在牧羊女蕾貝卡的帶領下,我們一群綿羊從愛爾蘭來到了法國。不是我在說,新家實在不怎麼適合羊居,不但獸醫一天到晚來敲門,隔壁鄰居還是群又臭又古怪的黑山羊。
其實只要蕾貝卡繼續讀《沉默的羔羊》給我們聽,並定時提供新鮮的糧草,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獸醫來了就裝死,黑羊來了就裝蒜咩。
但我忍不住要說,這裡,其實有點詭異……
先是蕾貝卡的紅衣服被撕成碎片,接著是一隻鹿橫屍在森林入口,然後,一具男屍在樹下被發現--而聽說,這一切都是「狼人」幹的。更讓我們嚇到掉毛的是,「狼人」曾在一夕之間殺光原本定居在這裡的綿羊同胞!
雖然我很想繼續裝死,但為了全體羊群和蕾貝卡的安全,賭上羊的勇氣和智慧,一定要逮到這匹惡狼啦!
一個聲音劃破寂靜,又長又遠,而且痛徹心扉。這會是「狼人」的嚎叫?還是獵物的悲鳴?……
作者簡介
萊奧妮.史汪Leonie Swann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德國慕尼黑近郊。在慕尼黑完成大學學業,主修哲學、心理學及英國文學。在巴黎旅行期間,她常嚮往鄉村生活;而一趟愛爾蘭之旅讓她見識到羊群的迷人之處,寫下《綿羊偵探團》這部小說,初試啼聲即轟動國際,締造長達數年不墜的暢銷熱潮。在全世界無數書迷的殷殷期盼下,萊奧妮終於推出續集《全羊公敵》,不斷切換人類與動物的視角,帶領讀者以更多元的趣味觀點來看待我們的世界。
目前她定居在柏林。
譯者簡介
闕旭玲
專事德文翻譯,譯有《綿羊偵探團》、《死亡的純度》、《火車模型歷險記》、《愛情的哲學》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