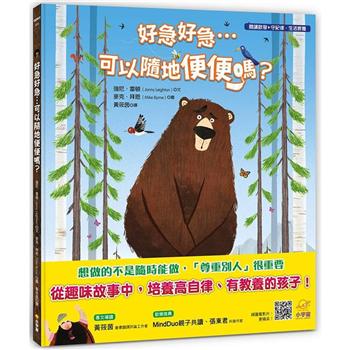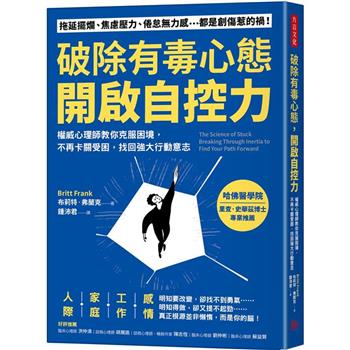她是最美麗的人間凶器,
也是最致命的愛情陷阱!
比《墮落天使》更危險!比《美麗魔物》更揪心!
即將改編拍成電影!亞馬遜書店讀者4.5顆星一致狂推!
不要碰觸我
((抱緊我))
不要愛上我
((守護我))
我的名字叫茱麗葉,我已經被關了264天,已經有6336個小時沒有觸摸過人類。我很飢餓,很想從人間蒸發,很想念窗外那片廣闊的天空。
他們都說我是瘋子,是怪物,是兇手。的確,我的身體是肉食性花朵,是上了膛的槍,隨時準備發射。只要有人碰到我,他就會發生不好的事,他會死。為了大家的安全,他們把我關在這裡。
就在我覺得全世界都快要忘記我的時候,他們送來了一個藍眼睛的男孩。我的新「室友」叫亞當,他對我微笑,說我沒瘋,他甚至觸摸我。奇怪的是,他毫髮無傷,而我感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溫暖,我好像已經「愛過」他了。
但亞當卻背叛了我,他把我交給一個神秘組織,組織的首領華納脅迫我成為他的「武器」,並接受他的「寵愛計畫」。他們把我囚禁在一個華麗的房間,我形同一具沒有靈魂的傀儡,直到我發現了亞當偷偷留下的紙條:「不是妳想的那樣……」
作者簡介:
塔赫拉‧瑪斐Tahereh Mafi
她出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一個小城,目前則定居在加州橘郡,以她的喜好來說,這裡的天氣有點太過完美。找不到書來看的時候,她喜歡看看糖果包裝紙、折價券和舊收據。
《擊碎我》是她的第一部小說,奇炫的背景設定、浪漫的情節發展,加上迷人到不行的男女主角,一推出就引起讀者熱烈討論,目前已售出二十一國版權,並即將改編拍成電影。在《擊碎我》大受歡迎之後,瑪斐又再推出續集《解放我》(UNRAVEL ME)和番外篇《摧毀我》(DESTORY ME),本本均叫好叫座。
想知道瑪斐的最新動態,可以參觀她的個人網站:www.taherehmafi.com。
譯者簡介:
陳芙陽
政大歷史系畢業。曾任大成報編譯和記者、路透社編譯,現為自由譯者,努力在文字與培養國家未來主人翁之間取得平衡。譯有《埃及艷后的皇宮》、《白色城堡》、《我想,我可能是瑪莎》、《寫給母親的情書》、《愛在巴黎午餐時》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讓人上癮,充滿張力,源源不絕的浪漫傾瀉而出!((我好嫉妒!))我簡直無法把這本書放下!──《墮落天使》作者/蘿倫‧凱特
這本處女作有令人興奮的冒險、源源不絕的浪漫情節,還有會讓青少年讀者大感認同的愛情,就像《暮光之城》的貝拉與愛德華一樣。筆觸新穎,以刪除線來透露女主角的內心世界,也增加了可看性!──《書單》雜誌
懸疑中加上浪漫因子……女主角主述故事並分享部分個人日記,形成與讀者之間的緊密關聯。角色發展扎實且逼真,結局為續集留下伏筆,卻又不至於過分吊人胃口,青少年會感到滿足,也會焦急地期待下一本!──學校圖書館期刊
瑪斐在這本初試啼聲的小說中,以心理刻劃的開始結合了動作冒險的結局,構成一部充滿多樣性又引人入勝的作品……作者勇於創新的寫作手法,織就出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說!──出版家週刊
《擊碎我》成功融入了目前受歡迎的反烏托邦題材,並且加上超能力、浪漫與懸疑的元素……這本小說值得一讀,令讀者熱切盼望續集!──《VOYA》雜誌
快節奏的動作場景栩栩如生地傳達出迫切的危險……既是警醒人心的寓言,又是情感豐沛的愛情故事,對喜愛動作冒險的書迷充滿吸引力!──寇克斯評論
名人推薦:讓人上癮,充滿張力,源源不絕的浪漫傾瀉而出!((我好嫉妒!))我簡直無法把這本書放下!──《墮落天使》作者/蘿倫‧凱特
這本處女作有令人興奮的冒險、源源不絕的浪漫情節,還有會讓青少年讀者大感認同的愛情,就像《暮光之城》的貝拉與愛德華一樣。筆觸新穎,以刪除線來透露女主角的內心世界,也增加了可看性!──《書單》雜誌
懸疑中加上浪漫因子……女主角主述故事並分享部分個人日記,形成與讀者之間的緊密關聯。角色發展扎實且逼真,結局為續集留下伏筆,卻又不至於過分吊人胃口,青少年會感到滿足,也會焦急地期待...
章節試閱
一
我已經被關了兩百六十四天。
只有一本筆記本與一枝斷水的筆,還有腦袋裡的數字陪著我。一扇窗,四堵牆,四坪大的空間,兩百六十四天被隔離的日子中,不曾說出口的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六千三百三十六個小時,沒再觸摸過人類。
「妳就要有個((囚友))室友了,」他們對我說。
「((但願妳在這裡自生自滅))因為表現良好,」他們對我說。
「((另一個跟妳一樣的神經病))不用再被隔離了。」他們對我說。
他們是「重建組織」的走狗。重建組織的創始理念應該是要拯救我們垂死的社會,而同樣的這群人,因為我無法控制的事,把我從爸媽家抓出來,關進收容所。沒人在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力量,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我只知道有人以一台白色的廂型車,開了六小時又三十七分鐘把我載來這裡。我知道自己被銬在座位上,知道自己被綁在椅子上。((我知道爸媽根本懶得跟我說再見。))我知道被帶走時,自己沒掉眼淚。
我知道天幕每天都會低垂。
太陽落入海中,窗外的世界激起一片棕紅黃橘的色彩。來自一百根不同枝頭的一百萬片葉子在風中滑翔,翩然舞出無法遠揚的飛行。狂風抓住樹葉枯萎的翅膀,迫使它們落下,任憑在底下站哨的軍人無情踐踏,遭人遺忘。
現在的樹木沒有以前多,科學家這麼說。他們說我們的世界原本是一片翠綠,雲朵原本是一片潔白,太陽始終閃耀著恰到好處的光芒。但是,我對這樣的世界印象模糊。我不太記得從前的事,唯一知道的存在是我現在擁有的世界,是過去的回聲。
我把手掌壓向小小的玻璃框,感受寒冷緊扣著我的手,給我熟悉的擁抱。我們都孤伶伶的,都欠缺了什麼而存在。
我抓起那枝墨水所剩無幾、現在已近乎無用的筆,儘管我早已領悟到必須每天節制用量。凝視它一陣子之後,我改變心意,放棄費力寫下文字的想法。有個囚友可能也不錯,跟真正的人類說說話可能會讓情況好過一些。我練習發出聲音,做出嘴巴已經陌生的常用字唇形。我練習了一整天。
我好驚訝自己居然還記得說話的方式。
我把筆記本捲成一團,塞往牆壁,然後在覆著帆布的彈簧床坐直身子,開始在這張我被迫要用來睡覺的床上來回擺動地等待。
我等著等著就睡著了。
一睜開雙眼,眼前是兩隻眼睛兩片嘴唇兩隻耳朵兩條眉毛。
我壓抑住想要尖叫,想要發洩四肢被重大恐懼攫獲的衝動。
「你是男──男──男──男──」
「妳是女生。」他揚起一邊眉毛,不再靠近我的臉,接著露齒一笑,卻沒有笑意。我好想哭,我的眼神無助、恐懼,瞄向已試開過無數次的房門。他們把我跟男生關在一起。一個男生。
老天。
他們想害死我。
他們是故意的。
這樣才能折磨我,讓我煎熬,讓我以後連晚上都不能入睡。他雙臂都有刺青,肩膀到手肘刺成紋身袖;眉毛少了一個眉環,一定是被沒收了;深藍色的眼眸,深棕色的頭髮,尖削的下巴,強壯精實的骨架。((耀眼。))危險、威嚇、恐怖。
他大笑,而我跌下床,慌張躲入角落。
他打量了今天早上才塞進空位的小床,以及上面的乾癟枕頭、薄薄的床墊與破舊的毯子,恐怕不夠大,連上半身都不夠蓋。他瞄瞄我的床,瞄瞄他的床。
他單手把兩張床併在一起,單腳把兩張金屬床架推到他那一側的房間。他在兩張床墊上伸展身子,抓起我的枕頭拍鬆放在腦後。我已經開始發抖。
我咬著唇,努力把自己埋進陰暗的角落。
他偷走了我的床我的毯子我的枕頭。
我一無所有,只剩下地板。
我未來一無所有,只剩下地板。
我永遠不會反擊,因為我太麻木太麻痺太多疑。
「所以妳是──什麼來著?瘋子?才會在這裡?」
((我才沒瘋。))
他撐起身子好看清楚我的臉,然後再度大笑。「我不會傷害妳的。」
((我想相信他。))我不信。
「妳叫什麼名字?」他問。
((不干你的事?你叫什麼名字?))
我聽見他擾亂人心的呼吸聲,聽見他在原本一半屬於我的床上轉身。我徹夜未眠,屈著膝蓋頂住下巴,手臂緊抱自己小小的身子,我那長長的棕髮是我們之間唯一的簾幕。
我不會睡。
我不能睡。
我不能再聽見那些尖叫聲。
二
早晨聞起來像是雨的味道。
房間飄散出潮溼的石頭以及土壤翻動的凝重氣味;空氣溼冷,散發出泥土的氣息。我深深吸了一口氣,踮著腳走到窗邊,卻只能把鼻子貼近冰冷的窗面,感覺自己的氣息在玻璃上凝成霧氣。我閉上眼睛,聆聽淅瀝的輕柔雨聲穿梭在風中。雨滴是唯一提醒我雲朵擁有心跳的東西。而我,也有。
我對雨滴總是充滿好奇。
我好奇它們怎麼會一直落下,是怎麼被自己的腳絆倒,摔斷了腿,然後在跌落天空通往未知的彼端時,忘記自己的降落傘。就好像有人在地球上方清空口袋,卻似乎完全不在意東西會掉到哪裡,似乎不介意雨滴撞擊地面時會爆裂飛散,不介意它們跌落地面時會碎散,而且人們還會指天罵地說雨滴膽敢敲他們的門。
我就是雨滴。
((爸媽清空在他們口袋裡的我,任由我在水泥地面蒸發消散。))
窗戶告訴我,這裡離山區不遠,而且一定瀕臨水域,只是這些日子以來,一切都接近水域。我只是不知道這是在哪一邊,又是面對哪個方向。我瞇起眼睛注視清晨的光線,有人拾起了太陽,再度把它釘在天幕,但它一天比一天來得低垂。它就像是怠忽親職的爸媽,對孩子只是一知半解,從不看看自己缺席造成了多大的影響,而我們在黑暗中是多麼不同。
一陣突如其來沙沙作響的聲音,我的囚友醒來了。
我連忙轉身,像是又被逮到偷拿食物。這只發生過一次,那時爸媽不相信我的話,我說不是我自己要吃的,而是要救街角的流浪貓,但他們認為我才不會那麼有人性,居然會去關心一隻貓。不是我,不是像我這樣的東西人。話又說回來,他們從不相信我說的任何事。這正是我在這裡的原因。
囚友正在打量我。
他沒脫衣服就睡了,身上是一件深藍色的T恤,搭配一件卡其工作褲,褲管收進小腿高度的黑色靴子裡。
我四肢套著硬邦邦的棉衣,臉上出現一抹玫瑰綻放的紅暈。
他的眼睛掃視我身體的輪廓,這個慢動作讓我的心跳加速。我接住從臉頰散落的玫瑰花瓣,它們飄浮在我身體的外圍,覆蓋住我,給人一種勇氣盡失的感覺。
別再看我了,我想這麼說。
別再用眼神碰觸我,請把雙手擺在身體兩旁,拜託拜託拜託──
「妳叫什麼名字?」他偏著頭,抗拒一半的重力。
我停下動作,眨著眼睛,屏住呼吸。
他移動,而我的眼睛粉碎成數千片,在房間四處彈跳,及時捕捉一百萬張快照與一百萬個時刻。明滅不定的影像隨著年代淡入淡出,凍結的思緒在死角不安定地翱翔,記憶的旋風劃過我的靈魂。((他讓我想起以前認識的一個人。))
一個清晰的呼吸聲,把我震回現實之中。
((別再做白日夢了。))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我問著水泥牆面的裂縫。四堵牆有十四道裂縫,帶來一千個灰色陰影。地板、天花板,全都是同樣的石板。搭得糟透了的床架,則是由舊水管打造。窗子只是一個小方框,但太厚打不破。我的希望耗盡,眼睛渙散疼痛,手指順勢描過冰冷地板上的一條慣性路線。
我坐在聞起來既像冰塊,又像金屬與泥土的地板。囚友坐在我對面,雙腿交疊,腳上的靴子對這個地方來說有點太閃亮了。
「妳怕我。」他的聲音毫無矯飾。
我的手指找到聚合成拳頭的方法。「恐怕你是弄錯了。」
我或許是在說謊,但不干他的事。
他哼了一聲,聲音迴響在我們之間死寂的空氣中。我沒有抬頭,沒有迎上他往我的方向鑽研的眼神,專心領略那種走味、呼出的氧氣與嘆息。我的喉嚨因為某種熟悉的事物而緊縮,某種我早已學會壓抑的東西。
兩下敲門聲把我的情感驚回原處。
他馬上起身。
「沒人,」我對他說。「只是我們的早餐。」兩百六十四頓早餐,我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做的。聞起來有太多化學成分;是一團亂七八糟的結塊,味道很極端,有時太甜,有時太鹹,但總是很噁心。而大部分時間,我都餓到沒辦法注意其中的差別。
我聽見他遲疑了一下就往門邊走去。他打開一個小小的狹槽,凝視不再存在的世界。
「該死!」他在襯衫上連連拍打手掌,差一點就把盤子從開口甩了出去。「該死,該死。」他咬緊牙關,手指蜷成一個緊緊的拳頭。他燙傷手了,如果他願意聆聽,我會先警告他的。
「你應該至少等三分鐘再去碰盤子,」我對牆壁發聲。我沒看點綴在自己小手上的模糊傷疤,那些沒有人可以教我避開的燙傷。「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我靜靜地說。
「哦,所以妳今天是在跟我說話嘍?」他很生氣。我看到他別過頭去之前,眼睛閃動了一下,我知道他超級難為情的,他可是個堅強的傢伙,堅強到不能在女孩子面前犯下愚蠢的錯誤;堅強到不能展現痛苦。
我緊閉雙唇,凝視據說是窗戶的小小玻璃外頭。現在沒剩多少動物了,但我聽說過鳥兒會飛的故事。或許,總有一天,我可以看見鳥。最近,這些故事已編得太過火,沒有多少可以採信,但我不只聽一個人說過,說是最近這幾年還見過在天空飛翔的鳥兒。所以我看著窗外。
今天會有鳥兒飛過。牠會是頭上有著金色條紋,彷彿戴著皇冠的白鳥。牠會飛。今天會有鳥兒飛過。牠會是頭上有著金色條紋,彷彿戴著皇冠的白鳥。牠會飛。今天會有──
他的手。
在我身上。
兩根手指的指尖放在我包覆著衣服的肩膀上,就那麼一下下,就讓我身體的每一條肌肉每一根筋,都繃得緊緊的,糾成一團緊緊依附在我的脊椎。我極力保持靜止,一動也不動。我沒呼吸,或許,只要我不動,這種感覺就會永遠持續下去。
((兩百六十四個日子以來,沒有人觸摸過我。))
有時,我覺得內心的寂寞就要迸裂皮膚現形;有時,我不確定歇斯底里地哭泣或尖叫或大笑是否真能解決問題。有時,我會極度渴望想要去觸摸、想要被碰觸、想要感覺,我幾乎確信自己會在另一個宇宙的懸崖上掉落,沒人能找到我。
這似乎並非不可能。
我已尖叫了好幾年,根本沒有人聽見我。
「妳餓嗎?」他的聲音放低了,還有點憂慮。
((我已經餓了兩百六十四天。))「不餓。」這句話從我唇間迸出時,不過就像是個斷續的小小呼吸聲。然後,我轉身了,雖然不該如此,但我還是轉身了。他凝視著我,研究著我,嘴唇微微張開,雙手垂在兩旁,而眼睫毛因為疑惑眨呀眨的。
我的肚子好像被打了一拳。
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有著什麼。
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我關上那個世界,鎖上它,轉緊鑰匙。
黑暗摺疊起來掩埋了我。
「嘿──」
我睜開眼睛。兩扇被擊碎的靈魂之窗,玻璃填滿了我的嘴巴。
「這是什麼?」他試著保持平淡的聲音,也熱切想要維持冷淡,卻徒勞無功。
((沒什麼。))
我專注在擋住我通往自由的透明方塊,我想擊碎這個水泥世界湮滅它。我想要更強大、更好,更強壯。
((我想要生氣生氣生氣。))
我想要成為那隻展翅飛翔的鳥兒。
「妳在寫什麼?」囚友又說話了。
((這是我的嘔吐物。))
((這支不可靠的筆是我的食道。))
((這張紙是我的瓷碗。))
「妳怎麼不回答我?」他太靠近太靠近太靠近了。
誰都不夠靠近我。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等著他跟我人生中其他所有人一樣,轉身走開。我的眼睛專注在窗外,想著原本會多美好的前景。那些更為宏大、更為偉大的前景,並且為深埋在我骨子裡的瘋狂因子找出一些理由,為我不管做什麼都會毀掉一切找出一些解釋。今天會有鳥飛過。牠會是有著金色條紋彷彿戴著皇冠的白鳥。牠會飛。今天會有鳥飛過。牠會是有著──
「嘿──」
「你不能碰我,」我低語。我騙人,我沒對他這麼說。他可以碰我,我永遠不會對他這麼說。請碰我,我想對他這麼說。
但每當有人碰我,就會有事發生,奇怪的事,不好的事。
致命的事。
我記不得任何一種擁抱的溫暖。無法逃避的孤立寒冰,讓我的雙臂疼痛。我的親生媽媽沒法用她的手臂擁抱我;我的爸爸無法溫暖我冰冷的雙手。我住在一個虛無的世界。
嗨。
世界。
你就要忘記我了。
叩叩。
囚友突然跳了起來。
淋浴的時間到了。
三
門打開來通往深淵。
沒有顏色,沒有光線,沒有承諾,只有位於另一端的恐懼。沒有言語,沒有方向,只是一扇打開的門,每次的意義都相同。
囚友有疑問。
「搞啥?」他看著我,又望向逃脫的幻影。「他們要放我們出去?」
((他們永遠不會放我們出去。))「淋浴的時間到了。」
「淋浴?」他沒有提高音調,但好奇心還是穿梭其中。
「時間不多,」我告訴他。「我們得快一點。」
「等等,什麼?」他伸手拉我的手臂,但我往後退。「可是又沒有光線──我們甚至看不見要去哪裡──」
「快。」我把視線移向地板。「抓住我的T恤邊緣。」
「妳在說什麼──」
遠方傳來警鈴聲,第二次嗡鳴聲近了一點。很快地,整個隔間就會跟警鈴聲一起振動,門就要滑回原來的位置。我抓住他的T恤,把他拉進黑暗之中,跟在我身邊。「別、說、話。」
「但──」
「住口,」我叱責他,然後使勁拖著他的T恤,一邊在這收容所的迷宮之中,憑感覺找路,引導他跟著我走。((這裡是問題少年的家,是來自破碎家庭、受人忽略的孩子的中心設施,是心理障礙人士的安全住所。))這是個牢獄,他們什麼也不給,我們的眼睛永遠不會看到彼此,只除了極少數的時刻,有光線偶然從他們佯裝是窗戶的玻璃縫隙透了出來。夜晚貫穿著尖叫與痛苦的啜泣聲,還有哀號與受折磨的哭喊,以及我永遠無法得知是因為受迫還是自己選擇的血肉與骨頭撕裂聲。來到這裡的前三個月,我都跟自己的臭味共處,沒人告訴我浴室與淋浴花灑在哪裡;也沒人跟我說這個機制是如何運作。除非是要宣佈壞消息,否則沒有人會跟你說話,也根本沒有人會觸摸你。男孩與女孩永遠找不到對方。
永遠,直到昨天。
這絕非巧合。
我的眼睛開始重新適應人工的夜幕。我的手指藉由粗糙的廊道,感覺出方向。而囚友不發一語,讓我幾乎為他感到驕傲。他比我高了二十幾公分,他的身軀擁有與我這年齡相仿的結實肌肉與力量。這個世界還沒破壞他,如此毫無自覺的自由呀!
「什──」
我更加用力拉著他T恤,阻止他說話。我們還沒穿過走廊。對於這個可能用兩根手指頭就可以折斷我的人,我有種奇怪的保護慾。他不了解自己的無知會讓他變得多麼脆弱,不了解他們可能毫無道理就殺掉他。
我決定不要怕他。我認定他的行動只是不成熟,而不是真的有威脅性。((他看起來是如此熟悉如此熟悉如此熟悉。))我曾經認識一個有著同樣藍色眼眸的男孩,我的記憶不讓我恨他。
或許,我也想要有個朋友。
再走六步,牆面從粗糙轉為平滑,然後我們右轉。再通過兩步遠的空間,我們來到一扇門把壞掉的破裂木門。數三下心跳,以便確定這裡只有我們。我往前一步把門片往內推,一個輕柔的吱嘎聲,窄縫開了,但裡面一無所有,只有我對這個空間的想像。「這邊。」我輕聲說。
我把他拉向一排蓮蓬頭,然後摸索地板排水溝找尋肥皂。我找到兩塊,其中一塊是另一塊的兩倍大。「手張開,」我對著黑暗說。「它黏糊糊的,但別掉了。這裡肥皂不多,我們今天很幸運。」
他已有一陣子沒說話,我擔心了起來。
「你還在嗎?」我懷疑這會不會是陷阱,會不會是計畫,有沒有可能是誰派他來這個小地方趁著一片漆黑來殺我。我一直不知道他們打算在這家收容所對我做什麼,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覺得把我關起來就夠了,但我一直覺得他們會殺了我,總覺得它似乎是個可行的選擇。
我不能說自己是無辜的。
但是,我會在這裡,是因為我從來不曾蓄意去做的事,而且似乎也沒人在意那是意外。
((我爸媽從未試過幫我。))
我沒聽見淋浴聲,一顆心懸在原地。這個特別的房間很少客滿,但通常會有別人在,即使只是一、兩個人。我後來發現,這家收容所收容的人要不真是瘋了而沒法找到淋浴間的路,就是他們根本不在乎。
我用力吞嚥了一下。
「妳叫什麼名字?」他的聲音劃破空氣,同時也打斷我的意識流。我感覺到他的呼吸比之前更接近。我的心狂跳,我不懂為什麼,但就是控制不了。「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妳的名字?」
「你張開手了嗎?」我口乾舌燥,聲音粗嘎。
他上前一步,我幾乎怕到不敢呼吸。他的手指輕輕劃過我衣服上的僵硬纖維,這是我唯一擁有的衣物。而我設法吐出氣息,只要他不碰觸我的皮膚,只要他不碰觸我的皮膚,只要他不碰觸我的皮膚。這似乎就是那個秘密。
我薄薄的T恤已經在這棟建築物的硬水中洗了無數次,感覺就像套在皮膚上的麻布袋。我把比較大的肥皂放進他的手心,躡腳往後退了一步。「我要幫你打開蓮蓬頭了哦。」我說明,並且小心不要抬高音量,以免被別人聽到。
「我的衣服怎麼辦?」他的身體還是太靠近我了。
我在黑暗中眨了一千下眼睛。「你得脫下來。」
他笑了起來,聽起來就像一種令人愉快的氣息。「是,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沖澡時要怎麼辦?」
「努力不要弄溼它們。」
他深吸了一口氣。「我們有多少時間?」
「兩分鐘。」
「老天,妳怎麼不──」
我打開他的蓮蓬頭,也同時打開我的,不太管用的蓮蓬頭流出斷斷續續的水珠,也淹沒他的牢騷。
我機械式地行動。我已做過許多次,早已記得擦拭、沖洗,以及在身體與頭髮之間轉換肥皂最有效率的方式。這裡沒有毛巾,所以訣竅是不要用太多水弄溼身體。如果太溼,就永遠沒法好好弄乾身體,接下來一星期可就會幾乎因肺炎死掉。我是知道的。
剛好九十秒,我已擰乾頭髮,又套進破爛的衣衫裡。我的網球鞋是我的所有物中,唯一仍保持相當良好狀況的東西。我們在這裡用不著走太多路。
囚友幾乎立刻跟著照做。我真高興他學得這麼快。
「抓住我衣服的邊緣,」我指示他。「我們得快一點。」
剎那間,他的手指輕輕掠過我腰背部位,我必須咬住嘴唇以壓抑緊張感,也幾乎停下腳步。從來沒有人把手放得如此靠近我的身體。
我必須迅速向前,這樣他的手指才不會碰到我。他踉踉蹌蹌趕了上來。
等我們終於又困在足以讓人得到幽閉恐懼症的熟悉四堵牆裡,囚友仍舊盯著我不放。
我把自己蜷縮在角落。他還是佔據了我的床、我的毯子與我的枕頭。我原諒他的無知,但或許當朋友可能還太快了些。或許我太急著幫他,或許他出現在這裡,其實只是要讓我變得更為悲慘。只是,如果我不保持身體溫暖,可能就要生病了。我的頭髮太溼了,而通常被我拿來包頭髮的毯子還在他那頭的房間。或許我還是很怕他。
在陰暗的白天光線下,我的呼吸太急促,抬頭太急促。囚友在我的肩膀上披了兩條毯子。
一條我的。
一條他的。
「對不起,我真是個大混蛋,」他對著牆壁輕聲說道。他並沒有碰我,我很((失望))高興他沒有。((我希望他碰我。))他不可以碰我。誰都不可以碰我。
「我叫亞當,」他緩緩說道,然後離開我身邊,挪好房間,他單手就把我的床架推回我這邊的空間。
亞當。
真是個好名字,囚友有個好名字。
這是我一直很喜歡的名字,但我忘記原因了。
我沒浪費時間,立刻爬上那彈簧幾乎已露出的床墊,而我實在累壞了,幾乎感覺不到那些就要戳進皮膚的金屬圈。我有二十四小時沒睡了,在疲憊令我的身體無法動彈之前,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亞當是個好名字。
一
我已經被關了兩百六十四天。
只有一本筆記本與一枝斷水的筆,還有腦袋裡的數字陪著我。一扇窗,四堵牆,四坪大的空間,兩百六十四天被隔離的日子中,不曾說出口的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六千三百三十六個小時,沒再觸摸過人類。
「妳就要有個((囚友))室友了,」他們對我說。
「((但願妳在這裡自生自滅))因為表現良好,」他們對我說。
「((另一個跟妳一樣的神經病))不用再被隔離了。」他們對我說。
他們是「重建組織」的走狗。重建組織的創始理念應該是要拯救我們垂死的社會,而同樣的這群人,因為我無法控制的事,把我...


 2015/01/27
2015/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