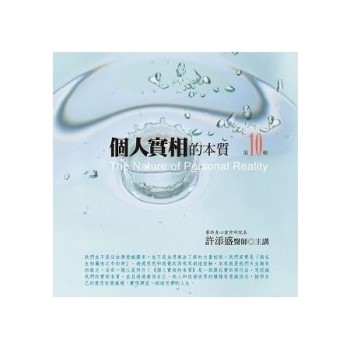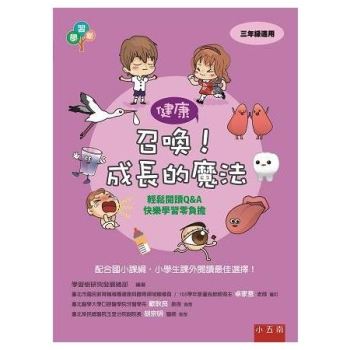圖書名稱:比利戰爭【完整新譯本】
在大審判之後過了兩年,患有多重人格障礙的比利,從原本接受治療的心理健康中心被移送到素有「地獄」之稱、專門收容精神異常罪犯的州立利馬醫院。
利馬醫院之所以被稱為「地獄」,是因為很少有病人能在這裡獲得良好的照料並痊癒,反而只要病人鬧事或不聽從院方人員的指示,就會被以激進的方式「治療」。許多人在「電擊治療」後變成植物人,或無法忍受不堪的對待而自殺。
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比利幾乎沒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而院方開出的藥物也讓比利的意識更加混亂,還好他和幾個院友成為同甘共苦的戰友,包括開朗的喬伊、大塊頭蓋伯、有老鼠般獠牙的巴比,以及單純而膽小的理查。
然而,內有二十四個人格在互相爭鬥,外有醫護人員的肢體和語言暴力,這場看似絕望的「戰爭」,究竟能不能找出一絲光明的希望?……
本書是《24個比利》出版十三年後,才在無數讀者殷殷期盼下推出的續集。書中真實揭露精神病院罔顧人權的黑幕,也因為太具爭議性,歐美各國至今無法出版,全世界僅有中文版和日文版。而透過比利的真實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尊嚴,即使在最幽微的黑暗中,依然熠熠生光。
名人推薦
知名精神科醫師王浩威、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方俊凱、北一女國文老師易理玉、文學與視覺藝術創作者尉任之、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黃裕舜 經典推薦! ●按姓名筆劃序排列
作者簡介
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
一九二七年生於紐約,擁有布魯克林大學心理學學位。一九五〇年代早期進入科幻小說雜誌《Marvel Science Fiction》工作,隨後轉換跑道,成為時裝攝影師與中學教師。凱斯在教學之際,利用課餘時間在布魯克林大學進行英美文學研究,再獲得文學學位。
一九五九年,凱斯在《奇幻與科幻》雜誌首度發表作品即一鳴驚人,短篇處女作《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並為他贏得「雨果獎」的肯定,而在擴展成長篇後又再榮獲「星雲獎」,一舉囊括了科幻小說界最重要的兩項大獎!這部探討心智障礙主角查理與白老鼠阿爾吉儂在醫療介入後,身體與心理所產生的變化的作品,更屢屢受到影劇圈的青睞,一九六八年先被改編拍成電影《落花流水春去也》 (Charley),讓男主角雷夫.尼爾遜拿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殊榮;而NHK也在二〇〇三年改編成電視劇《獻花給倉鼠》,法國、波蘭與英國則先後改編成舞台劇。
在《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大獲成功之後,多年來凱斯陸續推出了《第5位莎莉》、《24個比利》、《比利戰爭》以及《鏡像姊妹》等一系列以探討多重人格障礙為主題的作品,也使他成為讀者心目中最擅長描寫人類心理問題的作家。其中《24個比利》不但為他贏得了德國「科德.拉斯維茲獎」的最佳外國小說,並榮獲美國偵探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提名,美國華納電影公司也計畫改編拍成電影。
凱斯的作品已售出三十種以上語文版權,全球銷量超過六百萬本。一九八八年,布魯克林大學頒發榮譽校友獎章給凱斯;二〇〇〇年,美國科幻協會則頒發「榮退作家獎」,以表揚他在科幻小說上的卓越成就。
他另著有回憶錄《阿爾吉儂、查理與我》。目前居住在美國俄亥俄州雅典市。
譯者簡介
趙丕慧
一九六四年生,輔仁大學英文碩士。譯有《杜鵑的呼喚》、《臨時空缺》、《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易經》、《雷峯塔》、《穿條紋衣的男孩》、《不能說的名字》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