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並不消逝,只是遷徙。
張曼娟最歷久彌新的散文集,致我們都擁有過的瑰麗年華。
青春,是冰做的風鈴。
聽見透亮悅耳的聲響,忘記它正迅速消融。
青春,是令人永遠緬懷的滋味,
更是失去之後,費盡心思想要追尋的珍寶。
並且,絕對的不可復得。
但也許,青春成為一種印記,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和詮釋,深深烙印在生命底層,
我們保留了自己想要擁有的部分,我們變成了現在這樣的人。
於是,青春永恆的封存在記憶中,無法刪除,不能取代。
-張曼娟
| 購物比價 | 找書網 | 找車網 |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青春【全新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5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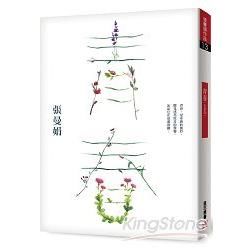 |
青春【全新版】 作者:張曼娟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3-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