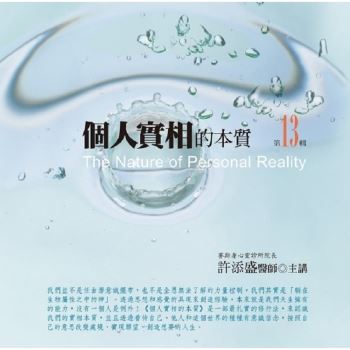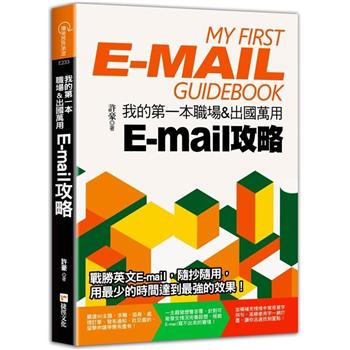虞姬寂靜
那時候,男人躺在女人懷裡,睡著了。
不過,男人身材太過高大,所以頭也相對較大。若是直接仰倘,把頭放在坐在床上的女人的大腿上,她纖瘦的身體一定無法承受。疼痛會透過單薄的肌肉,漸漸深入骨頭。所以,男人自己把鋪被捲起來,當成枕頭枕在脖子下面,只把梳起髮髻的頭頂部放在女人的大腿上,把那之外的修長身軀平擺在床上。
女人把一隻手放在男人的額頭上,另一隻手放在長滿鬍鬚的下巴上,用手臂圍住男人的輪廓,伸到床下的腳尖緩緩打著拍子。房間狹窄、微暗。放在床邊的燈火,照出微弱的光芒,影子在牆上無聲地跳著舞。女人邊看著影子,邊哼著歌。那是小時候母親唱給她聽的搖籃曲。但是,她沒有唱出歌詞。因為歌詞裡面有出現一下已經滅亡的國家的名字。女人對那個國名沒有任何感覺,但男人對那個國家恨之入骨,率領數十萬兵馬,把那個國家殺到片甲不留。
如果知道每天唱給他聽哄他入睡的歌,歌詞裡面有自己最忌諱的國家出現,男人會不會生氣呢?不過是跟國名一起讚揚浩瀚的河川而已,男人也會生氣嗎?女人用手指輕輕滑過男人筆直延伸的眉毛。現在的這個男人,一定不會生氣。她覺得,男人即使知道這件事,也只會用懶洋洋的眼神看她一眼,默默閉起眼睛。男人就是變得這麼溫柔了。看到女人的白色上衣,一天天變髒了,不再是剛做時的樣子,男人有時會露出悲傷的表情。把粗糙的手放在女人纖細的脖子後面,對她說對不起。以前,男人不是會露出這種表情的大王。由此可見,男人變得脆弱了。
被床帳隔開的前方,有個爐灶被點燃,用來取代暖爐。在爐灶裡燒光的木柴,發出咔唦聲崩塌了。女人停止男人睡著後也繼續哼唱的歌,忽然抬起頭來。女人如絲綢般白皙滑潤的眉間,蒙上了淡淡的陰霾。她微歪著頭,側耳傾聽。
她聽見了什麼聲音。
起初以為是風聲。
但是,感覺比風聲低沉、而且更厚重、密不透風般的聲音,從牆外傳進來時,女人停止了打著拍子的腳。
她心想該不該叫醒他呢?低頭一看,男人已經張開了眼睛。
長長的睫毛上下動了兩、三次,溼潤的眼眸反射著燈火曲折的火光。
「虞啊。」男人發出了聲音。
「是。」女人表情僵硬地點點頭。
「妳也聽見了嗎?」
「是的,大王。」
男人沉默片刻,用嘶啞的聲音喃喃說道:
「這不是夢吧?」
女人還來不及回應,男人已經爬起來了。
蓋到肚子的毛皮滑下來,男人的寬闊背部塞滿了女人的視野。從外面傳來的聲音,已經帶著旋律逐漸塑造出一首歌的形態。男人站起身來。女人叫喚「大王」,他也沒聽見。女人又叫喚了一次,但他只短短回了一句:
「妳待在這裡。」
男人頭也不回地鑽出帷幔,走向了隔壁房間。門一打開,剛才只是含糊不清的一團聲音,變成了清晰的歌聲。女人撿起滑落到地上的皮毛,急忙去追男人。她穿越毫不留情地從敞開的門灌進來的冷風,衝出了幽暗的戶外。
不知何時,男人們都聚集在一起了。不可思議的是,每個人都文風不動,也不出聲,只是像個木頭人呆呆站著,視線在虛空中茫然地徘徊。男人一出現,他們便趕緊點燃篝火,火光隨風飄搖,宛如配合著歌聲的抑揚頓挫。歌聲不是來自我方陣營,而是來自有幾十萬人的敵方陣營。慷慨激昂的歌聲,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
那是女人沒聽過的歌。女人吐出白色氣息,雙頰僵硬,聽著似乎被陰鬱壓抑的陌生音調。起初像是彼此試探的歌聲,氣勢逐漸高昂,就在合聲強烈到幾乎傳至天際的時候,眼前的巨大背部震顫起來。女人不由得把手上的皮毛披在那個背上。
「那是楚歌。」男人觸摸女人放在他肩上的手,回過頭說:「歌詞是說留在楚國的年老母親、妻子,都在等我們回去。從敵人的陣營,傳來了我們故鄉的歌,是以前支持我的那些人唱的。」
遮蔽男人的聲音且越傳越遠的歌聲波浪,似乎暫告一個段落,終於平靜地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圍繞著男人的士兵們的啜泣聲。
男人說:「妳會著涼。」抓起披在背上的毛皮,裹住女人。歌又從頭開始唱起,男人摟住女人單薄肩膀的手,加強了力氣,強到女人幾乎叫出聲來,驚訝地抬頭看著男人的臉。
看到那雙細長的眼睛,奇妙地搖曳著篝火的火光,女人知道男人哭了。
***
女人是在咸陽遇見了男人。
把女人帶到男人面前的老人,告訴她今後要叫男人「大王」,說完就無聲無息地離開了房間。光這句話,女人就知道坐在眼前的男人的身分了。在這個都城被稱為大王的人,只有那位消滅秦國,剛成為她居住的咸陽新主的年輕將軍。
跟女人獨處後,男人還是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沒說。
經過漫長的沉默,男人才緩緩站起來。
「我是項羽。」
他的身軀龐大,女人必須抬起頭才能看到他的臉。透過上衣也很容易看得出來,他有著宛如為戰爭而生的強韌骨骼、發達的肌肉。但是,男人的聲音比女人想像中沉穩多了。甚至聽得出來,為了不讓女人害怕,他特別用心。看到女人在他胸部位置的疑惑的臉,他簡短扼要地下令:
「從今天起,妳的名字叫虞。」
女人當然有父母為她取的名字。但是,范增老人把穿著絕非上等衣服、一看就知道是後宮婢女的她,從咸陽後宮帶到這裡時,只對她說:
「如果大王給了妳新的名字,以後妳就跟那個名字一起活下去。」
老人根本沒打算問她的名字。
「虞啊。」
如老人所說,男人給了女人名字。
當女人點頭接受那個名字,用嘶啞的聲音叫喚「大王」時,女人就成了男人的東西了。
第二天,男人放火燒了咸陽。
火燒了三天三夜,享盡世上所有榮華的秦國首都,就這樣燒成了灰燼。女人的父親在始皇帝死後,被拉去當兵,鎮壓各地接二連三發生的叛亂,從此下落不明。在這場大火中,一個人住在都城一隅的母親,是否平安無恙地活下來了,女人也無從確認。母親不知道女兒被帶去新大王的陣營了,女兒也不知道大王打算燒了都城。配合大王的行動搭上車子,躲開外界的視線離開關中後,她才聽說咸陽已經從大地消失了。
那之後的四年,女人都待在男人的陣營裡,以寵姬的身分隨侍在側。因為要往東、往北、往西與敵人交戰,所以男人總是置身於戰火中。對於一度企圖反叛的對手,男人會施加可以說是極盡無情的慘烈報復。但對於自己人,他會付出無限的慈愛,在戰場上一定自己打頭陣,對把生命交給他的人負責。男人的軍隊幾乎不知道什麼叫戰敗。主子的激情彷彿有移轉作用,士兵們都浴血奮戰,戰到一兵一卒,以此發誓對勇敢大王的忠誠。
跨上名為「騅」的愛馬前往戰場的男人,充分展現霸王的風格。然而,一踢馬鐙,馬開始奔馳,男人就瘋狂了。他曾經縱情地殺戮,也曾活埋了二十萬名無辜的人民。女人離開咸陽後度過的四年,男人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耗費在戰場上。男人在戰場上的無情,女人也時有所聞,但男人從未在女人面前展現過他粗魯的性格。在床上時,男人會對懷裡的嬌小身軀,深情地喃喃叫喚:
「虞啊。」
這時,女人便能從男人的叫聲中,感覺到男人堅定不移的情感,以及需求自己的強烈熱情。
從咸陽那一夜起,男人對她的深情從來沒有改變過。起初,女人完全無法揣測理由。後宮多的是從全國各地送來的美女,為什麼會選擇只是一般婢女的自己呢?女人曾問過那時的老人一次。范增當時可能是來實地勘查吧,帶著大批士兵闖入了咸陽後宮的中庭,女人跟同僚一起從房間窗戶察看狀況。范增一看到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她帶去了大王的陣營。
「虞美人啊。」
據說已經超過七十歲的范增老人,在女人面前恭敬地低下了頭。
「妳心中似乎有兩條互不相容的河川。」
從他沒剩幾顆牙齒的嘴巴,發出了很難聽清楚的聲音。
「假如自己的疑慮是真的……自己被選中只是某種錯誤,那麼,現在的富貴總有一天會消失,也就是說,這只是夢幻一場──妳有想承認這種不安來源的心情。以及,不,大王的愛情深度是真實的,絕不是一時興起的玩心──想否認前面想法的心情。兩種心情在同一個鼎中交雜,捲起了漩渦。但是,虞美人啊,妳非常滿意目前的現實吧?既然這樣,還需要想什麼呢?對妳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知道過程,也不是攪弄不安,而是接受那之後的結果。大王是個深情的人,只要妳愛他,他一定會回報妳的感情。」
老人撫摸著垂到胸口看起來很寒酸的白鬍鬚的手,突然指向了女人。指著在盤起來的髮髻上綻放鮮豔色彩的玳瑁髮簪,那是大王賜給女人的東西。
「祝妳幸福。」
老人露出一口黑牙,自己呵呵笑了起來。
包括聊天在內,范增這樣站在女人前面,用江南腔很重的音調與女人交談,只有過這麼一次,以前沒有,今後也不會再有。
在與劉邦率領的漢軍長期交戰的日子裡的某一天,老人突然從陣營消失了。
原因完全不明,有人說他是隱瞞病情工作,知道死期將近,便回故鄉了。也有人說,他一再責怪主人沒有在鴻門宴果決地殺死漢王劉邦,項王忍無可忍,就把他放逐了。甚至有人說,不,那是劉邦的離間計,企圖破壞項王與軍師之間的感情,結果他們兩人真的中計了。女人要判斷真相為何,不是那麼容易。大王在閨房絕不談公事,所以女人沒有對他提起過老人的事。但有件事顯而易見,那就是失去大王親奉為亞父、非常尊敬且重用為一軍首腦的范增後,男人的將星光芒很快就變得陰暗了。
在街頭巷尾流傳的許許多多讚賞大王的英勇的話中,女人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七十多場戰爭,從來沒失敗過」。沒有任何話,比這句話更能展現男人的強勁。沒有任何話,比這句話更能照亮男人的前途。
女人心想,怎麼會這樣呢?遇到敵人,從來沒輸過一次的大王,現在竟然被困在名為垓下的山丘上,只有幾戶民家相鄰。從包圍山丘的數十萬漢軍,傳來曾經是自己人的士兵所唱的故鄉的歌。男人們暴露在強烈寒風中的鬍子沾上了霜,眼睛泛著淚水,從剛才便一語不發。這都是為了什麼呢?
忽然,女人嗅到悄悄靠過來的死亡氣息。女人抬頭看大王。男人緊閉著嘴巴,瞪視著浮現在黑暗中的敵人的篝火之海。女人心中沒有恐懼,也沒有疑惑。男人是希望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能保住武士的自尊吧?那麼,自己身為霸王這輩子最愛的女人,也該毫不眷戀地死去。
***
來自四面的楚歌,依然沒有停止。
跟著男人回到房間後,女人坐在床上,呆呆地等著沾在衣服上的冷氣逐漸退去。
從隔間的帷幔前,傳來大王的聲音。接到命令要去準備酒宴的近侍跑出去了,男人在另一個留下來的從僕前,攤開了長長的手臂。
正好被斜斜垂下來的床帳擋住,從女人的位置,只能看到男人的身體的一半。從僕拿來的代表大王的甲冑,在微暗中依然閃爍著白光。男人默默穿上甲冑,女人聽著配件撞擊聲、皮革摩擦聲,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男人逐漸變成人人害怕的霸王模樣。
男人拿起被呈上來的刀,轉向了女人。
這時候男人才發現盯著自己的視線,表情浮現有些困惑的搖曳陰影。
瞬間,男人的臉在床帳前消失不見了。那是為了調整甲冑而有些移動,但不知道為什麼,女人卻覺得男人是猛然逃開了自己的視線。
「等一下要辦酒宴。」
走到女人前面,低下頭鑽進床帳裡的男人,臉部表情已經恢復戰場上的武士的模樣。難道是自己的錯覺嗎?從火光照耀下淡淡浮現的右半部的臉,女人看出大王已經有了最後的覺悟。
「我已經下令打開倉庫,把酒、肉等所有東西都分給大家。這裡不會留下任何東西。」
每次大戰前,大王都會辦酒宴。在酒宴上,與麾下將領們觥籌交錯,合聲高歌。然後,騎上在外面等候的騅,帶領諸將們一舉衝入戰場。女人一定會在酒宴上翩然起舞。區區一個後宮婢女,當然沒什麼舞蹈的素養。儘管如此,女人還是跳了。因為在身為唯一寵姬的日子裡,男人要求她學習。所以,女人拚了命學。可能是原本就有天分,女人幾乎在一年內就學會了所有的技藝。沒多久,女人就開始在戰前的酒宴上跳舞了。不知不覺中,大家都把女人的舞蹈當成了帶來勝利的幸運符。
「再也不會回來這裡了。」
男人說要跟窩了將近一個月的山丘告別了。從他的聲音,完全聽不出被楚歌波浪襲擊時的動盪不安。女人把懸在半空中的腳踝放入鞋子裡,從床上站起來。酒宴的會場應該會設在山丘上最大的屋子,所以女人攤開剛折好的皮毛,準備移到那裡。
但男人舉起手,阻止了她的行動。
「妳不必來。」
正要把皮毛披到肩上的女人,停下動作,反彈似地抬起了頭。
「妳收拾行李。」
女人還來不及開口問為什麼,聲音就從上面傳下來了。
「酒宴後,我會打開門打出去。妳趁我們引開對方的注意力時,從後門逃出去吧。那個范賈會協助妳。沒時間了。」
「不,大王,臣妾要留在這裡,跟你一起出席酒宴……」
「不行。」
男人搖搖頭,打斷了女人的話。他的聲音平淡得出奇,含帶著女人從來沒聽過的異常冰冷。
「妳叫什麼名字?」
女人不懂他為什麼這麼問,沉默了一會才小聲地回答:
「我叫──虞。」
男人又搖搖頭說不對。
「我是問妳原來的名字。妳並不是出生時就叫虞,虞是我給妳的名字。」
聽到男人一一確認什麼後再往下說的語調,女人深感疑惑,心想為什麼要問這種事呢?她是虞。即使這是男人在咸陽給她的名字,這個名字也已經在她體內,跟她緊緊結合在一起了,連伸入一根頭髮的縫隙都沒有。再說,以前的名字她早已忘了。生下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恐怕都不在世上了。事到如今,已經沒有她可以帶著名字回去的地方了。她只能以虞的身分活著、以虞的身分死去。
「恕我直言,大王……」
女人從來沒有反抗過男人,一次也沒有。但是,這次不一樣。如果聽大王的話逃走,就意味著與打最後一場戰的男人永別了。
「虞的生命與大王同在。若是大王不帶我去戰場,我隨時都可以死給大王看。」
說不定,她那道視線也帶著刺人般的嚴峻。因為是鼓足了勇氣說話,所以說到最後時還咳了起來。她覺得,不趕快把想法說出來,男人可能馬上就會離開這裡。
「妳叫什麼名字?」
男人只是不停地重複同樣的問題。即便女人的眼神,確實捕捉到了男人的目光,男人還是一副冷漠的表情,彷彿眼前沒有任何人。
「臣妾叫虞姬,沒有其他名字!」
女人顧不得有從僕站在大王後面,大叫著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把那個交給我。」
男人的聲音冷靜到不能再冷靜,指著女人的頭上。女人一時無法理解男人的意思,當她察覺指的是大王送給她的東西裡,她最珍愛的玳瑁髮簪時,男人又說了一句:
「把璣(不圓的珠子)也給我。」
大王的眼神只要她聽從指示。
女人覺得大腦一片空白,把手伸向了耳朵,摘下了耳環。那上面有小石頭那麼大的璣,閃爍著淡淡的光芒。接著,她把髮簪也拔下來了。她用指尖再次觸摸裝飾在上面的寶石後,把髮簪和耳環一起放在伸過來的厚實掌心上。稍微碰觸到的大王的手,十分冰冷。她沒辦法看男人的臉,只能盯著大大的手握起來。
「這幾年來,妳在我身旁,把我服侍得很好。今後,妳好好過日子吧。妳可以從這裡拿走任何妳喜歡的東西。」
反彈似地抬起頭的女人,眼睛已經泛紅了。
「虞、虞不要那種東西,虞只要跟大王在一起……」
「妳不是虞。」
女人懷疑自己的耳朵。
男人俯視張大嘴巴、表情呆滯的女人。
「我給了妳虞這個名字。但是,現在妳把這個名字還給我了。妳不再是虞了,沒有必要跟我待在這裡,快快離去。」男人很快下完命令,說:「再見了。」
女人連聲音都發不出來,目送寬大的背部從床帳逐漸遠去。可能是門打開了,甲冑的配件相撞擊的聲音,很快就被突然變大聲的楚歌淹沒,融入那憂鬱的旋律裡,消失不見了……
《霸王別姬》裡的虞姬竟然不是虞姬???在四面楚歌之際,遭到霸王拋棄的她,又會做出什麼驚人之舉?想知道萬城目學如何顛覆經典名作,絕對不能錯過超乎想像的《悟淨出立》!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悟淨出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6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悟淨出立 出版日期:2016-05-0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0 |
Others |
二手書 |
$ 110 |
Others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文學 |
$ 221 |
日本現代文學 |
$ 239 |
小說/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悟淨出立
喔喔喔,那些故事沒告訴你的事,原來是這樣!
只有萬城目學這種奇葩才寫得出來的狂想之作!
●《鹿男》天才作家暌違七年的最新短篇傑作!
●入圍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直木賞」!
●Amazon書店讀者★★★★大好評!讀書meter網站書迷熱烈回響!
經典名作的隱藏版劇情×無人知曉的秘密內心戲×不按牌理出牌的萬城目學
《西遊記》、《三國演義》、《霸王別姬》、《荊軻刺秦王》……
當那些故事中的「配角」,成為自己生命裡的「主角」,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子?
讓時間靜止在主角登場的前一刻,這一次,就看他們的了!
悟淨走路的時候在想什麼?趙雲在船上為什麼總是不說話?虞姬藏著什麼從沒跟別人說過的秘密?與那個刺秦王的荊軻同名會有什麼困擾?如果爸爸是死也要寫完《史記》的司馬遷會怎麼樣?
奇想天才萬城目學這次聚焦那些著名經典裡最無人關注的角色,他以獨特的視角深入描寫他們沉靜外表下的暗潮洶湧,不僅顛覆了我們對經典的刻板認知,更帶領我們重新體驗了一場穿越時空的魔幻旅程,讓人忍不住驚呼:真的太有趣了!
作者簡介:
萬城目 學
1976年出生於大阪,京都大學法學系畢業,現定居東京。
2006年以《鴨川荷爾摩》贏得第四屆「Boiled Eggs新人賞」後正式出道,並首度入圍「本屋大賞」。他的第二部作品《鹿男》不但再次入圍「本屋大賞」,更入圍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直木賞」。第三部長篇小說《豐臣公主》則幫他再度問鼎「直木賞」,而分別以京都、奈良、大阪為故事舞台的《鴨川荷爾摩》、《鹿男》和《豐臣公主》,也成為書迷心目中必讀的「關西三部曲」。
其後萬城目學又分別以《鹿乃子與瑪德蓮夫人》、《到此為止吧!風太郎》、《悟淨出立》入圍「直木賞」,以《偉大的咻啦啦砰》、《到此為止吧!風太郎》入圍「本屋大賞」,年紀輕輕即已五度入圍「直木賞」、四度入圍「本屋大賞」,並且多部作品均被改編拍成電影或日劇,堪稱近年來最炙手可熱的天才型作家。
另著有小說《巴別塔九朔》(暫譯)以及《鴨川荷爾摩》的戀愛番外篇《荷爾摩六景》和散文集《萬字固定》等書。
譯者簡介:
涂愫芸
東吳日語系畢業,遊學日本三年,任職日商七年,現為專職翻譯。譯有《鹿男》、《鴨川荷爾摩》、《荷爾摩六景》、《偉大的咻啦啦砰》、《萬字固定》、《到此為止吧!風太郎》、《華麗一族》、《欠踹的背影》等書。
●萬城幻遊官網:www.crown.com.tw/makime
TOP
章節試閱
虞姬寂靜
那時候,男人躺在女人懷裡,睡著了。
不過,男人身材太過高大,所以頭也相對較大。若是直接仰倘,把頭放在坐在床上的女人的大腿上,她纖瘦的身體一定無法承受。疼痛會透過單薄的肌肉,漸漸深入骨頭。所以,男人自己把鋪被捲起來,當成枕頭枕在脖子下面,只把梳起髮髻的頭頂部放在女人的大腿上,把那之外的修長身軀平擺在床上。
女人把一隻手放在男人的額頭上,另一隻手放在長滿鬍鬚的下巴上,用手臂圍住男人的輪廓,伸到床下的腳尖緩緩打著拍子。房間狹窄、微暗。放在床邊的燈火,照出微弱的光芒,影子在牆上無聲地跳著舞。女...
那時候,男人躺在女人懷裡,睡著了。
不過,男人身材太過高大,所以頭也相對較大。若是直接仰倘,把頭放在坐在床上的女人的大腿上,她纖瘦的身體一定無法承受。疼痛會透過單薄的肌肉,漸漸深入骨頭。所以,男人自己把鋪被捲起來,當成枕頭枕在脖子下面,只把梳起髮髻的頭頂部放在女人的大腿上,把那之外的修長身軀平擺在床上。
女人把一隻手放在男人的額頭上,另一隻手放在長滿鬍鬚的下巴上,用手臂圍住男人的輪廓,伸到床下的腳尖緩緩打著拍子。房間狹窄、微暗。放在床邊的燈火,照出微弱的光芒,影子在牆上無聲地跳著舞。女...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中文版作者自序
我想成為寫出這種文章的作家!
高中時,我在現代文學的試題中,邂逅了有趣到不行的文章,至今仍記憶猶新。
內容是三藏法師和孫悟空、沙悟淨、豬八戒,前往天竺取經途中的故事。我心想原來這就是《西遊記》啊,結果並不是。在試題的文章裡,沙悟淨似乎思考著什麼。這個水裡的怪物,一個人嘀嘀咕咕沉吟,用深奧難懂的話語,認真探索著悟空的天賦、三藏法師目光前的永恆。我心想這篇有點怪但有趣到不行的文章,究竟是什麼啊?瞬間被吸引的我,把考試拋在腦後,一頭栽進了文章裡。
當時,我不知道是誰寫的,也沒有關於試題...
我想成為寫出這種文章的作家!
高中時,我在現代文學的試題中,邂逅了有趣到不行的文章,至今仍記憶猶新。
內容是三藏法師和孫悟空、沙悟淨、豬八戒,前往天竺取經途中的故事。我心想原來這就是《西遊記》啊,結果並不是。在試題的文章裡,沙悟淨似乎思考著什麼。這個水裡的怪物,一個人嘀嘀咕咕沉吟,用深奧難懂的話語,認真探索著悟空的天賦、三藏法師目光前的永恆。我心想這篇有點怪但有趣到不行的文章,究竟是什麼啊?瞬間被吸引的我,把考試拋在腦後,一頭栽進了文章裡。
當時,我不知道是誰寫的,也沒有關於試題...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萬城目學 譯者: 涂愫芸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03 ISBN/ISSN:978957333230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25 開 (14.8cm × 21cm)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
|

 2016/12/22
2016/12/22 2016/11/22
2016/11/22 2016/09/05
2016/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