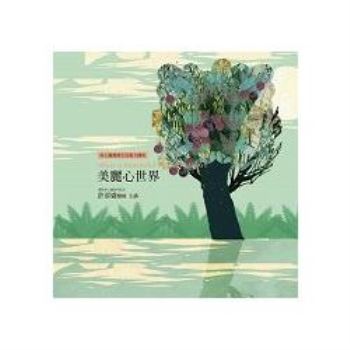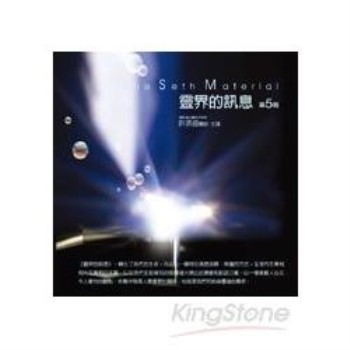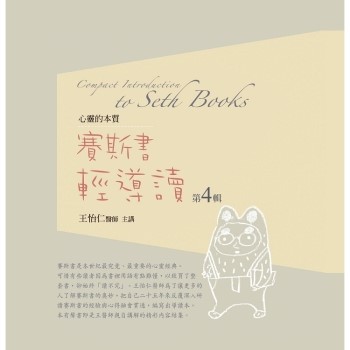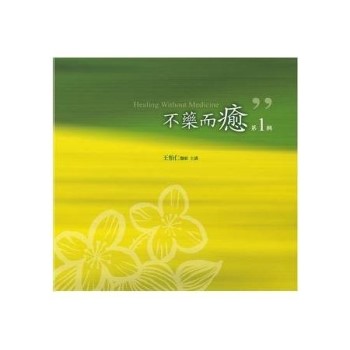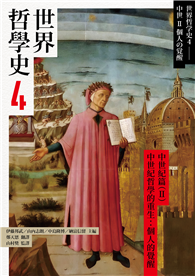一瞬之光
這個傍晚,我外出散步,看見非常美麗的天空。
是那種被稱為莫內藍的顏色,也就是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晚年在接受白內障手術之後,看見了一般人看不見的紫外線,所畫出的藍色睡蓮那種藍。
莫內藍,此刻映入我眼中的天空藍,是黃昏最後的微光,這種不屬於人間的藍色,據說可以直抵人心最幽深之處。
我停下腳步,虔敬地仰起臉,把整座天空看進眼中,收入心底。再過一會兒,這微光就要淹沒在漸深的黑夜之中。這樣的一瞬之光接近一種天啟。身旁不斷有人來來去去,然而沒有人抬頭看向天空,因為他們專注於掌中狹小的視窗,忽略了頭頂之上,那個巨大美麗的藍色視窗。在這樣的當下,彷彿只有我看見了某種神祕的指引,就像一個Just for me的祕密。
在這一瞬間,生命中無數的一瞬一起重現,也一起幻滅。
也是在這一瞬間,我想起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我年紀很輕的時候,我曾經無法在黃昏的天空下行走,因為我害怕看見一日的餘光消失,害怕進入夜色之中。當那樣的光直抵我內心最幽深之處時,總是讓我無法承受。所以我習慣在黃昏時待在室內,並且拉上厚重的窗簾,假裝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
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是「黃昏憂鬱症」,是對於一日將盡的惆悵與失落。
但此刻,我獨自凝視著那同樣是莫內藍的天空,沉浸在它無邊遼闊的寧靜美麗之中,心中卻是充滿喜悅與恩寵。為什麼我的心境如此不同?
或許過去那不是憂鬱,而是對於美在瞬間消逝的不捨與留戀,所以寧可不要看見,因為沒有得到就沒有失去。然而在經歷了人生種種,好的壞的,歡愉的悲傷的,光明的黑暗的,在這一切的發生之後,我已經明白,無常是人生的本質,就像一瞬之光的天空。
生命是無數的一瞬,是一個片刻連著一個片刻,不知什麼時候,我已學會放手讓那些片刻過去,不再留戀也不再回想,不再因為害怕失去而不敢擁有,也不再因為已經失去而憾恨。於是如今我不但能安然地在黃昏的天空下行走,還能駐足欣賞那即將消失的微光,這或許表示我心中對於未知的恐懼已得到了療癒。
在一日將盡的此刻瞥見這一瞬之光,就像在長長的人生裡,無數擦肩而過的機緣中,一次驚鴻一瞥的偶遇與回眸。雖然每一個一瞬終將逝去也正在逝去,或是已經逝去,但我知道,只要我心甘情願地放這一瞬走,這一瞬我就得到了自由。
現在的自己
一個朋友約我看戲。散場之後,我們一起去喝長島冰茶,然後為了把酒醒一醒,沿著深夜的街道慢慢散步。
無人的台北街頭有一種繁華落盡的靜謐氣氛,很適合我們中年微涼的心境。我和朋友認識的時候還很年輕,年輕到人生簡直不算真正開始,後來各自經歷了命運的曲折起伏,有過各種悲歡離合,足夠各寫一部可歌可泣的長篇小說。如今,那些曾經讓我們以為過不去的傷心事終成往昔,再回首時已經皆付笑談中了。
朋友問我,如果時光可以倒流,還願意回到年輕的自己嗎?我說,不,好不容易才走到現在呢,回去做什麼?把走過的路再走一遍嗎?豈不前功盡棄。
年輕的自己擁有大把的光陰和無限的可能,卻也擁有太多的不安與不定,說得好聽是青春飛揚,但同等的意思就是心緒浮躁。那時太容易喜歡別人,也太容易對人失望,太容易相信別人,也太容易因人受傷。那時還不懂得如何與自己好好相
處,常常要拿枝微末節來和自己過不去。那時與人相處也總是驚惶而敏感,擔心犯錯,也果然犯了許多錯,並且付出了不少代價。
現在的自己依然會犯錯,但有了年紀的優勢就是知道怎麼與自己和解,就算還是會低落,也知道如何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得失。比起從前,現在有待面對與解決的難題更多,但看待世情不再非黑即白,已經懂得如何去欣賞人性中的砂礫與人生中的灰色地帶。
我並不懷念年輕的自己,但我接受所有走過的道路,不管那其中有多少錯誤和傷痛,因為是它們成就了現在的自己。那些錯不像臉書上的貼文,寫壞了可以刪除或隱藏,它們是切切實實地發生了,也造成了必然的損傷,但人生本來就不完美,而現在有彈性接受這樣的不完美,知道那就是真實的人生。只要有這樣一個小小的體悟,所有的坎坷就值得了。
生命像一列火車轟隆隆駛過,揚起煙塵,再漸漸沉寂下落,曾經渴望的都得到了,其中有些已失去,另一些也不再那麼重要,所有的狂喜與狂悲宛如一場夢境,過了也醒了。現在的自己不再年輕,卻總算有了一張心平氣和、在任何狀況下都可以微笑的臉。
「所以,比起年輕時的我,我更喜歡現在的自己。」我說。
朋友笑了。「我也是。」他說。
當不再等待別人也不再期待永遠,才終於有了從容與淡定,有了千金難買的自在。我和朋友都同意,那是比起青春美貌更好的東西。
見面
以前想念一個朋友,我們給他打電話,現在想念一個朋友,我們追蹤他的臉書。但還是有些朋友選擇在雲端之外,過著與臉書絕緣的生活,例如Jonson。
Jonson一週有三天在花蓮教書,而我在報社的工作最早也要十點才能下班,兩人的時間要能湊得上並不容易,僅管如此,我們還是每隔一陣子就相約見面,在深夜的小酒館或居酒屋裡,搭配蟹肉煎餅或干貝串燒,以彼此的近況做為下酒的材料,也只有這樣我才能了解他最新的動態,畢竟他不用臉書。
在臉書統治全世界的今天,能安然做臉書王國的化外之民,頗有一種獨釣寒江雪的孤冷,也像堅持自己用捲紙捲菸草一樣,幾乎可說是一種個人風格了吧。
我自己加入臉書的時間也算晚的,若不是因為喜歡大衛芬奇的《社群網戰》,所以才心生好奇,想研究看看臉書究竟是怎麼回事,說不定現在也沒有臉書帳號。因為我總覺得,臉書這種最初只是幾個大學男生在男生宿舍裡惡搞出來的發明,彷彿有著某種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的危險。臉書是一張效益弘大的公眾布告欄,傳遞與交換訊息的速度既快又廣,卻也因此而容易招惹是非,更容易失去個人隱私,所以與它維持安全距離是必要的,私事不能說,心事也不能說,說了十之八九要後悔。
不能告訴臉書的私事與心事,只能告訴值得信賴的朋友了。
但縱使有三千個臉書朋友,真能聽你傾吐心中塊壘的又有幾人呢?
真正的感情,還是得在真實的生活中才能感受。就算與某個朋友在臉書上互動得再熱絡,中間還是隔著終端機的海洋,感覺其實並不那麼精準。畢竟如果沒有近距離地感受到他的氣息、碰觸到他的肢體、看得到他的表情,又怎能聽得到他心裡真正的聲音?
所以,當我因想念某個朋友而去看他的臉書動態時,總不禁要思索,這些輕描淡寫的文字背後還有哪些隱藏的訊息?他快樂嗎?最近好嗎?如果可以的話,還是約出來見見吧。
就像紙本書很難被電子書取代一樣,見面這件事,還是很重要的,情感這種東西,也終究不是在電腦、手機或iPad的兩端想像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氣味、溫度與擁抱,face to face的表情、眼神與微笑,再先進的3C產品也無法製造。見面的當下,那外在的環境與內在的心境所交織而成的感覺與氣氛,後來都會成為偶爾
掠過心頭的回憶,那樣進入心裡的畫面,永遠無法被任何電子產品所取代。
收集三千個臉書帳號,不如有一個可以一起談心的朋友。所以,哪天約他見見面,一起去散散步吧。
重逢
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一個朋友,於是在臉書頁面上鍵入他的名字。很快地,他的照片出現了,當下我沒有太多猶豫,發了一封訊息過去:「還記得我嗎?這些年來,你一切都好嗎?」原本以為只是試試看,沒想到幾乎是立刻,我就得到了他的回覆:「我很好,現在正在安克拉治參加一個醫學會議,過幾天會回台灣,到時見面聊聊吧!」
前後不到五分鐘的時間,串起二十年的失聯,而且他還在遠得要命的安克拉治!在那個奇妙的當下,漫長的時空距離彷彿消失在轉瞬之間。
那是我第一次,或許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在臉書上的尋人經驗,然而也足夠了,我已徹底感受這其中不可思議的強大威力。
臉書讓許多失散的親人故舊重逢,從茫茫人海到茫茫網海,連接起許多中斷的情緣。它是一個人際關係的重整,小學時坐在隔壁的同學、好久不見的鄰居、大學的社團夥伴、以前共事過的同事,甚至初戀情人,都有可能在某天打開臉書時就
忽然出現。而每一回的乍然相見,那種恍若隔世之感,就算只是在雲端,依然令人心底驚呼:啊,這真是太神奇了!
有些網路上的重逢,會進一步成為面對面的相聚,卻也有些尋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相認。
我的朋友M,在網路上找到了多年前的女友,但她可能從未發現,自己從前的戀人是現在的臉書朋友,因為他使用的是英文暱稱,而且個人資料皆未公開;事實上,他設立這個低調的帳號,就是為了尋找她,可是他小心翼翼隱藏著自己,並不希望她認出他來。畢竟這麼多年過去,他雖然還是單身,她卻早已嫁作人婦,就算曾經愛得再怎麼轟轟烈烈,也都是從前的故事了。
「不想再見她一面嗎?」我知道他一直對她念念不忘。
他笑了笑,淡淡地說:「我見到了啊,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他說,只要能安靜地看著她的動態,這樣就夠了。
於是每天晚上,他會進入她的臉書,看她今晚做了什麼菜,看她白天去了哪裡,見到什麼人,發生什麼事,看她假日和先生孩子去哪裡出遊……那就像看著她的窗口亮著的燈火,裡面有她幸福溫馨的生活,但已不是他可以加入的了,然而他的心裡是安慰的。「過去我無法給她的未來,已經有別人給她了。現在的她過得很好,這不是就很好了嗎?」
我點點頭,對於深情的人來說,或許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吧。
有些時候,重逢可能是一個續集的開始,卻也可能是一場毀滅的結果。所以,有些故事,留給從前就好,有些思念,收在心裡就好。
那從未開始的
她一直記得,那個在火車上拿面紙給她擦眼淚的男人。
當時她正坐在南下的火車上,窗外的景色不斷倒退,但她什麼也看不清,因為淚水盈滿她的眼眶,讓她的視線一片模糊。
她坐在靠窗的位子,頭抵著窗,心裡翻滾的全是她的愛貓Nini可愛的身影,但半個小時之前她接到家人的電話,說Nini撐不住,沒等到她就走了,她專程從台北趕回台南老家也見不到Nini最後一面了。
Nini從小與她一起長大,不只是一隻貓而已,還是她的朋友,她的家人。
這幾年她在台北讀書,每次回家都看得出Nini日漸無精打采,畢竟人與貓的時間表不同,她長大了,Nini卻老了。理智上她知道Nini總有一天會離開,但感情上她並不想面對那一天,而現在,她連一句我愛你都來不及對Nini說,就算回到了家,她見到的也只是Nini冰冷的小身軀,想到這裡,她不禁要哭出聲來,但因為極力忍住的緣故,成為低聲的嗚咽。她的肩膀劇烈地顫抖著,像海面的波浪,像波浪止不住的哀傷。
就在這時,她身旁那個男人站起身來走開了,不久之後又回來,手裡拿了一疊面紙,一面遞給她,一面吶吶地說:
「妳哭出聲來沒關係,這裡面紙很多……」
雖然不懂哭出聲來和面紙很多有什麼關聯,但聽到他這麼說,她彷彿得到某種鼓勵,真的就嚎啕大哭起來。
她哭著哭著,一開始是因為失去Nini的悲痛,後來漸漸參雜了其他,關於一個年輕女孩離鄉背井在台北的孤單生活,關於她不順的情感,關於她在學業上努力與收穫的不成正比,她愈想愈多就愈哭愈兇,哭成了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她很久沒有這樣哭了,所以這場大哭是把積壓多年的淚水一次出清。她一邊哭一邊擤鼻涕,面紙不夠用了,身旁的男人又起身去不知從哪兒拿了一大疊來(應該是洗手間?她猜)。她不顧一切,也不管是在火車上,就這樣哭得淋漓盡致,哭到漸漸覺得整個人平靜而放鬆。
「不要擔心,一切都會過去的。」
本來她以為是自己心裡這麼想的,後來才意識到這是身旁的男人為了安慰她所說的話。她總算第一次轉過頭去看他,是個面容清俊的好看男人呢,眼裡寫滿了對她的關心。她對他微微一笑,表示感謝,他也鬆了一口氣似地笑了。
「妳好多了就好了。」他說得那樣真心誠意。就是在這一刻,她心裡某些什麼被觸動了。
然而台南到站,她起身下車,匆匆說聲再見就往出口奔去,雖然急著回家,但她還是意識到那個男人一直在她身後亦步亦趨,然而在驗票口,他被攔住了,她聽見驗票的工作人員說,「你這是到台中的票,已經過站了,你要補票。」
她坐上計程車時,轉頭一瞥,他還在那兒補票。他穿了一件藍格子的棉質襯衫,一條洗白的牛仔褲,高高的個子在流動的人群中給她一種靜止的感覺,在他之上是無盡的藍天,而那一瞥從此也成為她記憶裡的定格。
她這時忽然明白,他是為了她而坐過站的,他早該在台中下車的,卻為了哭泣不止的她而一直陪她坐到台南。她心中一熱,淚又流了下來。她想對他說聲謝謝,但車已往前駛去……
✽
這已是從前從前的事了,但我的朋友卻一直記在心裡。這個故事,我聽她說過不只一次。她每次描述的細節都一樣,可見她在心頭不斷溫習,從未忘卻。
「如果當時我停下來等他,把我的電話給他,就好了。」每次她也總會這麼幽幽輕嘆,「感覺是個好溫暖的人哪,是那種可以相守一生走下去的人,但被我錯過了。」
我的朋友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其中包括一次短命婚姻和幾段痛徹心扉的愛情,但她卻始終念念不忘那個火車上的陌生人,因為那個人出現在她後來的人生之前,他代表了一切後來的坎坷與動盪都還沒發生之前那種無限的可能。或許她的潛意識裡,一直想回到那一天的驗票口前,只要多等他一會兒,說不定她後來的人生就是另一番景況,說不定那些坎坷與動盪就不會發生。
從來沒有開始的戀情總有最多的想像。也因為沒有開始,所以不會有那些過程裡的波折,不會有結束的撕裂與痛苦。那樣的純潔無瑕,就像是裝在水晶瓶子裡的回憶,讓我的朋友每每因為壞感情而壞了心情的時候,就要拿出這個回憶的瓶子搖一搖,彷彿這樣就能得到某種甜美的安慰。
✽
我的另一個朋友則一直記得那個幫她停車的陌生人。
那是在她剛剛拿到駕照時,也是從前從前的事了。那天她開車上路,到達目的地之後,路邊正好有個位子,可是畢竟是生手,她喬了半天還是無法把車子喬進那個停車格,偏偏那又是個單行窄巷,後面一串車子在等她喬好,愈堵愈多,她也愈來愈慌,急得快要哭了。
就在這時,後面那輛車的車主下了車走過來,敲敲她的窗,帶著溫和的笑臉問她,「小姐,我幫妳停車好不好?」
於是她讓出駕駛座,移到一邊,看著那個男人熟練地轉著方向盤,輕鬆優雅地就把她的車停進那個她對付了半天依然束手無策的空位,瞬間解救了她。他有一雙修長好看的手,一雙充滿男性力量的手,她覺得那雙手放在她的方向盤上,再適合也不過了。
然後他轉過頭來,幽默地說,「以後停不進格子裡的時候,就打電話給我,反正我都在電話亭附近。」他用的是電影《超人》的梗。
多年之後,她想起來還是惆悵,為什麼那時只會紅著臉微笑,卻沒有順勢問他的電話號碼呢?「然後我就可以藉由感謝的名義,約他出來喝杯咖啡,說不定後面會有故事。」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臉上竟有一種天真少女的表情。
雖然那杯咖啡從不存在,但她後來的每一段感情,都是從手開始的,如果男人有一雙修長好看的手,就會讓她充滿安全感,然後才會讓她產生愛的感覺。她一直記得他那雙方向盤上的手。在不知不覺當中,一個陌生人成為她心上的幽靈,幽微地影響了她情感上的命運,這或許也算是後面的故事吧。
那些從未開始的,往往是影響最深遠的。雖然她早已過了相信王子公主故事的童話年齡,但在內心深處,或許還是期待著一個可以把她從混亂之中解救出來的男人。
✽
而我一直不能忘記的,是那個彈吉他的鄰家男生。
那時我還是個高中女生,而他已經是個大學生了,他的窗就對著我的窗,每天晚上,當我挑燈讀小說的時候,他的窗常常是黑的,顯示無人在家,大學生的生活多采多姿,與苦悶無聊的高中生是天壤之別;而當那扇窗亮著的時候,總見他抱著一把吉他在那兒隨興所至地自彈自唱。他喜歡唱Simon and Garfunkel、Dan Fogelberg、Eagles的歌,歌聲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窗就對著我的窗,那給了我無限的想像。這時我會掩上窗簾,莫名地心跳臉紅,假想著那些歌都是為了我而唱。
但當然不是,我想他根本沒有意識到我的存在吧。
其實我甚至沒有和他說過話,他的模樣對我來說也很模糊,不過是個窗前的剪影,如果在街上遇到了,也許我還認不出他來。然而他的歌聲穿透過許多個夜晚,落在一個生命經驗貧乏的高中女生心上,滋養了情竇初開的花。
於是當我自己也成為一個大學生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去學吉他。
我必須承認,很長的一段時間,會彈吉他的男人特別令我心動,直到現在,吉他還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樂器。吉他的弦聲總會讓我想起那些浮想翩翩的夜晚,那些苦悶憂傷又單純的青春時光。
那些從未開始的,才是最純淨的,不會被「後來」汙染。它已停留在某個從前從前的遙遠的過去的時空裡,成為一種永恆。
✽
張愛玲有一篇散文,寫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某個春天的晚上,她穿了一件月白的衫子,在自家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對面那個從來沒打過招呼的年輕男人走了過來,輕輕說了一聲,「噢,妳也在這裡嗎?」就只有這樣一句話,卻讓她記了一輩子。「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這篇文章全文只有三百四十五字,非常簡短,卻綿延了一個女子的一生。而張愛玲給它下的標題是〈愛〉,如此輕盈卻也如此隆重,愛。她的小說裡向來只有千瘡百孔的現實人生,從未說愛,卻是在這篇散文裡,那偶然的一瞬間,那從未開始的,那後來再也沒有後來的,她說,那是愛。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花開的好日子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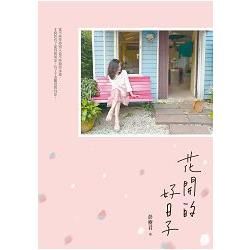 |
花開的好日子 作者:彭樹君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花開的好日子
當不再等待別人也不再期待永遠,
才終於有了從容與淡定,
有了千金難買的自在。
天空沒有邊緣,卻以它的空無涵蓋了一切,心也不該有任何設限;
而土地像是永恆的召喚,如果還沒見到某種風景,只是因為走得不夠遠。
如果我的心像天空一樣自由,包容一切卻什麼都不執著,
我就可以進入心靈的秘境,走向更深的內在旅程。
如果我的心夠安靜,我就能在無人的樹林裡聽見花開的聲音。
生活中每個瞬間都是花,突如其來、不請自開。
為了不讓其僅此一現,
彭樹君彷若時光的採集者,細膩觀察,耐煩揀拾,
她從漫漫的生活河流裡,掏出以時間為名的金色流沙。
那些記憶中的日常時光,生活上的轉瞬之間,
人際間的情感攻防,過往裡的人生故事……
有遺憾,也有美好;有失落,也有溫暖。
我們才終於明白,那些美好與溫暖終能讓我們微笑釋懷,
只要帶著一份溫柔,
每一刻,都能聽見花開的聲音,
每一天,都是花開的好日子。
作者簡介:
彭樹君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得過許多文學獎,擔任過廣告公司企畫撰文、女性雜誌資深編輯、文學雜誌採訪主任,也曾主持深夜廣播節目,目前為報社副刊主編,用本名寫小說與散文,以筆名「朵朵」寫朵朵小語。
22歲出版第一本書,至今有小說、散文、札記、採訪集等二十幾本著作,以及十九集《朵朵小語》。寫作的養分來自於閱讀、音樂、電影、旅行、蒔花弄草、觀察人生百態,以及苦甜交織的生命本身。文筆清麗細膩,對於種種人生況味往往深入幽微,尤其擅長描寫女性曲折情思,字裡行間總有溫柔撫慰的療癒光芒。
歡迎光臨──
彭樹君的創作花房:sky7272.pixnet.net/blog
彭樹君的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lightriver
朵朵小語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duoduo
TOP
章節試閱
一瞬之光
這個傍晚,我外出散步,看見非常美麗的天空。
是那種被稱為莫內藍的顏色,也就是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晚年在接受白內障手術之後,看見了一般人看不見的紫外線,所畫出的藍色睡蓮那種藍。
莫內藍,此刻映入我眼中的天空藍,是黃昏最後的微光,這種不屬於人間的藍色,據說可以直抵人心最幽深之處。
我停下腳步,虔敬地仰起臉,把整座天空看進眼中,收入心底。再過一會兒,這微光就要淹沒在漸深的黑夜之中。這樣的一瞬之光接近一種天啟。身旁不斷有人來來去去,然而沒有人抬頭看向天空,因為他們專注於掌中狹小的視窗,忽略了頭...
這個傍晚,我外出散步,看見非常美麗的天空。
是那種被稱為莫內藍的顏色,也就是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晚年在接受白內障手術之後,看見了一般人看不見的紫外線,所畫出的藍色睡蓮那種藍。
莫內藍,此刻映入我眼中的天空藍,是黃昏最後的微光,這種不屬於人間的藍色,據說可以直抵人心最幽深之處。
我停下腳步,虔敬地仰起臉,把整座天空看進眼中,收入心底。再過一會兒,這微光就要淹沒在漸深的黑夜之中。這樣的一瞬之光接近一種天啟。身旁不斷有人來來去去,然而沒有人抬頭看向天空,因為他們專注於掌中狹小的視窗,忽略了頭...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推薦序】
聽見花語
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郭強生
跟樹君很早很早以前就結識了,早在還不懂文學是什麼的當年,我們就只是開心地在寫,順利地出了書。幫我們出書的那家出版社,當時網羅了一群像我們一樣年輕的孩子,與所謂主流文壇形成了對壘,因為這群「風花雪月」的校園作家,每本書都以一個月再刷一次的銷售速度迅速竄起而飽受批評。然而,那段搭上了台灣出版盛世的黃金歲月,不過短短兩三年,我們隨即就奔往人生的下一個目標,繼續求學的繼續求學,正式進入體制的進入體制,結婚的結婚,出國的出國……焉知,那樣...
聽見花語
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郭強生
跟樹君很早很早以前就結識了,早在還不懂文學是什麼的當年,我們就只是開心地在寫,順利地出了書。幫我們出書的那家出版社,當時網羅了一群像我們一樣年輕的孩子,與所謂主流文壇形成了對壘,因為這群「風花雪月」的校園作家,每本書都以一個月再刷一次的銷售速度迅速竄起而飽受批評。然而,那段搭上了台灣出版盛世的黃金歲月,不過短短兩三年,我們隨即就奔往人生的下一個目標,繼續求學的繼續求學,正式進入體制的進入體制,結婚的結婚,出國的出國……焉知,那樣...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前言】
但願天天都是花開的好日子──彭樹君的自問自答
這本《花開的好日子》是怎樣的一本書?
這是我的散文集,分成三個部分:〈Moment〉是許多一瞬,一些偶然的片刻;〈Facebook〉寫臉書的世界,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靠近與疏離、熱情與寂寞;〈Memory〉寫生命中的過往,以及失落與領悟的故事。
這些文章是成書的時候才做這樣的分類,但在書寫的當下,很像是忽然開出的花,沒有什麼事先的計畫。
更多的時候,靈感就像天邊過境的飛鳥,如果沒有立刻寫下來,一眨眼就不見牠的蹤跡了。
所以當片段的創作文字成為具體的一本書時,我總...
但願天天都是花開的好日子──彭樹君的自問自答
這本《花開的好日子》是怎樣的一本書?
這是我的散文集,分成三個部分:〈Moment〉是許多一瞬,一些偶然的片刻;〈Facebook〉寫臉書的世界,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靠近與疏離、熱情與寂寞;〈Memory〉寫生命中的過往,以及失落與領悟的故事。
這些文章是成書的時候才做這樣的分類,但在書寫的當下,很像是忽然開出的花,沒有什麼事先的計畫。
更多的時候,靈感就像天邊過境的飛鳥,如果沒有立刻寫下來,一眨眼就不見牠的蹤跡了。
所以當片段的創作文字成為具體的一本書時,我總...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彭樹君
- 出版社: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06 ISBN/ISSN:978957333241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開數:25 開 (14.8cm × 21c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16/07/14
2016/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