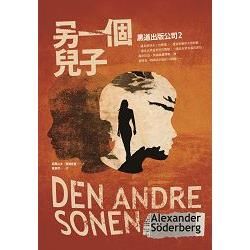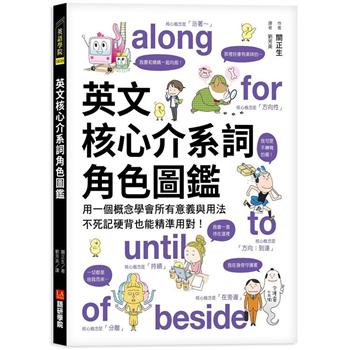為了生存,為了復仇,為了愛,
她必須喚醒自己心中的黑暗……
她必須喚醒自己心中的黑暗……
女性版的《無間道》+《教父》!
直追《龍紋身的女孩》!北歐犯罪小說的最高傑作!
一邊是餘情未了的舊愛,一邊是患難與共的新歡;
一邊是比黑道更黑的警察,一邊是有情有義的罪犯;
蘇菲知道,無論她選擇哪一邊,
都將是一條無法回頭的不歸路……
原本只是單純的單親媽媽,但自從愛上黑道大亨赫克特後,蘇菲也身不由己地捲入各方勢力的危險漩渦中。
蘇菲被古妮拉警官脅迫當線人,卻發現她是披著羊皮的狼,其實是瑞典警局裡最腐敗的黑手,反而赫克特的黑幫家族對她有情有義。蘇菲決定不再對警方據實以報,古妮拉卻拿她的兒子艾伯特的性命要脅。
另一方面,赫克特和蘇菲的舊情人詹斯、赫克特的死對頭漢克家族,以及俄羅斯黑手黨,多方人馬在特哈斯登餐廳意外爆發一場激戰,赫克特因為遭到好友背叛,身受重傷,被秘密送往西班牙避難療傷。
槍戰之後過了六個月,赫克特的父親和弟弟相繼被漢克家族暗殺身亡,蘇菲不得不成為赫克特的代理人。她四處奔走,力圖穩定大局,沒想到艾伯特卻在此時遭到漢克家族綁架!
為了救出艾伯特,並結束這一連串腥風血雨,蘇菲偷偷前往德國去跟漢克家族談判,並在詹斯的協助下,找到了可能藏匿艾伯特的農場。然而蘇菲在那裡卻並未發現艾伯特的蹤影,只看到一位與艾伯特年齡相近的男孩,而且那個男孩的容貌竟然與赫克特十分相似……
好評推薦
亞歷山大‧瑟德貝里最驚人的作品之一!《黑道出版公司》的精采已超乎我的預期,如同黑幫的警察,猶似貴族的罪犯,瑟德貝里創造了一個極具娛樂性,而且又奇妙、刻薄的世界。作者是位偉大的說書人,就是這麼簡單!──《禁入廢墟》作者/史考特‧史密斯
作者深諳跨國犯罪組織的運作精髓,精采緊湊的情節,如臨現場的對話,緊張又幽默,閱讀過程更令人亢奮!──《凱特任務》作者/克里斯‧帕馮
當今最耐人尋味的驚悚劇!以飽和細膩的色彩與極簡的黑白速寫所成就的一部北歐犯罪小說!──《推理現場》雜誌
一部關於殘酷黑道的故事,瑟德貝里對角色的刻劃不僅用心,也深具同情心,情節流暢又精采!──《書頁》雜誌
最優秀的作品!最精采緊湊的劇情!──出版家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