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所知道的每件事,
都是謊言……
劇情發展完全超乎預期!Amazon讀者★★★★☆(4顆半星)好評不斷!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是謊言……
劇情發展完全超乎預期!Amazon讀者★★★★☆(4顆半星)好評不斷!
但不僅僅是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事,
而是「關於你」的事,
他們希望你永遠不會知道……
凱洛琳的人生在一夕之間幡然改變。她舉起手摸了一下脖子後方,醫師驚訝的聲音依然在耳畔回響:怎麼會有顆子彈卡在妳的脖子裡?!
在大學裡教授法國文學的凱洛琳,近來飽受手腕疼痛之苦,她去醫院做了核磁共振檢查,沒想到竟發現脖子裡埋著一顆點三八子彈。凱洛琳的記憶中從未遭到槍擊,那這顆子彈究竟從何而來?
在凱洛琳不斷地追問下,她的父母終於吐露了驚人的真相:凱洛琳其實是他們領養的孩子,她的親生父母在她三歲時遭人殺害,兇手至今依然逍遙法外,而當時脖子中彈的小凱洛琳雖然奇蹟似地倖存下來,卻因為子彈太靠近神經和血管無法取出,只好一直留在她的身體裡。
深受衝擊的凱洛琳頓時陷入「自己是誰」的迷惘裡,為了找尋消失的過去,她重新回到了三歲前的老家亞特蘭大,並赫然發現,她脖子裡的那顆子彈,正是解開父母遇害真相的關鍵線索,而這也將是一場充滿危險的競賽:她必須在兇手找上她之前,先找出真正的兇手……
好評推薦
這顆子彈直接打中了我!全書充滿獨特的風格與智慧,情節安排巧妙流暢,直到最後一頁!──前CIA探員/瓦萊麗‧普萊姆
瑪麗‧露易絲‧凱莉的《在我脖子裡的那顆子彈》是一個難以抗拒的陷阱,一連串絕妙的布局讓人直到最後都喘不過氣來,然後迎向那個以自信、沉穩的手法所披露的結局。這是一本魚與熊掌兼得的作品,讓人心滿意足。真希望我能擁有時光機,這樣就能把書中驚人的點子據為己有!──《三墳俱滿》作者/潔米‧梅森
高潮迭起的劇情,充滿浪漫的感觸,再結合「女主角是誰」的驚喜感,創造了一個深具想像力,並超越哈蘭‧科本的驚悚故事!──《書單》網站
《在我脖子裡的那顆子彈》敘事手法令人喜愛,故事曲折多變,既是驚悚小說,也是醫學謎案,同時也在探究我們究竟有多了解所愛的人。──《肢解記憶》作者/愛麗絲‧拉普蘭
瑪麗‧露易絲‧凱莉完成了艱難的成就,她在挑戰可信度的界限中,寫出這本引人入勝、教人欲罷不能的作品!──出版家週刊
劇情峰迴路轉又引人入勝,正中目標!──《深夜好眠》作者/海莉‧艾弗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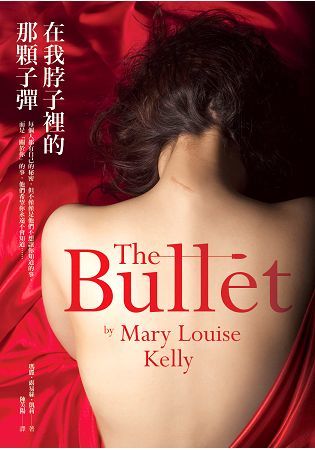
 2017/11/06
2017/11/06 2016/11/29
2016/11/29 2016/09/25
2016/0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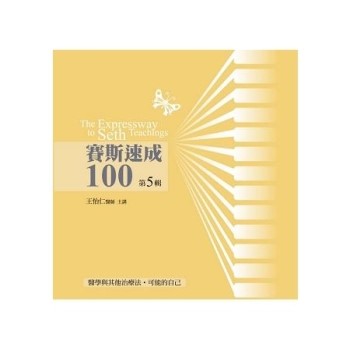





![114年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國民營事業] 114年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