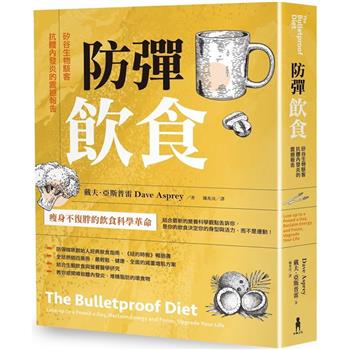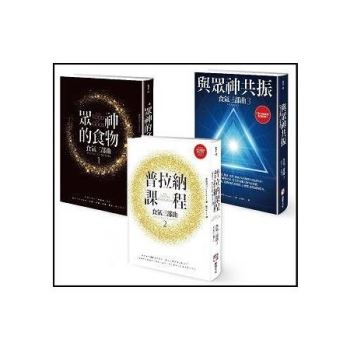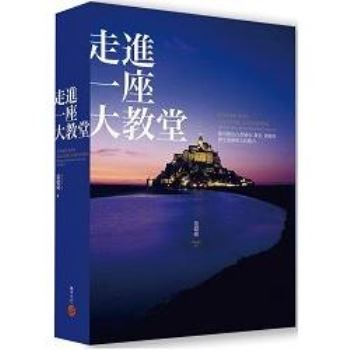我們都是被囚禁在時間線上的旅人。
神之布局,鬼之妙筆!
文壇奇才張草構思多年,重磅出擊,
徹底顛覆你對生死的認知!
殺人很重要,
按「程序」執行更是重要。
兇手是常數,被害者是變數,
只有精準的執行,才能得到完美的解答。
手臂畸形彎曲、皮膚滿布爛瘡、身體歪扭佝僂、聲音嘶啞難聽,他的靈魂被拘禁在悲慘的軀殼裡,苟延殘喘地遊走在這個世界的邊緣。遭人歧視地活著,落寞孤獨地死去,似乎就是他難以逃離的宿命。
然而某一天,他的生命卻出現了驚人的變化。一個年輕女孩車禍身亡、左臂折斷後,他扭曲的手臂也不藥自癒!九歲小男孩跌落糞坑溺斃,他身上的惡瘡就突然一夕消失!那些看似偶然的意外,竟讓他的痼疾莫名痊癒。
於是,他開始踏上執行「必要程序」之路。首先,他割斷了一位服飾店員的頸動脈、切開一個大學女生的手腕,接著毒死了資深鑑識官、打爆老榮民的頭顱……隨著殺死的人數越多,他身上的「問題」就越少,而鏡子裡的他,也慢慢變成了「另一個人」……
究竟他與這些死者之間有什麼關聯?他們的死,又為何能夠換來他的浴火重生?警方緊咬著線索,卻始終無法觸及核心,因為所有的人還不知道,想要解開真相,就必須先破解如數學般縝密的「殺人程序」……
作者簡介:
張草
第三屆「皇冠大眾小說獎」首獎得主,他以《北京滅亡》獲得評審壓倒性的青睞,並與之後的《諸神滅亡》及《明日滅亡》構成「滅亡三部曲」,成為華文科幻的經典之作。
張草成長於馬來西亞沙巴州,從小就廣讀群書,被戲稱為「人肉百科全書」,初中三年級即以超齡之姿贏得馬來西亞丘陶春盃文學獎公開組冠軍。後赴台灣就讀台大牙醫系,二十四歲在《皇冠雜誌》發表《雲空行》系列,一鳴驚人,之後即創作不輟,並致力於各種小說類型的創新,他的極短篇《很餓》、《很痛》、《很怕》,以及奇幻靈異作品《雙城》也均備受好評。「庖人三部曲」──《庖人誌》、《蜀道難》、《孛星誌》則是張草前後耗時十二年才終於完成的代表作,並開創了「職人武俠」的新風格。其他作品還有《啊~請張嘴:張草看牙記》等。
目前張草一邊回鄉開業當牙醫,一邊參加合唱,至於手上的小說計畫,則據說再寫二十年也寫不完。
臉書專頁:張草菜圃
章節試閱
x=0雪筠
雪筠人如其名,長得白白淨淨的,皮膚不需許多保養,就總是毫無瑕疵的白皙。老實說,她的五官也不是挺美,沒有一對烏黑閃亮的大眼,沒有鼻樑高挺的鼻子,但所謂一白遮三醜,她只消燦爛的笑起來,就是人見人愛,沒有人不感受到她的魅力的。
但是,她死了。
一月,春天未至,冬天的寒風仍在肆虐時,晨跑的婦人發現她安靜坐在社區小公園的椅子上,兩眼失去張力的半合著,皮膚白得比平日更白,不過是完全失去血色的慘白。
晨跑的婦人覺得有異,因為她是認識雪筠的,這位十九歲的小女生總是很熱心幫助周遭的人,每個人都會記得她那沒有一絲心機的笑容。今天早晨的她一臉呆滯,但是,坐在椅子上的她不像在等人,也不像睡著了,而是……婦人有一番年紀了,親族的葬禮也參加過很多場了,雪筠的表情,就跟那些被瞻仰的遺容沒兩樣:沒有張力的表情肌,放空了的眼神……她死了。
婦人晨跑經過社區小公園時,望見坐在長椅上的雪筠,見她的臉斜斜面對公園內的花叢,原本只是想跟她打個招呼,因為她打從心裡喜愛這名熱心的可愛女孩。當她發覺雪筠可能已經死亡時,她心中產生一絲憐憫,於是大膽的湊前去,將兩指伸到雪筠鼻子前方,確定沒有鼻息了,再將同樣的兩指按壓在雪筠耳朵下方的脖子上,確認沒有脈膊了。
婦人大膽的進一步觀察:雪筠穿著長至膝蓋的白色大衣,腳穿長筒皮靴,脖子圍著羊毛圍巾,兩側垂下的卷曲長髮也遮住了脖子,她還戴了羊毛手套和帽子,說明昨晚很冷,因為有氣象預報寒流會來襲,理應今早才會轉冷的,但寒流不會聽氣象預報的話,昨晚的確提早降臨了。她穿著這麼厚實的重重衣服,應該不可能是冷死的?但婦人看不見她身上有傷痕,也沒見血跡,或許是衣服擋住了也說不定。
婦人於是兩手合掌,口唸阿彌陀佛:「小雪,你等著,阿姨找警察去。」她輕輕拍了拍雪筠冰冷的手背,便奔跑向附近的派出所。她生怕別人也發現了雪筠,會對雪筠的屍體不敬,或是會破壞現場,心中可是焦急得很。
「這麼好的女孩,為什麼這樣歹命?」婦人邊跑邊想,「不能讓她受到屈辱!」
婦人離開小公園時,有一對冷漠的眼神目送她離去。
婦人穿著粉紅色的緊身褲,在灰色的清晨很容易辨認,他見婦人跑遠了,那抹粉紅色在視野中消失了,那人才踱步到社區小公園的外面,但嚴謹的不踏入小公園的範圍。他拉起大衣的高領,拉低帽子的邊緣,一方面阻擋寒風,一方面不讓人瞧見他的臉孔。
他手中輕揉著暖暖包,一邊感覺暖暖包傳進手心的熱量,一邊望著清冷的街道,留神公園對面的住家,有沒有人從樓上張望下來,有沒有趕路的學生揹書包經過。
哦,沒有!因為他刻意選了星期日的清晨,沒有學生也沒有上班族會早起的星期日清晨,他選擇這個時間,為的正是不要有太多人會接觸到屍體,只有晨跑族才有發現屍體的可能。因為,他也不想這位少女的屍體遭到瀆辱。
事實上,他之所以站在小公園外頭,就是要保護少女的屍體,在晨跑的婦人帶著警察回來以前,確保少女不要受到打擾。
他弓著從來直不起來的背,跟雪筠背對背坐著,想像著少女如同一具巨型的洋娃娃,優雅的坐在公園長椅上,背景是一片落了葉的樹叢,伴著冷灰色的底色,構圖淒美極了。回想昨晚,他好不容易將雪筠擺好在長椅上,撐直她的背,將她的手放在漂亮的位置,整理好她的衣服和頭髮,務使她早晨被人第一眼發現時,是美美見人的。
他望著空無一人的周圍,想著雪筠的靈魂,此刻是否正在困惑的望著自己的屍體,然後轉頭發覺站在小公園外面的他,走向他,凝視他……他感到背脊一涼,猛然回身離開,大踏步走進小公園旁的小巷,遠離現場。
同一時刻,晨跑婦人帶著警察,在街角轉彎處現身。
分秒不差。
因為他早就知道了。
知道一切。
x=1飛鵬
上午十點,距離少女雪筠的屍體被發現已經過了四個小時,偶爾在灰濛天空中露臉的太陽,對溫度的提升一點幫助也沒有。
社區小公園外圍了很多人,打算在星期日上午出門的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打亂了步調,紛紛停步詢問先來圍觀的人,是出了什麼事沒有?記者猛按公園旁邊住家的門鈴,在對講機上很客氣的詢問能不能進去?希望能從高處瞰拍到構圖不錯的照片,好在八卦雜誌全頁登出。
警方的黃色警戒帶包圍了社區小公園,不准任何無關人士進入,免得踩踏地面,弄損現場遺留下的微小線索。由於黃色警戒區內的人員不多,相較於圈子外的擁擠,圈子內顯得十分空曠,警方人員可以自在的活動。
一位初老的男子半跪在地面,端詳雪筠的兩隻手,一隻穿了羊毛手套,另一隻手套已經被先來的鑑識人員拿下,封存在長椅旁的一個塑膠證物袋內。他用戴了乳膠檢驗手套的手握著雪筠兩手,將兩手比對了一下,遂將另一隻羊毛手套小心取下,再把眼睛貼近她的手背,細看皮膚的顏色,看了一陣,最後男子乾脆脫下乳膠手套,用手直接觸摸雪筠的皮膚。
他是資深鑑識人員,今早本來約了唸大學的兒子去登山的,沒想到主任一通電話打來,說需要他出馬一趟。
他有預感,這個星期日的假期是要泡湯的了。
「剛才是誰檢查的?」
「老師,是我。」身旁那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慌忙舉手,他甩個頭示意年輕人過來,年輕人便趕緊跪在他身邊。
這年輕人習慣稱呼他老師,也對,年輕人是他一手帶進鑑識組的,跟過他冒著風雨檢驗屍體,經過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可說是身經百戰,練就了很強的觀察力,漸漸已經能夠自立。所以若是年輕人要求他親自前來,他就有心理準備,要不是會面對難解的案件,就是有趣的案件。
「小吳,」他翻過屍體的兩手,讓雙手掌心朝上擺在大腿上,給年輕人看清楚,「兩隻都有。」
小吳神色凝重的皺緊眉頭,望著屍體兩隻手腕上深深見骨的切口:「很乾淨。」
「太乾淨了,連血跡都沒有,」老鑑識人員把鼻子湊近手腕的切口,用力嗅了幾下,「有用酒精清理過,很淡的氣味。」空氣很冷,通過鼻腔的冷空氣把嗅神經麻痺了,也刺激了鼻水分泌,所以鼻子比平常來得不靈敏。
兩隻手腕被切開這麼深的切口,衣服和地面竟連一點血跡也沒有,兩人心照不宣,這個社區小公園絕對不會是第一現場。
「我聽老師說過那個故事,所以才想……」小吳語帶保留。
是的,他是說過,所以這是個有趣的案件嗎?
他告訴過受他訓練的員警們,一個他在美國受鑑識訓練時聽過的案件,這具少女屍體令小吳聯想起那個案件,是當然的事。
老鑑識人員忽然間有個靈感:「小吳,周圍的照片,都拍下了嗎?」
「拍了。」小吳揚了揚掛在胸前的專業相機。
「我要你拍三百六十度,」他伸手在空中劃過,比劃他所要涵蓋的範圍,「四方要三百六,上下也要三百六。」
「馬上。」小吳興奮的站起來。
「把這女孩也拍進去,」他指指雪筠的屍體,「我要拍下她跟四周的相對關係。」
小吳忙著拍攝的時候,一位老刑警走過來問候:「老李,怎麼樣?」
老鑑識人員姓李,名飛鵬,跟打招呼的老刑警是同期,只不過在警察學校的訓練中,李飛鵬轉了個彎,轉去走刑事鑑識這條路,還被派去美國特訓,回國後又幫忙破了不少案件,所以在警界中很有分量。
李飛鵬告訴老刑警:「等小吳拍完了照片,先把這女孩帶回去……運屍車來了嗎?」
「在外頭,等你吩咐,就開進巷子來。」
李飛鵬點點頭:「現在,我不知道的還比知道的多,很多要帶回去了,才可以分析。」
老刑警猜他說的是溫度。
這位死者死在大寒天的外頭,照理說體溫會降得很快,但她又穿了很厚的昂貴大衣,連手腳都有保溫,只有一小張臉露在寒冷的空氣中,所以體溫的測量變得困難,對於死亡時間的推算也增加了許多變數,此時,大概只有死者的肛溫最能提供幫忙,不過他們總不能大庭廣眾的測量肛溫。
「那我現在叫他們開進來好了。」
「麻煩你了。」
老刑警擺擺手,便回頭叫屬下去呼喚運屍車。
李飛鵬站起來,輕輕拉開雪筠半合的眼瞼,用小手電筒照看她放大了的瞳孔,看看眼白上的血絲,此時,貼近雪筠鼻子的他聞到熟悉的氣味,是薄荷糖的人工香精味,不,還有一種……
「那邊的,」他指向另一位正在採集指紋的鑑識人員,「漢明是嗎?」
「偉明,老師,」那人糾正他,「有什麼吩咐?」
「採集死者的鼻黏膜,要化學分析。」
「是。」
李飛鵬不用分析也知道是什麼,但任何發現都必須要寫報告,所以程序還是免不了……這種氣味太熟悉了。
氯仿,這是那種氣味的正式化學名詞,民間直接音譯為哥羅芳,就是犯罪電影中用來倒在手帕掩去人家鼻子就會暈掉那種。
事實上,要是用量太多的話,可是會讓人死掉而不是昏迷的,以前中學上實驗課要解剖老鼠,就是把老鼠扔進放了氯仿的水桶裡去,然後將蓋子蓋上,等老鼠不再發出掙扎的聲音了,才拿出來切開胸膛,觀察心臟的跳動。
有時候,氯仿放得太多,老鼠的心臟早就不動了。
李飛鵬挺起身體,退後兩步觀看。
少女的屍體一如解剖板上的白老鼠,姿勢被細心的擺得好好的,像是準備要拍照的模特兒。她的背景被一片矮樹叢像兩手般環抱著,雙腳輕柔的放在能夠讓泥土呼吸的空心水泥磚上,腳邊還有大花盆,種植了較大棵的景觀植物,而她半合的雙眼彷彿等人等累了,正想小睡一下。
李飛鵬忽然一陣暈眩。
他當下以為是剛剛嗅到了一點氯仿的緣故。
不,他似曾相識。
Déjà Vu,法文,似曾相識,正式名詞是「既視感」。一種突如其來的熟悉感,明明是現在面臨的事件和場景,卻彷彿一切曾經經歷過,發生過,而現在又猛然想起。
李飛鵬穩住身體,直視長椅上的少女,那股熟悉感更加強烈了,不像是剛剛發生的,反而是打從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經熟悉這一刻的存在了!
他走近少女,將她腳邊的大花盆推斜,伸手到大花盆底下,摸出一個沾了泥土的零錢包,可以兼放證件的那種。
老刑警驚訝的望著他。
李飛鵬打開零錢包,取出幾張證件:機車駕照、大學學生證、悠遊卡、書店會員卡,還有一張美妝店的集點卡。證件照片上的少女是死者沒錯,今年十九歲的大學生,比他兒子小兩歲而已。
他把證件連同零錢包一起遞給老刑警時,忽然覺得自己莫名其妙的好累,不禁連連打起呵欠來,他摀著嘴巴說:「她名叫莊雪筠……」
老刑警接過東西,說:「我們早就知道了。」他端詳證件上少女的笑容,清秀的淡淡微笑,像被攝影師逗得很高興似的,很討人歡喜,「這周圍看熱鬧的人之中,大概有一半的人認識她。」
「她住這附近嗎?」
「不是,」老刑警說,「但發現屍體的女人認識她,還告訴我,她是一位很熱心助人的好女孩。」
李飛鵬像神遊太虛一般,愣愣的望著老刑警。
老刑警按捺不住滿腹狐疑,他揮揮手中少女的零錢包和證件,咬著牙問道:「你怎麼知道這東西壓在花盆底下?」
「我就是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知道。
「老李,最好是這樣,」老刑警繃著臉說,「要不是你我相識多年,我會懷疑你是兇手。」
圍觀的人之中,有個人在看見李飛鵬抬起花盆的那一刻,滿意的點了點頭。
看見了他需要看見的那一幕之後,便毫不戀棧的離開人群,他吃力的挺起緊繃的背部,不想給人注意到他的異常。巷口轉角有家快餐店,他打算在快餐店的早餐時間過去之前,去吃個乳酪貝果早餐。
張國棟驚醒時,全身泡在汗水裡頭。
心臟像個高速運轉的引擎般,激烈撞擊胸口,有如要衝破肋骨掙脫出體外。
他踢開棉被,像要溺水窒息的人一般用力喘氣,第一時間拿起放在床頭的手錶來看時間。
十點半,太晚了,鬧鐘沒響嗎?
他例常會在星期日早晨享用的快餐店早餐,已經剛剛結束供餐了,店員們一定已經取下早餐套餐的展示牌,換成平日供餐了。
待沉重的心跳稍微減慢下來之後,張國棟開始回想,是什麼原因令他驚醒?是因為惡夢嗎?如果真有作夢的話,他可是一點也想不起來。
天氣真的很冷,即使宿舍的窗口是緊閉的,寒意依然透過窗戶的玻璃一陣陣傳入。他知道他汗濕了的身體很快便會發冷,他打了個哆嗦,知道即使蓋回棉被也沒用,因為連棉被也是濕的。
他打算爬到床下去換件衣服。
下床之前,他掃視了一遍房內的室友,這裡一如尋常的大學宿舍,一房四人,每人分配到一個角落,上舖是床,下舖是生活讀書的空間。床位靠門那兩位,一位仍在呼呼大睡,發出安詳的打鼾聲,另一位是台南人,前天下午下課就跑回鄉下了,那傢伙幾乎每個星期都回台南,估計明早才回來,因為他要十一點才有課。跟張國棟同樣睡靠窗的那位也不在床上,被單如常一片紊亂,不知道是出去玩了還是只是走出了房門而已,國棟探頭望到對面床下的書桌,背包不在,嗯,是出去玩了。
張國棟爬下不鏽鋼梯子,走到床底下的位置,那兒是他書桌和衣櫃所在,他在床的下緣夾了一塊大布,以便能在需要時拉上,用來隔開外界,可以專心讀書,不需要時拉開,可以通風,同時跟室友們打屁聊天。
他拉起布幕,隔絕了冷空氣,才脫下被汗濕透了的衣褲,打開衣櫃,從一堆昨天剛晾乾尚未折好的衣服之中挑出一件厚T恤,旁邊是另一堆折得整整齊齊的衣服。自從他交上女朋友之後,才開始留意衣服上有沒有過度的皺痕,才開始養成將衣服好好折起來的習慣。
不過,昨晚他約會回宿舍之後,由於太晚太累,精神又一直不安,所以在刷過牙之後,在宿舍洗手間旁邊的室內晾衣場收起晾乾的衣服之後,才剛鑽進被窩就一覺睡到剛才起床了。
他老是覺得有些不對勁,卻又說不上來為什麼?
他找到書桌上的手機,還連接著充電器,手機當然已經充飽電,但他還是看了一眼確定,才拔開充電線,習慣性的看看螢幕上有沒有未接來電或是訊息,沒有,沒人找他。於是,他撥打女朋友的號碼,打算跟她道個早安,順便看看今天要不要去哪兒逛街?或許他的女朋友又要去哪裡當義工,他也會去陪她,自己也從旁協助,他覺得這還挺有意義的,比膩在一起卿卿我我還有意思。
女朋友的手機在那頭響了,他等待著,通常沒響幾下她就會接了,但今天,也響太久了,難道她也還沒起床嗎?不可能的,她習慣早起。
他等到那頭的鈴聲停止響了,發出轉接到語音信箱的聲音時,便掛斷了電話。等一等吧,女朋友通常會打回來的,不管有多忙,她很少不回電的。
果然沒等多久,手機響了,是她的號碼沒錯,就說了會打回來是吧?
他趕忙按下接收鍵,滿心期待聽見她甜美開朗的聲音:「喂?」
手機另一頭是一陣沉默。
他聽見另一頭的背景聲音,是室外空間,有汽車來來回回,有一些路人的細碎談話聲,還有手持電話的人帶有吸鼻涕聲音的沉重呼吸。
張國棟心裡涼了一截,他繼續對另一頭說話:「喂?喂?是誰?為什麼不說話?」一股濃濃的焦慮即刻包圍了他的心房,整顆心彷彿瞬間跌到了谷底,他加大了聲量:「你是誰?!」
對方終於說話了:「你是張國棟嗎?」是一把男人的聲音,輕輕柔柔,很和氣的聲音,但聲調中充滿了練幹,十分確定自己正在說的每個字。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手機螢幕上有顯示你的名字。」
當然了,問題是,那支手機正在誰的手上?「你為什麼會用這支手機?」他緊張得聲音發抖。果然起床時的那種不祥感覺是真的!出事了!
對方用字簡練的告訴他:「這支手機,現在是警方的證物。」然後,對方沉默了一陣,等他回應。
「小……小筠出事了嗎?」他的胸口緊繃得快要炸開了,淚水盈然在眼角打滾,覺得快要崩潰了!
「小筠是指莊雪筠嗎?」
「是,莊雪筠是我女朋友,你是警察嗎?」他已經受不了了,聲音開始哽咽,越來越大的聲量也吵醒了沉睡中的室友,睡眼惺忪的爬起床俯視他,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我是刑事鑑識組的李飛鵬。」對方的說話變快了起來,「告訴我你現在的位置,原地不要移動,我們現在就派人去找你。」
x=0雪筠
雪筠人如其名,長得白白淨淨的,皮膚不需許多保養,就總是毫無瑕疵的白皙。老實說,她的五官也不是挺美,沒有一對烏黑閃亮的大眼,沒有鼻樑高挺的鼻子,但所謂一白遮三醜,她只消燦爛的笑起來,就是人見人愛,沒有人不感受到她的魅力的。
但是,她死了。
一月,春天未至,冬天的寒風仍在肆虐時,晨跑的婦人發現她安靜坐在社區小公園的椅子上,兩眼失去張力的半合著,皮膚白得比平日更白,不過是完全失去血色的慘白。
晨跑的婦人覺得有異,因為她是認識雪筠的,這位十九歲的小女生總是很熱心幫助周遭的人,每個人都會記得她那沒有...


 2017/10/14
2017/10/14 2017/10/09
2017/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