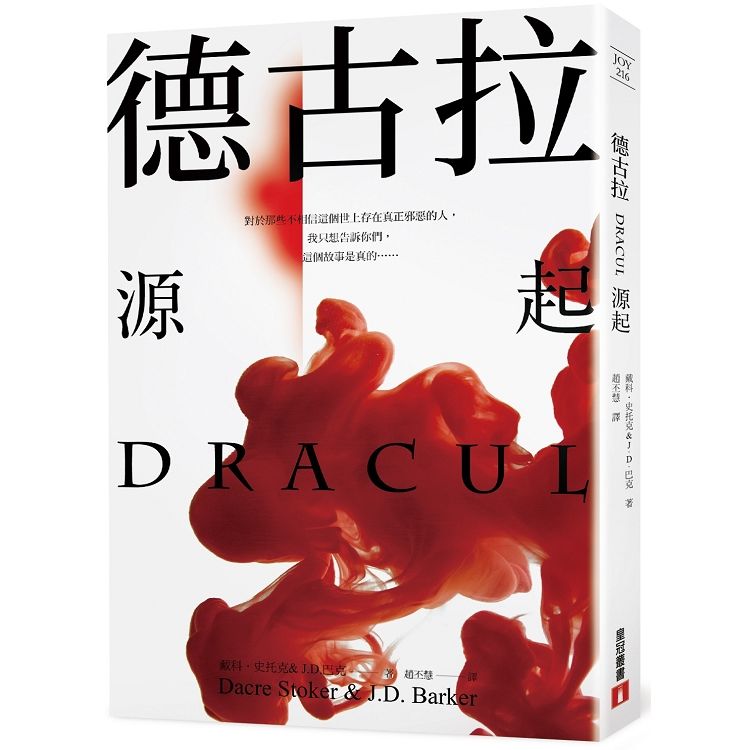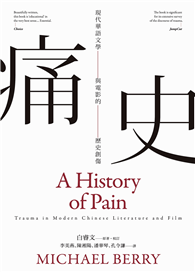圖書名稱:德古拉:源起
湮沒120年,吸血鬼經典《德古拉》
被刪除的101頁初稿終於重現人世!
耗時3年,史托克家族傳人親自執筆,第一部德古拉正宗前傳!
派拉蒙火速搶下電影版權,《牠》億萬導演安迪•馬希提執導!
對於那些不相信這個世上存在真正邪惡的人,
我只想告訴你們,
這個故事是真的……
無論你多麼畏懼黑夜,時候到了,它總會找到你。
布拉姆.史托克環顧四周,一個人、一把槍、一瓶白蘭地、七朵白玫瑰。房間裡布滿鏡子,牆上釘了數十個十字架,門鎖很牢固,縫隙裡還塞滿了聖物,但他很清楚,這些東西都擋不住即將到來的「他」……
布拉姆不禁想起,「好奇」就是這一切錯誤的根源。童年時的他體弱多病,生活起居全依靠能幹的褓姆愛倫照料,但愛倫隱藏的秘密就跟她美麗的容貌一樣勾人。為何她的眼睛顏色會變化不定?為何夜半她會獨自走進闃暗的幽林?為何她的房間裡會有標示著兇案地點的地圖?為何她總是睡在濡濕的泥土裡?還有七歲那年,愛倫又為何在他的手臂留下了兩個永不癒合的小孔?
彷彿察覺到他的懷疑,一天早上愛倫突然消失無蹤,但布拉姆卻沒有就此放棄,他循跡找到一座廢棄的城堡,並在一個大木箱中發現了一隻戴著戒指的斷臂,戒指上寫著一個神秘的名字:德古拉。
如今,當戒指的主人找上他,布拉姆才終於明白這個名字背後的恐怖意義,而這個陰暗狹小的房間,極有可能成為他的墳墓。轉瞬間,門檻上的白玫瑰腐朽成了一團黑,「他」更近了,而夜,還很長……
1897年,布拉姆‧史托克創作的吸血鬼經典小說《德古拉》正式問世,前101頁卻因為情節太過恐怖而遭到出版社刪除。為了還原其最初面貌,史托克家族傳人和暢銷驚悚名家攜手合作,耗費三年時間鑽研史托克的手稿和筆記,終於推敲出那個「不能說的秘密」!《德古拉:源起》不只將帶領我們親歷史托克童年那段恐怖的回憶,更完美實現史托克未竟的心願,解開文學史百年來的終極謎團!
作者簡介
戴科.史托克Dacre Stoker
吸血鬼經典《德古拉》作者布拉姆.史托克的曾姪孫。
在《德古拉》出版120年後,戴科繼承先祖的衣缽,以三年的時間鑽研布拉姆的手稿與筆記,終於重現德古拉故事的真正起源。
他同時也擔任《布拉姆.史托克散佚日記:都柏林歲月》的共同編輯。他目前與妻子珍娜定居在美國南卡羅萊那州艾肯市,管理布拉姆.史托克莊園。
J.D.巴克J.D. Barker
以驚悚小說《四猿殺手》享譽全球的暢銷作家,作品常結合恐怖、犯罪、神秘、科幻及超自然元素,並曾入圍「布拉姆.史托克獎」最後決選,也被改編為影視作品。目前與妻子黛娜與女兒安珀定居在美國賓州。
譯者簡介
趙丕慧
1964年生,輔仁大學英文碩士。譯有《絲之屋》、《莫里亞蒂的算計》、《少年Pi的奇幻漂流》、《穿條紋衣的男孩》、《易經》、《雷峯塔》、《不能說的名字》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