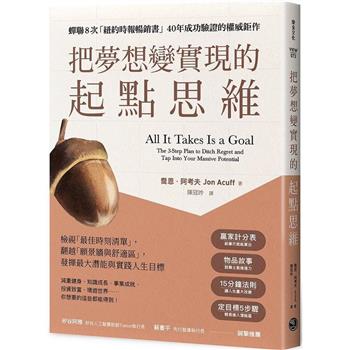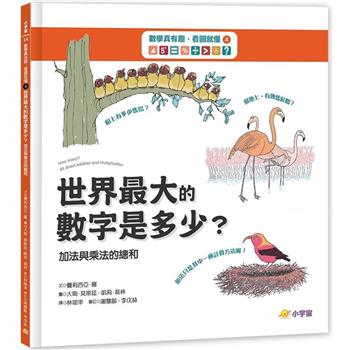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異鄉客的圖書 |
 |
異鄉客 作者: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 / 譯者:葉淑吟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2-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小說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說!
馬奎斯顛峰狀態的殿堂級神作!
12個關於流浪的故事,12種孤獨到底的情狀
每個人物都光彩奪目,每篇故事都宛如寶石
胡淑雯 專文導讀
王定國、伊格言、吳曉樂、高翊峰、陳雪、郭強生、黃崇凱、童偉格、韓麗珠 等小說家致敬推薦!
〈一路順風,總統先生〉
談論一個總統,
最惡劣的行為或許是兩種混在一起講:真話與謊言。
我們國家所經歷最悲慘的遭遇,就是我當上總統。
而我這輩子最大的成功,是讓大家都忘了我……
〈賣夢女郎〉
她從沒說過她的真實姓名,
我只聽過一個饒舌的德文外號:芙烈達夫人。
我興高采烈地以無禮的口吻問她如何在遙遠的異鄉安頓。
她回了我一個不可思議的答案:「我賣夢。」
〈我只是來借個電話〉
醫生將她編入住院名單,並註記了「躁鬱」的診斷。
看著她不斷哭泣,醫生卻催眠般地說道:
「想哭盡量哭,眼淚是最佳良藥。」
然而她仍不停地呼喊:「我只是來借個電話……」
〈雪地上的血跡〉
「沒事,只是刺傷。」
她舉起那隻戴著鑽戒、被玫瑰刺傷的手指。
「想像一下,從馬德里一路滴到巴黎的雪地血跡,
你不覺得很美,很適合一首歌嗎?」
因為一個無法解釋的葬禮夢境,馬奎斯寫下了這些奇異又荒謬,寫實又夢幻的故事:落魄的流亡總統、賣夢維生的婦人、被關進瘋人院的正常人、泅泳在流光中的孩童,以及血流不止的女子……他以舉重若輕的筆法,將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寫得靈動輕盈、充滿魔力。本書也讓我們知道,馬奎斯不僅是一位實至名歸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更是一位最會說故事的小說家!
作者簡介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年3月6日生於哥倫比亞阿拉卡塔卡,自小與外祖父母一同生活在炎熱多雨的小鎮巴蘭基亞,鄰近一個名叫「馬康多」的香蕉園。1940年與父母一同遷往內陸小鎮蘇克雷,1947年進入位在首都波哥大的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法律,並沉迷於卡夫卡與福克納的作品,同時也開始在《觀察家報》發表短篇小說。1948年因內戰舉家遷往卡塔赫納繼續大學學業,並兼任《環球日報》記者。1954年出任《觀察家報》的記者與影評人,1955年發表〈一個船難倖存者的故事〉系列報導廣受好評,隨後出任該報的駐歐記者。1957年在巴黎與海明威邂逅,並奉其為「大師」。因景仰古巴革命,1960年擔任古巴的拉丁美洲通訊社駐波哥大和紐約記者。
1965年駕車前往墨西哥城途中萌生《百年孤寂》的寫作構想,在閉關十八個月後,終於完成這部醞釀了二十年之久的經典之作。1967年《百年孤寂》甫出版便造成轟動,並於1969年獲頒義大利「基安恰諾獎」與法國「最佳外國作品獎」。1970年《百年孤寂》英譯本在美國出版,並被選為年度12本最佳作品之一,同年馬奎斯並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72年馬奎斯再獲頒美國「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以及拉丁美洲文學最高榮譽的「羅慕洛.加列戈斯獎」,1981年則獲法國政府頒發「榮譽軍團勳章」,1982年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並擔任法國西班牙語文化交流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語言科學院名譽院士。
其他作品包括《預知死亡紀事》、《愛在瘟疫蔓延時》、《迷宮中的將軍》、《異鄉客》、《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苦妓回憶錄》等,每每一推出都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2014年4月17日逝世,享年87歲。
譯者簡介
葉淑吟
西文譯者,永遠在忙碌中尋找翻譯的樂趣。譯有《百年孤寂》、《謎樣的雙眼》、《風中的瑪麗娜》、《南方女王》、《海圖迷蹤》、《愛情的文法課》、《時空旅行社》、《黃雨》、《聖草之書:芙烈達.卡蘿的祕密筆記》、《螺旋之謎》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