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別管這個吵著要加入的傢伙了!
利瑟爾病倒啦!!
隨書附贈:「與夥伴們一起慶祝」雙面拉頁海報
特別加碼:第10集出版「三人同賀」
利瑟爾被狂信者綁架,前來營救他的,正是他最信賴的隊友劫爾和伊雷文。但奴隸青年夸特卻阻擋在伊雷文面前,不讓他繼續前進。
原來夸特出身過去曾被奉為「最強戰士」的民族,在利瑟爾逃出牢房時,夸特也希望能夠跟他們一起離開。然而他與伊雷文的個性根本水火不容,兩人之間的各種大小衝突不斷,讓利瑟爾傷透了腦筋。
不只如此,歷經牢獄之災的利瑟爾,竟因過度勞累而得了重感冒!但在安心養病之前,還得先讓受到魔法陣影響而出現異變的魔鳥恢復原狀……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10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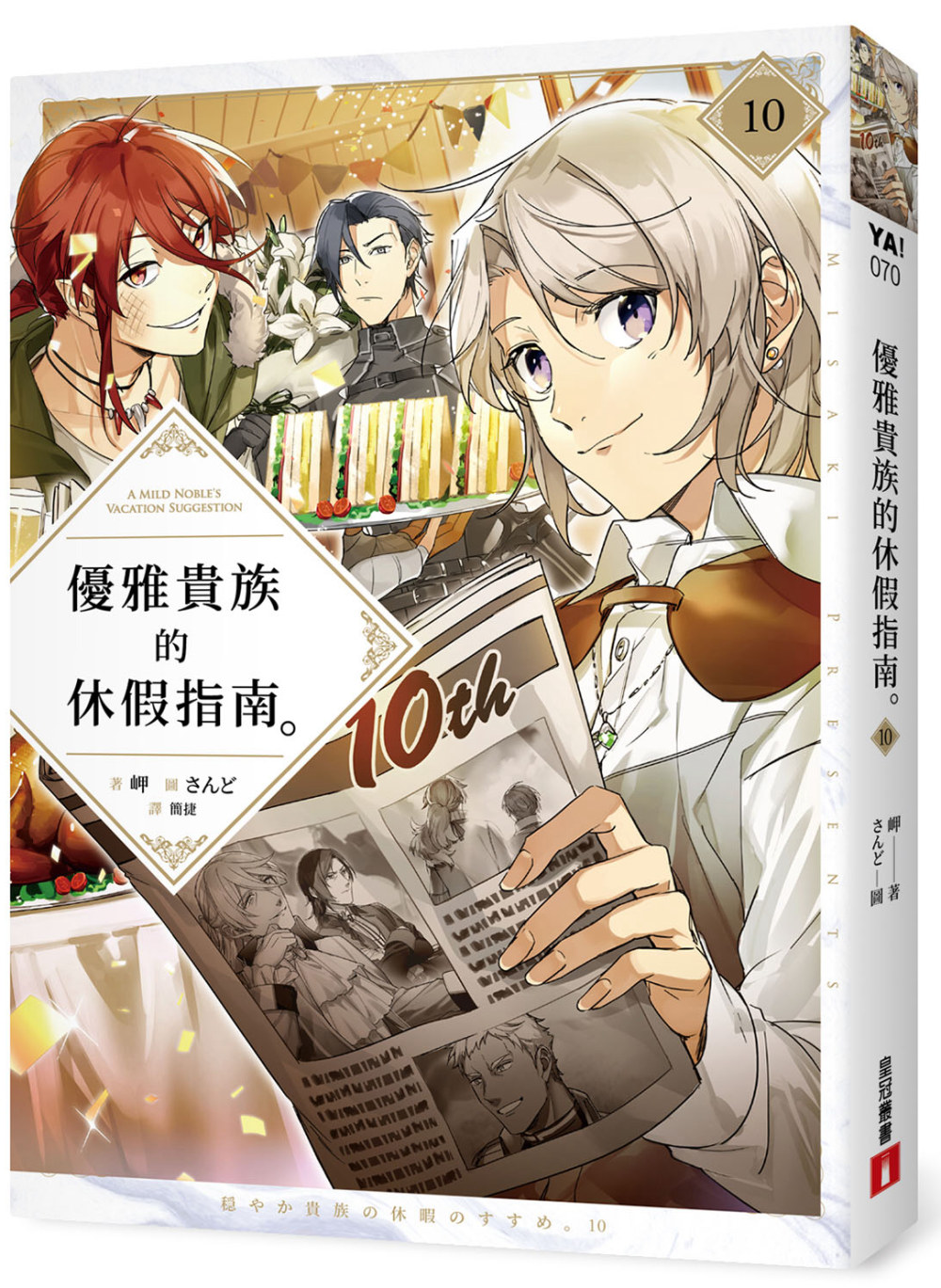 |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10 作者:岬 / 譯者:簡捷 出版社:皇冠 出版日期:2021-12-1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0頁 / 14.8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4 |
幻奇冒險 |
電子書 |
$ 225 |
奇幻冒險 |
$ 253 |
Books |
$ 253 |
Books |
$ 253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272 |
奇幻冒險 |
$ 282 |
中文書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