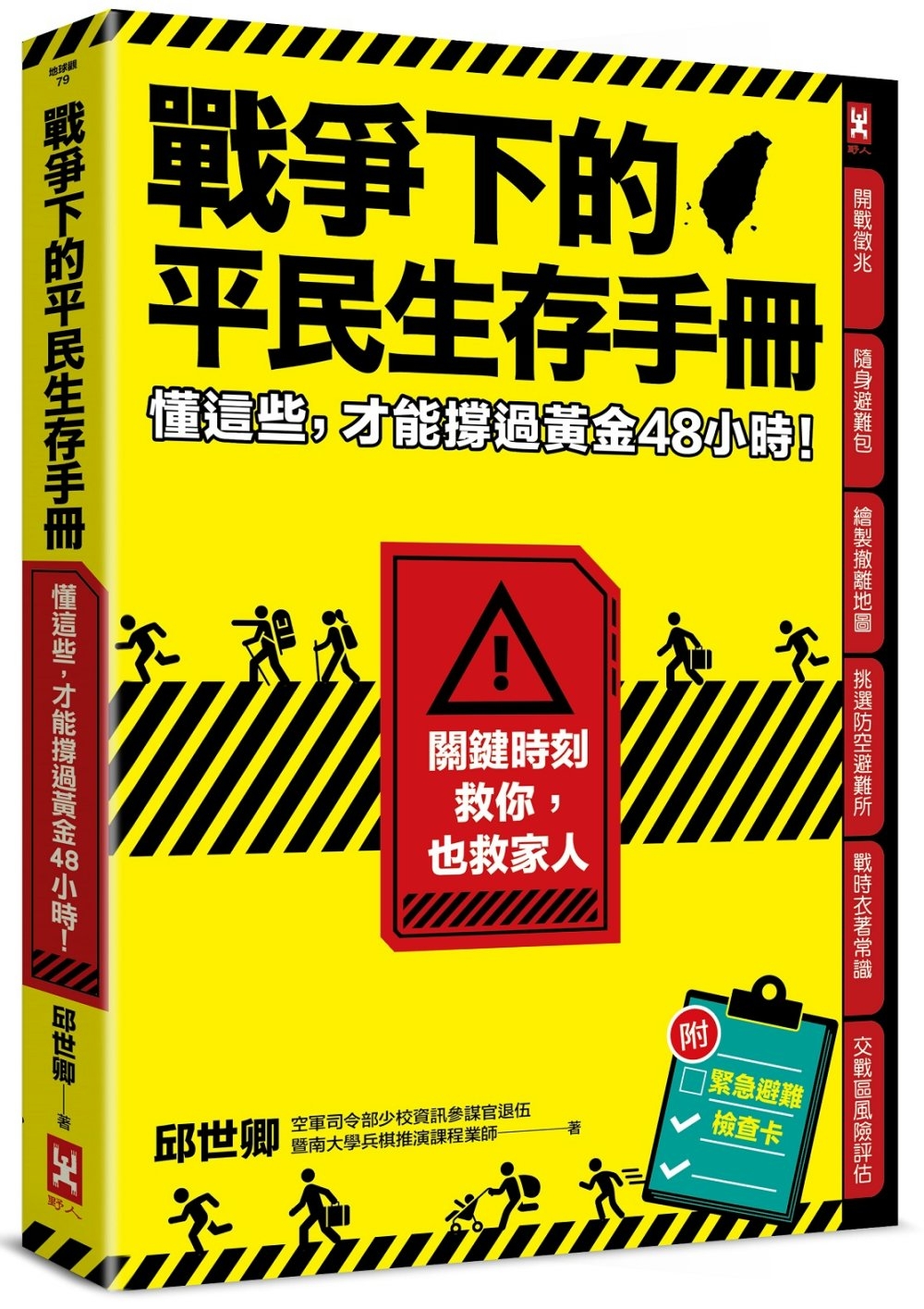小說的價值在於展現生命裡存在的可能性,
將深埋在你我心中的東西發掘出來。
文壇大師米蘭‧昆德拉對藝術的獨到見解,
20世紀至今猶然散發歷久不衰的耀眼光芒!
我們碰觸到了圍繞在他遺囑四周那段傳說裡的最大謊言:
卡夫卡根本不想毀掉他自己的作品。
一個人兩腿一伸以後,不是被當做廢物處理,就是被當做象徵供奉。
對於他已喪失的個體性,兩種做法都是不敬。
美學意圖不但從作者所寫的表現出來,也從作者所刪去的部分顯露出來。
寫出一段文章是不簡單,
但刪掉它,卻要求更多的天賦,更多的文化背景,更多的創造力量。
所以出版作者所刪去的部分,這和刪去作者決定要保留的部分一樣,
都是同樣粗暴的侵犯。
米蘭‧昆德拉延續《小說的藝術》中小說創作的源起,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持續引領讀者在文學史上的經典巨作之中徜徉,進而衍伸探究文學、音樂乃至藝術發展的脈絡。
透過大師的筆觸,探究自古典與現代接壤的二十世紀以降,現代主義、浪漫主義與藝術創作者所處的當代環境、政治社會,在「創作」的洪流中爬梳過去、現在與未來。
本書與《小說的藝術》、《簾幕》、《無謂的盛宴》並列昆德拉的四大文學論集,以廣袤的哲學語境與批判精神,奠定其當代大師地位。
作者簡介: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一九二九年生於捷克的布爾諾。一九七五年流亡移居法國。作品有長篇小說:《玩笑》、《身分》、《笑忘書》、《生活在他方》(榮獲法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的「麥迪西大獎」)、《賦別曲》(榮獲義大利最佳外國文學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朽》、《緩慢》、《無知》、《無謂的盛宴》;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評論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簾幕》、《相遇》;此外還有一部舞台劇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靈感來自狄德羅小說《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譯者簡介:
翁尚均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博士,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文化行政職系公務人員正式退休,現專事英法文中譯工作。
章節試閱
第一部:帕紐朱不再令人發笑的時候
幽默的發軔
大喉嚨夫人身懷六甲,嗜吃牛羊下水,因為過度飽食,不得不服用一帖收斂劑。這收斂劑的藥效過強,引發胎盤鬆弛,結果胎兒高康大(Gargantua)脫落下來,順著血管上溯,最後從他母親的耳朵裡誕生出來。從一開始這幾個句子裡,我們就清楚了解這本書的路線:這裡所敘述的並不是正經八百的東西。作者並不打算給讀者確定什麼真理(科學的或者神話的);不打算描述真實世界中發生的事件。
拉伯雷(Rabelais)的幸福時代:小說的彩蝶披著蛹殼的皮翩然起飛。龐大固埃(Pantagruel)的巨人形象仍舊屬於過去那個離奇故事的年代,然而帕紐朱(Panurge)形象嶄新,是小說藝術前所未見的。一種劃時代的新藝術產生了。這個了不起的際會給予拉伯雷的創作不可思議的豐饒。裡面什麼都不缺乏:似真性和荒誕怪異、寓言和諷刺、巨人和常人、軼聞趣事、沉思冥想、真實的和幻想的旅行、博學的辯論,只為展現壯麗的詞藻的東拉西扯。今天的小說家師承十九世紀的風格,心裡一定豔羨最早期的那些同行:因為他們創造炫人眼目的大雜燴世界,並且快樂地悠游在其中。
拉伯雷在小說開頭的幾頁裡面,讓高康大從他母親的耳裡呱呱墜地。同樣出人意表,塞爾曼.魯西迪在他的《魔鬼詩篇》中,兩位主角竟在自己的飛機半空爆炸解體,然後向下墜落的過程中,不是閒扯就是唱歌,而且舉止滑稽,令人直覺不可思議。與此同時,「在上方,在後方,在下方,在空中」浮盪著一張張可調整靠背角度的扶手椅、紙杯、氧氣罩以及其他旅客。其中一主角名叫吉百列(Gibreel Farishta),他「在空中泳動,有時像游蝶式,有時像游蛙式,有時又將身軀蜷縮成個肉球,有時再把手臂腿部伸直出去,而那天空則像黎明曙色,幾乎沒有邊際」。另外一個主角名喚薩拉丁(Saladin Chamcha)則像是「一抹纖巧黑影,頭下腳上墜落,身著灰色西服,釦子一個也沒鬆脫,頭戴著瓜皮帽,兩掌緊貼著左右大腿」。他的小說就像是以這種局面開場的。魯西迪和拉伯雷一樣清楚,小說家和讀者間的契約在作品一開始就要確立。才一起頭便打開天窗說亮話:即便接下來要陳述的事令人驚駭,但是故事本身並非嚴肅莊重。
這既恐怖又輕鬆。就舉《第四冊》(Quart Livre)裡的一個場景為例:龐大固埃的船在外海巧遇一艘載有數名販羊商人的船。其中一位看見帕紐朱穿褲子前面沒開襠,無邊軟帽上面別了一副眼鏡,就瞧不起他,不但一副趾高氣揚的模樣,還譏笑他老婆專偷漢子。帕紐朱立刻採取報復行動:他先向那商人買來一頭綿羊,然後將那牲畜扔進海裡。因為羊性盲從,看見第一頭羊落海,其他的羊也就噗通噗通,一隻一隻跳進水裡。眾商人見狀都慌了手腳,紛紛前來攔阻,有的抓住羊毛,有的扯住羊角,可是不但無效,而且最後全被拖進海裡。而站在船上的帕紐朱則把船槳握在手裡,不是為了救人,而是阻止他們爬回船上。在此同時,他還不忘對這群人誇誇其談,說是今生今世也不過一場苦難,幸福良善只得往那冥府裡頭去尋,並且斷言,死人要比活人愜意。最後他說,如果諸位仁兄覺得與人為伍不致太過討厭,那麼不妨學學《聖經》裡的約拿,住到鯨魚肚裡面去。等到眾商人都淹死以後,那位偕行的好修士尚(Jean)趕忙向他道賀,不過對於他亂花錢買羊難免數落幾句。可是帕紐朱答道:「老天,這場遊戲本來要花五萬法郎才辦得到!」
這個場景是虛幻的,不可能發生的;裡頭是否包藏什麼教訓?拉伯雷是不是要譴責商人的狹隘氣度,只有看他們出糗我們才能稱快?還是作者呈現帕紐朱的殘酷,全為激發我們的憤慨?還是他站在反教會的立場,揶揄帕紐朱口中那些陳腔濫調的愚蠢教義?讀者慢慢猜吧!
歐塔維歐.帕茲(Octavio Paz)說過:「荷馬和魏吉爾 都不懂得幽默;亞里奧斯德 似乎懵懂意識到了,可是一直要等到塞萬提斯(Cervantes)出現,幽默才具體成形〔……〕。」接著,帕茲又補充道:「幽默是現代主義精神最偉大的發明。」這段話的核心重點:幽默並不是人類自年湮代遠以來便具備的。它的出現和小說藝術的濫觴是密不可分的。幽默不是發笑,不是嘲弄,不是諷刺,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詼諧。按照帕茲說法(這是了解幽默的關鍵),「幽默可讓所及之事曖昧起來。」讀者要是無法津津有味品賞帕紐朱眼睜睜放任販羊商人淹死,還要讚嘆來世如何美好的這段插曲,那麼就永遠無法理解小說這門藝術。
道德評斷暫停的領域
如果有人要問,在我和讀者的誤解當中,最常見的原因是什麼,那我會毫不遲疑回答:幽默。記得當時我來法國沒有多久,有一位醫學界鼎鼎大名的教授希望見我一面,因為據說他相當欣賞拙作《再見的華爾滋》(La Valse aux adieux)。這點讓我十分得意。根據他的看法,我的小說具備一種預言特質;書中有位名喚史克雷塔(Skreta)的醫生,他在一處溫泉療養勝地專門治療一些看來是患了不孕症的婦女,可是卻暗中利用一個特殊注射器,將自己的精液注入她們的體內。由於這個情節,他認定我的作品觸及了未來的一個重要課題,並且邀請我出席一個主題有關人工受精的研討會。這位學者從口袋中摸出一張紙,然後將他論文的草稿唸給我聽。精液捐贈必須是匿名的,無償的,而且(說到這裡,他認真地盯著我的雙眼)必須基於三層愛心:第一層,對於一顆陌生卵子,一顆渴望克盡天職的卵子的愛;第二層,捐贈者對自我的愛,因為經由捐精,這個「自我」得以傳遞下去;第三層,對於某對不孕夫妻的愛,這種夫妻因為膝下無嗣而感失落。說到這裡,他又再度凝視我的眼睛;儘管他的學術威望高人一等,他還是輕率說出他的批評:我沒能夠大力強調精子捐贈這行為中所蘊含的道德美。我辯解道:小說的本質是滑稽!我筆下的司克雷塔醫師是個異想天開的古怪人物!這本小說的內容大可不必全部都用正經八百的態度看待!聽到這話,那位學者一臉狐疑問道:「這麼說來,你的所有小說都不必用嚴肅的態度看待?」這句話把我問糊塗了。不過,才轉瞬間,我會意過來了:讓人了解幽默簡直要比登天還難。
在拉伯雷的《第四冊》裡有段海上颳起暴風雨的場景。船上所有的人都竭盡全力搶救,以免船覆人亡。在這緊要關頭,只有帕紐朱嚇到癱瘓,獨自在一旁呻吟著。而這哀嘆足足耗去好幾頁的篇幅。最後,天氣恢復平靜,他也重拾鎮定,這時,他卻開始數落同儕,說他們個個是懶鬼。耐人尋味的是這點:這個懦夫、游手好閒、愛說謊話又愛譁眾取寵的人,不僅沒有激起義憤,反而讓讀者們欣賞他的吹噓。拉伯雷的作品走筆至此,已經全面地、根本地達成小說藝術最終極的境界,那就是:暫停所有道德評斷。
暫停所有道德評斷並不表示小說就不道德。這個前提正是它的道德。遽下結論,妄做判斷,這是人類根深柢固的老毛病,而這道德正是反對這種作法,挑戰人類未理解就先仲裁的積習。以小說藝術智慧的觀點來看,這種愛下斷語的急切天性,正是最可惜的蠢行,最危險的罪惡。倒不是說小說家走極端,要懷疑道德判斷的正當性,而是將它放在小說領域的外面。走出小說,如果你願意,不妨大罵巴爾努治懦弱。罵不夠的話還有艾瑪.包法利(Emma Bovary)、哈斯提尼亞克 可供譴責。不過那是你的閒事,小說家可就管不著了。
小說創造出一個想像的場域,在這其中,道德判斷暫時終止,這可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功勞。唯有在這種情況下,小說人物才能充分發展成長。這些筆下造出來的人物不是根據既存的真理而成形的,不是「善」與「惡」的典型,也不代表彼此相對立的客觀律法,而是根據自己本身的道德而塑造出的自由個性。西方社會已經習慣將自己和講人權的社會等同起來。可是在「人」獲得「權」以前,他還得先具備自我意識,在自己和別人的心目中形成既定形象。如果不是因為歐洲有源遠流長的藝術及小說傳統,特別是那些教導讀者對旁人好奇,對異於自身真理標準認真理解的小說,哪裡可能產生重人權的社會?以這角度來看,西奧杭 說得真好,歐洲社會即是「小說社會」,歐洲人則是「小說之子」。
去神聖化
世界的去神聖化(德文作Entg tterung)是定義「現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去神聖化」並不是「無神論」,只是點出一個狀態:自我,思考的自我取代了神祇,成為一切的基石。人們大可依舊保有信仰,在教堂裡跪地行禮,或者睡前誠心禱告,但是他的宗教虔敬從此以後只屬於個人的主觀領域。海德格在指出這種情況之後又下結論道:「因為這樣,眾神只好走為上策。祂們所遺留的空白則被神話的歷史學和心理學探索所填補。」
從歷史學和心理學兩個切入點來探索神話,探索神聖的文本,這意味著:將之賦與世俗意義,將之去神聖化。「世俗」(profane)一詞源自拉丁文profanum,意即神殿前的空間,神殿外的場所。去神聖化因此就是把神聖事物移出神殿之外,離開宗教的範疇。一本小說裡面,如果好笑的成分稀薄分散,幾近不可見,那麼去神聖化就發揮最大作用了。因為去神聖化和幽默是無法互容的兩件事。
托瑪斯.曼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二年間寫成的四聯創作《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 即是對神聖文本所進行的最精采的「歷史學和心理學探索」。作品裡的語氣是托瑪斯.曼特有的歡愉以及壯闊的沉悶,其中嗅不到一絲神聖的味道:在《聖經》原典中那個自亙古以來便存在的上帝,到了托瑪斯.曼的筆下卻成為人類的一項發明,是亞伯拉罕的創造。亞伯拉罕將祂從混亂的多神信仰中抬舉出來,先是讓祂神威冠於諸神,最後將祂定於尊一。上帝明白是誰創造祂的,於是驚呼說道:「真是不可思議,卑微人類對我居然瞭若指掌。從一開始,連我的名字都是他給的。但事實上,我卻要去替他塗敷聖油。」值得一提的是:托瑪斯.曼特別強調,這是一本幽默小說。什麼?《聖經》可以拿來嬉笑?還有約瑟夫和普蒂法兒的那一段也是;普蒂法兒瘋狂地愛上約瑟夫,舌頭弄傷之後只能像小孩一般口齒不清地把「陪我睡吧!」這種挑逗話就走音唸成「陪我s é吧!」的滑稽調。在那三年當中,秉性純潔的約瑟夫不厭其煩地一再告訴那個喜歡發出/s/、/z/音的女人,自己是不可能與她燕好的。最後到了那要命的日子,他們兩個人湊巧孤男寡女守在屋裡,那個女的重新展開攻勢,陪我s é吧,陪我s é,而我們那品德極高的男主角又捺住性子,像師長訓誨弟子般的口氣告訴她,不能與她苟合。不過在義正辭嚴說教的時候,他褲襠間的東西卻不聽使喚,一再脹大脹大,好結實的一大球。結果被普蒂法兒瞧見,一時之間失去理智,伸手扯掉約瑟夫的上衣。約瑟夫見狀,顧不得褲襠間那物事依舊興致勃勃,只能拔腿就跑。而普蒂法兒一樣失了方寸,亂了陣腳,情急之下只好扯起嗓子大喊救命,並且誣指約瑟夫對她意圖不軌。
托瑪斯.曼的這本小說普獲各界好評;這證明了,去神聖化並不被視為對宗教的冒犯,因為這種態度業已成為風俗習慣的一部分了。在「現代」這個歷史時代裡,不信宗教的人不若以往那樣滿腹懷疑、那樣故意挑釁,但是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的人也失去了昔日那種傳教士般地自信以及排他態度。在這個轉變當中,史達林主義的衝擊起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史達林一方面堅持抹滅所有基督教文明的記憶,他卻同時也清楚而且專斷地宣稱,不管我們信不信神,不管我們篤信上帝或者瀆言毀教,我們每一個人都隸屬於同一個植基於基督教歷史的文明。沒有這個文明,我們都將是沒有實體的幽魂,缺乏語彙的推理者,心靈上的無國籍者。
我自己從小接受無神論的教育,而且覺得十分慶幸。可是在共產黨統治最陰沉的那幾年裡,我見識到了那些飽受侮辱刁難的基督徒。突然之間,我青少年時期最早的那個愛好挑釁的狂熱無神論階段戛然中止,而且回頭去看,不過就是乳臭未乾的愚蠢行為。我開始能夠理解那些信教的朋友;有時基於感動以及支持他人的立場,我也會陪他們去做彌撒。不過即使如此,我的內心深處還是無法相信有神,更別說相信這神能左右我們的命運。可是,我到底真能確定什麼?而他們又到底知道什麼?他們真能確信自己所信為真?我坐在教堂裡,心中有種奇特又快樂的感覺,我的不信和他們的堅信居然這樣接近。
歷史之井
個體是什麼?他的自我認同何在?所有的小說作品都在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換個角度,所謂的「我」如何定義呢?經由他所做的,他的行為?可是行為卻不受施行者的控制,而且幾乎一定會回到他的身上。還是另有定義,靠他的內心世界,他的思想,他那些不為人知的情感?還有,一個人難道真的了解他自己?他那些不為人知的思想可是塑造他自我認同的關鍵?人的定義會不會要靠他對世界的觀點,也是就德文字的Weltanschauung呢?這也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美學基礎:他筆下的人物都具有鮮明的個人意識型態,而且由於這種意識型態,支撐他們行動的就是一套不可妥協的邏輯。而托爾斯泰正好相反,所謂個人的意識型態絕對不是固定不變的,不是個體自我認同賴以建立的礎石:「史代凡.阿卡迪維奇(Stephane Arcadievitch)從不選擇他的態度或是立場,因為態度或是立場自動會來就他。就像平常他也沒習慣選擇禮帽或是禮服,只是但有便穿。」(《安娜.卡列妮娜》)可是,如果個人的思想並不是個體自我認同的基礎(要是它的重要性不超過一頂帽子),那麼這個基礎又在哪裡呢?
對於這個撲朔迷離的問題,托瑪斯.曼倒是做出了相當可觀的貢獻:我們認為自己在行動,認為自己在思考,實際上是另一個人或者另一些人在我們心中行動或者思考;一些起源甚早,出處不可追尋的習俗,一些原型,全披上了神話的外衣,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包藏其強烈的誘惑力,從(托瑪斯‧曼所說的)「歷史之井」的深處遙控我們。
根據托瑪斯‧曼:「人的自我是否包藏在極有限的範疇裡,而且密實地鎖閉在他那短暫的,屬肉的軀殼裡?組成他個體的好幾種成分不都屬於外在於它,先前於他的宇宙?〔……〕普遍的心靈和個人的心靈之間的差別在昔日並不比在今日來得明顯……」他還說道:「我們所面對的或許是一種大家很想稱之為模仿或延續的現象,根據這種生命觀點,每一個人擔任的角色正是重現祖先所建構的某些既定的形式,某些神話綱要,讓它們得以依附新的肉體並且再生。」
《聖經》裡面,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掃之間的衝突不過就是昔日亞伯和他的哥哥該隱間對立關係的翻版,是上帝的寵兒與他人,這個被忽略的,妒意滿盈的他人之間的抗衡。這種衝突,這個「祖先所建構的神化綱要」又在雅各的兒子約瑟夫這個上帝的寵兒身上再度淋漓體現出來。雅各因為受到一股起源甚早、出處不可追尋、上帝的寵兒的罪惡感驅使,因此遣他下來去和他那些善妒的兄弟和解(這招真是下下之策,因為他的兄弟會將他扔進井裡)。
甚至受苦受難的亦復如此,這種看似無法控制的反應其實追根究柢依然是「模仿以延續」:小說中當我們看到雅各為約瑟夫的死搥胸頓足而哀傷悲吟之際,托瑪斯‧曼就下評語論道:「這並不是雅各慣常的說話方式〔……〕挪亞在面對大洪水而感到威脅時,也曾經使用相同或近似的語言,而雅各的一番哀嘆只是他祖先那些話的翻版。他的絕望透過多少是熟詞奮語的話傾吐出來〔……〕不過不能因為這點就懷疑他是否言不由衷。」這裡,我們要注意到:模仿並不代表缺乏真心,因為個體無法不去模仿已經發生過的。就算他再坦白,所說的話不過是種再生;就算他的心志如何誠摯,所說的話其實只是從那歷史之井湧上來的命令以及建議。
第一部:帕紐朱不再令人發笑的時候
幽默的發軔
大喉嚨夫人身懷六甲,嗜吃牛羊下水,因為過度飽食,不得不服用一帖收斂劑。這收斂劑的藥效過強,引發胎盤鬆弛,結果胎兒高康大(Gargantua)脫落下來,順著血管上溯,最後從他母親的耳朵裡誕生出來。從一開始這幾個句子裡,我們就清楚了解這本書的路線:這裡所敘述的並不是正經八百的東西。作者並不打算給讀者確定什麼真理(科學的或者神話的);不打算描述真實世界中發生的事件。
拉伯雷(Rabelais)的幸福時代:小說的彩蝶披著蛹殼的皮翩然起飛。龐大固埃(Pantagruel)的巨人形象仍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