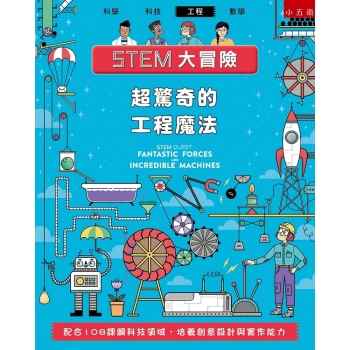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史上最年輕芥川賞得主得獎作品✧
青春的「青」是瘀青的「青」——
這是只有19歲的少女能寫得出來的故事。
暢銷突破
✦150萬冊✦
獨家收錄
\中日對照印刷留言扉頁/
\繁體中文版紀念作者序/
\名書評家全文解說/
✧ ✦ ✧
▍好想給這毫無防備的背部一腳,
▍好想看他疼痛的樣子。
▍驟然綻放的全新欲望,
▍像閃光般瞬間刺痛了我的眼睛。
孤寂發出鳴叫,有如高亢清澈的鈴聲,刺痛了耳膜。我於是用手指將講義撕成長條狀,撕得又細又長,用紙張刺耳的撕裂聲來掩蓋,不讓周遭聽見孤獨的聲音。越堆越高的紙屑山,是我孤獨的時間凝縮成的小山。
在老師問分組有沒有人落單時,我和另一個多餘的人不得不悲慘地舉起手來。這證實了一件事,那就是在班上還沒交到朋友的人只有我,跟這個男生蜷川。多餘的東西本來就該配給多餘的人,這不是霸凌,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為就是這麼天生一對,沒辦法。
我悄悄瞄向身旁的蜷川。他有點奇怪,一個男生居然敢在課堂上翻閱女性時尚雜誌,我的撕講義簡直太不值一提了。他不發一語,當我不存在,反而是雜誌裡的模特兒Oli對我露出了熟悉的笑容。我說,我見過這個人。
我看見整個世界在蜷川的眼裡亮了起來。Oli成為我和蜷川變成朋友的契機,然而看著他迷戀Oli的背影,我的心中卻湧升好想踹他的衝動。這種「好想傷害他」又「不想失去他」的心情,究竟是什麼……
✧ ✦ ✧
青春期有一種潔癖。不討好師長,不加入小團體,一句誇獎就願意全力以赴,認定夥伴後首先交換秘密,被揶揄時堅決主張這不是愛情。這是年僅十九歲的綿矢莉莎劃時代的純文學經典,全面抗拒青春的青春小說。如果溫柔造成距離,傷害反而靠近,那麼愛你或是踹你,就同樣都是「我在乎你」的變體。
✧ ✦ ✧
✦史上最年輕得主芥川賞得獎作品
先是橫掃40歲至70歲芥川賞評審,讓純文學名家們瞠目結舌;接著更是賣出史無前例的百萬銷量,成為轟動文壇的現象級純文學小說。前所未見的「不青春小說」,一腳「踹」破青春小說的定義。
✦獨家收錄繁體中文版序:〈為什麼如此燦爛奪目呢?〉
「高中校園的一隅明明平淡無奇,為什麼看起來會如此燦爛奪目呢?青春的碎片瑣瑣細細地散落在高中生活裡,同樣也隨處散落在這本書裡。希望所有讀者,都能感受到那樣的燦爛奪目。」——綿矢莉莎
年僅17歲便奪得文藝賞作家出道,19歲時以《欠踹的背影》拿下日本純文學最高殿堂芥川賞,28歲再獲大江賞。至今仍是三大賞史上最年輕得主的綿矢莉莎,最經典的純文學作品。
✦全新收錄解說:〈「踹」意味著什麼?〉
「同樣描寫十多歲的世界,《欠踹的背影》卻跟其他作品劃清了界線。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拒絕被納入『青春小說』,並貫徹到底的態度。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這兩個『白目的高中生』才能成功地『踹』了青春小說的世界一腳,這應該就是這本小說最具衝擊性的地方吧。」——【文藝評論家】齋藤美奈子
✦19歲少女眼中的世界化為文字
「我可以清楚想像,自己在這世界上最長的十分鐘休息時間,坐在位子上一動也不動,毫無表情地一點一點死去的樣子。」
「我壓根不想與世上萬物互動,可是如此努力抹消自己存在的我,卻又害怕去確認自己的存在是不是被徹底抹消了。」
「我希望他肯定我,也希望他原諒我。還希望他像把纏繞在梳子上的頭髮一根根拔除般,也把纏繞在我心中的黑線,用手指一條條揪出來,扔進垃圾桶。」
難以用文字表達的焦躁心情,被十九歲綿矢莉莎的犀利目光捕捉,讓人無法別開眼去,共鳴直擊內心。
✦20週年紀念版全新設計
象徵青春的灰藍色、起腳準備踹人的少女、戴著單邊耳機的少年。當女孩踩上男孩的影子,對於自己的定位和難解的情感,她飛奔去尋找答案。正在學習中文的綿矢莉莎更親自寫下日文及中文留言,印製於扉頁向所有讀者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