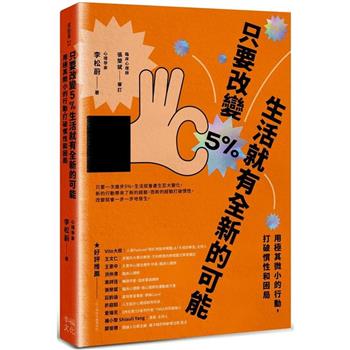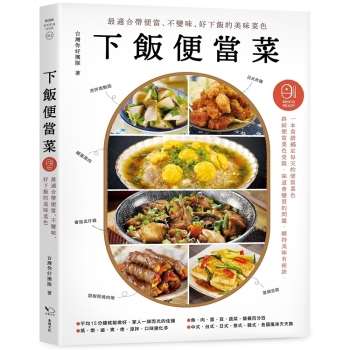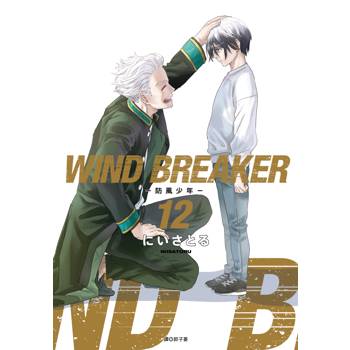沒有飛機掉下來
在我退伍以後很久的一個夏天,我忽然接到一通來自澎湖馬公機場的電話,電話那邊傳來是我後期醫官的聲音,他用亢奮的聲音告訴我:
「我告訴你,飛機掉下來了!真的掉下來了!」
隔著電話,我聽到了飛機引擎聲,逼真的臨場感。
「有沒有人傷亡?」我問他。
「沒有。」
他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連珠炮似地跟我說個不停。
真的掉下來了?我保證那絕對不是幸災樂禍,但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的感覺。
掛上電話,耳朵都是澎湖機場上轟隆隆戰鬥機、運輸機、噴射客機的聲音。我想起了從前開著救護車,守在機場的那些日子。
當時我的任務就是等待飛機掉下來。
我想我不該那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莫名其妙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那時候我等了兩年,沒有飛機掉下來。退伍了。
1
我一直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我的長官指著鼻子罵人的樣子。
任何人聽到這樣的任務應該都會有和我一樣的反應才對。
「可是……你是說,像這樣,」我順手比了一個飛機墜毀的手勢,「等飛機掉下來?」
「哼?」他的尾音拉得好高。
「我是說,飛機,飛機……怎麼會掉下來?」
「你覺得很滑稽是不是?」我的長官顯然生氣了,他指著我的鼻子,「我鄭重警告你,不管你覺得事情有多可笑,再滑稽的事背後都有嚴肅的一面,你最好永遠給我記住這句話。」
我還來不及問出更多的問題之前,他已經交代完了他的任務。背著手,越過滑行道,消失在跑道的那一端了。
2
看來似乎是個不太順利的一天。
我的駕駛兵正在踢他的救護車。
「你在幹什麼?」我問他。
「我在修理救護車,」他又踢了兩腳,跑到駕駛座去發動引擎,「有時候這樣可以發動。」
他發動了引擎,沒一下,熄火了。
「你有沒有去給車輛分隊那些人檢查過?到底是什麼毛病?」
「精神病,」他又猛烈地搖晃車身,「他們說是精神病,在這裡待上十四年,不得精神病,那才奇怪。」
發動引擎,還是沒著火。
「十四年?」我抓了抓頭,「難道我們沒有試著申請新的救護車?」
「別傻了。」他笑著指著跑道上正在起飛的C-119運輸機,「看到沒?那飛機四十幾年都還在飛。你十四年算老幾?上次他們就是這樣告訴我的。」
「這樣不行,萬一有飛機掉下來,我們就完蛋了,」我繞到救護車後面找我的救護兵,「阿成,下來,幫忙推車。」
「拜託……你沒看到我很忙,明天總部要來視察了。」我的小兵坐在救護車內很認真,一字一句地寫他的紀錄。
「你在寫什麼紀錄?」我湊過頭去看。
「很—成—功—地—完—成—了—這—一—次—義—診—的—任—務—,充—分—發—揮—了—軍—愛—民—,民—敬—軍—,軍—民—一家—的—革—命—精—神。」
「我怎麼不記得我們曾經出去義診過?」我訝異地表示。
「那個村子早就剩下沒幾個人了。去了也沒有用,所以我們沒有去。」
「沒有去怎麼還會有四十幾個人的病歷紀錄?」我問他。
他對我露了一個詭異的笑。
我隨手抓起病歷翻閱。看看沒有去義診,怎麼寫出病歷來?
「咦?」這可有趣了,「這個張青峰,不就是雜貨店老闆娘的爸爸。幾個月前死了,我們還收過白帖子,怎麼可能昨天來看病呢?」
「他不能死。」醫務兵理直氣壯地回答。
不能死?
「總部規定每個月義診診數至少四十人,每個人都死了,去哪裡找四十個人?」
「他還會說話?」我愈翻愈覺得好笑了。
他把病歷搶回去。
「我們一邊義診,一邊做政治教育。他當然要說話。表示我們得到了成果,這樣政戰部看了才會滿意。」他一副要我少不上道的表情。
「我看看他說什麼話?」我一把又把病歷搶回來,「哈,李總統很英明。怎麼每個人都說同樣的話。」
「沒有人規定不能說同樣的話,」他看看我,「哎喲,醫官,別鬧了,拜託幫我想個幾句話,總部明天要來抽查,今天晚上我再不交就泡湯了……」
轟隆隆又從我頭上飛過七三七噴射客機,那聲音大得我不得不蒙上耳朵。
車身晃動了一下,顯然我的駕駛兵又狠狠地踢了救護車。
他走到前座去。發動。
「他媽的。」
顯然還是沒著火。
就在我們萬念俱灰的時候,精采的事可發生了。
「這裡是塔台,救護車及消防車請立刻出發在北跑道終點待命!聽到請回答,OVER。」
「什麼?」抓住無線電對講機,我幾乎大叫起來。
「不是演習,再強調一次,不是演習!OVER。」
3
就在我們都下來踢救護車的時候,我看到所有的車輛都往北跑道終點奔去。
這次來真的。
先是大型T-33消防車,聲音其大無比,像是森林裡的大象出動了一樣,驚天動地奔向待命位置。跟在消防車後面的是漆著黃色Follow me字樣的吉普車,那是屬於飛行管制中心的車輛。
另外有兩三部吉普車不約而同地奔向北跑道終點。看都不用看就可以猜出來是指揮官、副指揮官、政戰主任的座車,表示老大、老二、老三都已經出動了。
「救護車,請立刻就待命位置,我再重複一遍,請立刻就待命位置,OVER。」
「怎麼辦?」駕駛兵急得都快發瘋了,他再發動一次引擎,還是沒著火,「怎麼辦?場面事故視同前線作戰,無故不到可判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嚴重者可加重刑責,判處無期徒刑至死刑。」
「別慌,」我安慰駕駛兵,「別慌,別慌……」
「醫官,我看我們直接抬著擔架,帶著醫療用品跑過去算了!」醫務兵告訴我。
「開玩笑,要跑一、二千公尺……」
「總是比無故不到強很多。」
「到時候怎麼運送傷患?」我問。
「那邊車輛那麼多,隨便找都有一部。你人到了,誰都不能把你怎樣,」醫務兵一副老鳥的樣子,「要就快一點,不然飛機下來就麻煩了。」
我給駕駛兵一個眼神,「把擔架抬出來。」
「真的要跑過去?」
「你還敢說,平時都不好好保養車輛,你死定了。」
「我怎麼知道飛機真的會掉下來!」
好了,空軍是最科技先進的軍種。跑道上所有障礙都已經清除,消防車閃動著紅燈,所有車輛幾乎已經就位完畢,擴音器已經搭架起來。指揮官進入指揮位置,利用無線電與擴音器同時對塔台及周圍人員下達命令。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抬著擔架一邊跑,我忽然覺得很慚愧,倒不是難過,主要是丟臉。你看,在這麼現代化的部隊裡,我們竟然用跑的,而且還跑得踉踉蹌蹌。
「醫務所在搞什麼鬼?」果然沒錯,從擴音器的聲音就知道指揮官已經大發雷霆。
立刻飛奔過來的是黃色的Follow me吉普車。
「你們耍什麼寶?」飛行安全官探頭出來大罵。
「救護車臨時拋錨。」我露出無辜的微笑。
「搞什麼嘛,」飛安官把吉普車停了下來,「上來,上來,統統上來。」
駕駛兵坐在我的旁邊,我可以感覺到他一直在發抖。
「給我出狀況?」指揮官的聲音,透過麥克風顯得又粗糙又可怕,「看我不修理你們。」
比我們更遜的是陸軍的警衛連部隊。他們平時警衛機場安全,同時也負有支援救難的任務。有時候,我承認我們空軍實在不太了解陸軍的作為,不過我看見他們每個人都把洗臉用的臉盆帶出來,準備飛機迫降後救火,那實在是太誇張了。
「第一班!」下令的是一個掛階和我一樣的少尉排長,「就取水位置。」
有差不多一班十個人,輪流有模有樣地到消防車把臉盆裝滿水,並回來立正站好。
我看得出來指揮官頭上已經快要七孔冒煙了,他大叫:
「警衛連搞什麼鬼?他媽的拍《筧橋英烈傳》是不是?」
「報……報……告,指揮官,依照勤務作業手冊規定……」
他從袋子裡翻出一本破破爛爛,不曉得是民國幾年以後就沒有再修訂過的冊子。
4
過了不知多久,漸漸從海面那邊看到了一個小點,以及啪啪啪很清楚的螺旋槳聲。
「海鷗部隊。」
怎麼會是直升機?
「聽說命令是直接從總部下來的,會不會是演習?」醫務兵悄悄在我耳邊低語。
看起來飛機飛行得很好,完全沒有迫降的態勢。一切更陷入五里霧中。
「二十五公尺範圍內人員全部清除。消防車第一線待命。救護人員在消防車上風十公尺處第二線待命。」擴音器的聲音。
直升機的身影愈來愈大,捲起了一陣風,慢慢降落下來。
「消防車撤退,救護人員就飛機接運傷患。」等確定沒有爆炸的危險,指揮官的命令又下來了。
聽到命令,我和兩個醫護兵扛著擔架,低著頭,逆著風慢慢靠近直升機。
螺旋槳慢慢停了下來,裡面走出來一個軍官,他告訴我:
「病人在後面,從望安來的產婦,開始陣痛了。等一下下來的直升機就是。」
現在我搞清楚了。是救難,不是迫降。看飛機的番號應該是台中飛過來支援的救難部隊才對。
我放下擔架,往南方的天空望了一下。那就是望安的方向。看來今天的風浪不小。從澎湖本島坐船過去最快也要二、三個小時。望安島嶼並不大,騎摩托車只要二十分鐘就繞完一圈了。居民主要以捕魚為生。交通出入並不方便,常常看的是昨天的報紙。在那裡的衛生所想找一名護士都相當不容易,更不用說是醫院或者是婦產科醫師了。
「今天是禮拜天,國內沒什麼重要的政經消息,配合政策需要,這新聞晚上搞不好可以上頭三條。」那個中校向指揮官行了一個軍禮,似乎很興奮地表示。
現在我可仔細地看清楚了跟在他後面下直升機那幾個傢伙,手上拿著攝影機、燈光,以及麥克風。他們很快在跑道架設起他們的設備。
「好,醫官,我們整個國軍部隊的榮辱都繫在你的身上了,」他拍我的肩膀,「等一下我要你們抬著擔架,沿著這裡,有沒有,對,就是燈光的地方跑過去,你要稍側一下身,別擋到飛機上的國徽,知不知道?」
我點點頭。連指揮官都熱心地過來幫我整理軍服,顯然是很重要的任務。
他一直看著我,好像什麼地方不對勁。他皺了皺眉頭,終於問:
「你們有沒有好看一點的醫官?」
「沒有,就這一個。」指揮官和我同時都給他不好看的臉色。
5
為了讓狀況看起來很緊急,逼真,直升機的螺旋槳一直轉動著。
我不得不用很大的聲音對著病人喊話:
「妳還好吧?」
很典型的離島漁婦。她的頭上冒著汗珠,不過她仍然用很大的聲量告訴我:
「現在還好。不過過一陣子又會痛起來。」
看來像是產痛。並不需要任何緊急的處理,只要把她立刻轉送到島上的海軍八一一區域醫院應該就可以了。
我可以感覺到攝影機一直在轉動。我們合力把產婦搬上擔架,沿著燈光的路線跑回來,一切都非常優雅。
當我跑回來時,攝影機停下來。所有的弟兄對我報予熱烈的掌聲,好像看完一場精采的勞軍公演或演唱會似地。
「等一下,」中校摸著他的下巴,「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說不上來。」
他走過來,又走過去,忽然想通了。
「啊!救護車。」
「救護車哪裡去了?」這時指揮官也突然會悟過來。
「報告指揮官,救護車拋錨了。」飛安官跑過去向他報告。
「駕駛兵!」我看到指揮官氣脹了臉,「你搞什麼鬼?給我出這種狀況,你他媽的不要命了是不是?你看我有沒有辦法辦你?」
我的駕駛兵立正站在那裡,看得出來全身發抖。
「病人情況還可以嗎?」中校走過來問我。
我對他點點頭。又看他走過去和指揮官咬耳朵。
等他們咬完耳朵,中校面帶微笑地走過來,對著病人說:
「實在很不好意思。我們剛剛畫面拍得不好,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們希望能重拍一遍,但是一定要經過妳同意……」
同時我聽見指揮官向消防車下令:
「去把救護車拖過來。」
我看見消防車奔向救護車,在救護車前面綁上了一條粗麻繩,不久救護車在麻繩的牽引下,果然動了起來。
6
在畫面上,救護車跑得快極了。當然,誰也沒有看到拉著它的那條麻繩。
國軍部隊又以其精良的訓練、迅速的運送與精湛的醫技,成功地完成了救援的任務。
看著畫面上的自己,我總算明白那個中校一直問有沒有好看點的醫官那份苦心。
「國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衛人民,保障人民的財產與安全。平時,我們要做好敦親睦鄰與愛民的工作,以充分發揮軍愛民,民敬軍,軍民一條心……」
畫面上接著是指揮官接受訪問的片段。
出乎意料地,這條新聞竟是當天的頭條。許多部會首長參觀地方建設、主持運動會開幕、接見外賓這些新聞都排在指揮官畫面之後。
我們像打了一場勝仗一樣地歡呼起來。
很快地,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單位的電話響個不停。
「恭喜!哇,你們醫務所紅透半邊天了。」
「醫官,你的榮譽假放不完了。」
不久,指揮官的傳令兵也搬來了一打啤酒。
「總部來電嘉勉指揮官,指揮官很高興,要我搬這一打酒來嘉勉你們,給你們加菜。」
我們像過嘉年華會一樣,很快就把一打啤酒喝光了。
駕駛兵喝得一、二分醉意,他一掃今日的陰霾,大嚷著:
「沒酒了,我再去買一打!」
他掏出鑰匙,下意識走出去發動救護車。一發動,竟然著火了。
「他媽的,竟然發動了!」
老實說我們都被救護車嚇了一跳。
7
「你怎麼不跟他們一起去喝酒?」我問我的醫務兵。
「明天總部要來了,我還有一堆資料沒寫,哪有時間去喝酒?」
他從一堆資料裡抬起頭,看了我一眼。
「你在寫什麼?」我問。
「今天的事啊,新聞那麼大,明天總部來一定要看報告的。」
充—分—地—顯—示—出—軍—愛—民—民—敬—軍—軍—民—一—條—心—的—團—結—精—神……他一字一句地寫著。
「對了,醫官,你可不可以幫我問看看生了沒有?到底是生男的還是女的?」
「問這個幹嘛?」
「沒什麼好寫,寫寫這個也不錯。」
照說也應該生了。我撥通了電話,接上今天與我交班的醫官。
「我是機場的醫官,我想知道今天送過去的病人生產了沒?」
「病人才三十四週,生什麼生?」
「今天不是有產痛嗎?」我問。
「你說那個哦,」他停了一下,「我們照過X光片,腸子堆積了一些糞便,應該是便秘。」
便秘?我怔了一下。
「醫官,到底是男是女?」
「是男是女你就不用寫了。」掛上電話,我忽然覺得好笑。
叭——叭——叭——救護車的喇叭。
「快點,醫官。我們要去慶祝了。」他們在救護車上大叫。
「你確定不去?」
「我再寫完政戰教育,還有成效,就好了。」他回答。
「哎喲,我們根本沒空問她,她那麼痛,你還有時間做政戰教育,這種報告誰相信?」又要捏造事實。
「沒辦法,這是規定。」
「然後她接受了你的教育,居然還有成效?」我睜大了眼睛。
「當然,她受了我們英勇行為的感召,自然會說出一些內心的話,那就是我們的成果……」
「你退伍以後可以去寫小說了!」我告訴他。
「難道你不覺得這一切都很圓滿,大家都很高興嗎?」醫務兵回過頭來問我。
叭——叭——叭。救護車上傳來的聲音。
「快點啦!」
我笑了笑。不曉得為什麼,我忽然想起我的長官告誡我的話:
「再滑稽的事都有它嚴肅的一面。」
「到底要讓她說什麼呢?」他不斷地搔著腦袋,「哎,管他的。」
然後我看見我的醫務兵終於寫完了他報告千篇一律的最後一行。
「李——總——統——很——英——明。」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離島醫生【三十週年紀念版】的圖書 |
 |
離島醫生【三十週年紀念版】 作者:侯文詠 出版社:皇冠 出版日期:2024-04-0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72頁 / 14.8 x 21 x 1.3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5 |
散文 |
電子書 |
$ 285 |
散文 |
$ 300 |
現代散文 |
$ 300 |
散文 |
$ 300 |
中文現代文學 |
$ 323 |
小說/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現代散文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離島醫生【三十週年紀念版】
「等飛機掉下來?」我睜大眼睛問。
「對,」長官說:「這就是你往後最重要的工作。」
☀三十週年紀念版☀
只有侯文詠,可以把當兵寫成一部文學!
那年的風島艷夏,那一段段難忘的「風」中奇緣。
不論退伍多久,想起澎湖那段服役時光,侯文詠似乎還聽得見戰鬥機、運輸機轟隆隆的聲音。
更永遠記得當時的任務是「等飛機掉下來」,以及出動真槍實彈包圍一隻小狗!本以為身為醫生,生死場面已經見過不少,但那趟回台北搭乘的「老母雞」,竟是和死神最接近的一次!醫官的配備更是難忘,用最新的救護箱,裝著過期但不能丟的藥品,還有一輛不一定發得動的救護車……眼界大開的場面歷歷在目,彷彿預習未來人生將面對到的荒謬。
小島的軍旅生活卻也淳樸,休假時做個觀光客,等到不再覺得稀奇,觀光客成了半個當地人。每晚的「熱線」時間,每個大官小兵都成了慈祥體貼的男人,對著話筒維繫著遙遠又親密的日常。
澎湖的風持續地吹,吹送著各種離譜、嚴肅、奇妙的見聞與感悟,也吹整成離島醫生心中的氣度與風景。一個又一個年代過去,生命無窮無盡地循環,偶爾在一個多風的日子裡,陽光來得正好,那些遙遠的什麼似乎又都回來了。
☀
如果時代慢慢改變,有一天,真的有愈來愈多人看完了故事,覺得不可能發生,或者是大叫荒謬,我相信我會覺得開心。
屆時問我,我也許會回答:「從前從前曾經有過一個年代,我們都不怎麼滿意,卻又沒什麼好辦法。不過它已經過去,不再回來了。」
是的,不再回來了。那時候,一切都美好。
我們在這個不確定的年代裡,充滿渴望與期待。
──侯文詠
作者簡介:
侯文詠
台灣嘉義縣人,台大醫學博士,目前專職寫作。
侯文詠Facebook:www.facebook.com/houwenyongpage
●侯文詠官方網站:author.crown.com.tw/wenyong
章節試閱
沒有飛機掉下來
在我退伍以後很久的一個夏天,我忽然接到一通來自澎湖馬公機場的電話,電話那邊傳來是我後期醫官的聲音,他用亢奮的聲音告訴我:
「我告訴你,飛機掉下來了!真的掉下來了!」
隔著電話,我聽到了飛機引擎聲,逼真的臨場感。
「有沒有人傷亡?」我問他。
「沒有。」
他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連珠炮似地跟我說個不停。
真的掉下來了?我保證那絕對不是幸災樂禍,但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的感覺。
掛上電話,耳朵都是澎湖機場上轟隆隆戰鬥機、運輸機、噴射客機的聲音。我想起了從前開著救護車,守在機場的那些日子。
當...
在我退伍以後很久的一個夏天,我忽然接到一通來自澎湖馬公機場的電話,電話那邊傳來是我後期醫官的聲音,他用亢奮的聲音告訴我:
「我告訴你,飛機掉下來了!真的掉下來了!」
隔著電話,我聽到了飛機引擎聲,逼真的臨場感。
「有沒有人傷亡?」我問他。
「沒有。」
他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連珠炮似地跟我說個不停。
真的掉下來了?我保證那絕對不是幸災樂禍,但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的感覺。
掛上電話,耳朵都是澎湖機場上轟隆隆戰鬥機、運輸機、噴射客機的聲音。我想起了從前開著救護車,守在機場的那些日子。
當...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