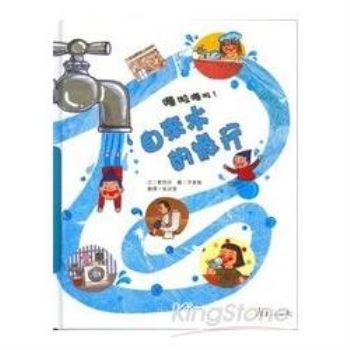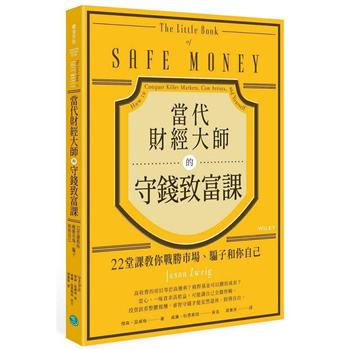第169屆
✦芥川賞入圍作品✦
未成年偶像 × 推活文化 × 夢小說
真名、藝名、網名、未命名,
哪個才能真正代表你?
|特別收錄|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印刷留言簽名扉頁
# # #
{ 請輸入名字。空欄的話,將顯示為 ##NAME## }
我的名字是什麼呢?
如果不由你喚起,那就沒有意義。
# # #
✦芥川賞入圍作品✦
未成年偶像 × 推活文化 × 夢小說
真名、藝名、網名、未命名,
哪個才能真正代表你?
|特別收錄|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印刷留言簽名扉頁
# # #
{ 請輸入名字。空欄的話,將顯示為 ##NAME## }
我的名字是什麼呢?
如果不由你喚起,那就沒有意義。
# # #
▍那段被閃光燈照亮、與妳一起度過的時光,
▍被他們稱之為「現代社會的黑暗面」——
▍可是我們的黑暗,明明那麼耀眼。
小學五年級的雪那與美砂乃同為演藝經紀公司的培訓生,和人氣高的美砂乃不同,雪那一直沒有大紅的機會。上了國中後,身為培訓生的雪那,要面對情緒勒索的母親、嚴厲的經紀人;身為學生的雪那,要面對知道她曾經拍攝兒童泳裝照,而帶著有色眼光對她冷暴力的同學。
雪那,藝名「Setsuna」,網名「雪路」,她沉迷於可以自填姓名的二次創作「夢小說」,閱讀時卻從不填上名字,任由系統顯示未命名的「##NAME##」。在熟悉的故事裡,沒有名字的她,藉著失去身分得以安心。然而,她所喜愛作品的漫畫家因持有兒童色情影片被移送法辦,同為BL研究社的朋友指責她怎麼能悶不吭聲,應該要以自身經歷揭露社會黑暗面。
又是黑暗面。雪那不喜歡這個詞,那就像遇到陌生領域、面對沉重現實時吐出的咒語,好像只要說出這個詞,就可以代替誰表現出憤慨與憐憫。貧窮的黑暗、業界的黑暗、無以名狀的黑暗。她想起在那段「黑暗」的日子中,美砂乃朝她伸來的溫熱小手,呼喚她的溫柔嗓音。她的名字,是在那一刻才有意義……
※夢小說:流行於ACG界的二次創作小說類型,讀者可以填入自己的名字,系統會取代小說內原創角色的姓名,讓讀者能與喜歡的原作角色發展故事。如無填入名字,系統會顯示預設的「##NAME##」。
▶ •၊၊||၊|။|||| |
▸▸「即使不挺身而出,你也不需要用『我很弱小』來否定自己。」
沒有人能定義你是不是受害者,也沒有人可以決定怎樣的事算得上是受傷。
沒有人能斷言你的選擇有沒有意義,揭不揭穿和原不原諒都由你決定。
如果你可以為他人,堅強好幾次;那麼也為自己,好好受傷一次。
▸▸為偶像打造世界觀的作詞家,最貼近、最犀利卻也最溫柔的觀察
兒玉雨子高中開始即以作詞家身分出道,以「Hello!Project」旗下的日本女團為主,亦為遊戲《偶像大師》、《IDOLiSH7》,動畫《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兔女郎學姊》、《藍色監獄》等作品的歌曲作詞。抱持著「原本就知道未成年偶像存在的我,或許可以寫這個題材」的想法,完成了這本書。
▸▸繁體中文版序:〈我無法苛責那些在遭遇困境時選擇沉默的人〉
「被害者之所以會選擇沉默,當然是被純粹的惡意所逼迫,但或許也是因為害怕這樣的圍觀。因此我無法苛責那些在遭遇困境時選擇沉默的人,或明明痛苦不堪,卻故作沒事傻笑的人。用不著說,若是每個人都能在當下鼓起全副勇氣對抗,再也沒有比這更棒的事了。然而這世上到底有幾個人能夠一出世就立刻收住哭聲,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我們應該都是依靠身邊的人哺育、以只屬於自己的名字被呼喚、學會說話,然後才慢慢站起來的。」
▸▸一字一句,寫給每個人心中那個未命名的自己
「要在如此小巧、小到可以完全收進掌心的小螢幕裡,專心致志地輸入綿綿不斷的訊息和閱讀夢小說,需要不光是崇高或憤慨的其他情感,要不就是得用混合這些情感而成的燃料當作能量。」
「沒有任何造型品的赤裸髮絲散發出油脂的氣味,凝固的奶油似乎黏附在我的每一個角落,罩上一層薄膜。我覺得只要有這層膜,往後就再也不會與世界有任何摩擦了。」
「霸凌?我沒有遇上這個詞彙能夠聯想到的種種,像是躲在廁所吃便當、被人潑水、被拳打腳踢,或是室內鞋被放圖釘。班上同學雖然不會主動找我攀談,但如果我開口,他們也不會不理。有些女生會騷擾,有些不會。不會騷擾的女生也不會制止騷擾行為,只是這樣而已。」
「非得做出什麼,否則一切都是白費嗎?什麼都不是的我,會怎麼樣?」
▸▸文字工作者感動推薦:「我看見妳們了!」
「在懷抱星夢的少女們或平淡或歡樂的日常對話裡,暗藏著過曝風險與提早長大的傷痕。
行為舉止要像大人,在鏡頭前卻得像小孩,是她們永遠的矛盾。
即使放棄成名,這些過往依然糾纏著她們,就連二次元淨土也被汙染。
曾用過的藝名、拍過的電視廣告、穿著學校泳裝的照片,她們真正想掙脫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作家/ami亞海
「剝去未成年偶像、兒童色情、夢小說、同人文化等標籤,《未命名 ##NAME##》所探討的主題,意外樸素而單純──如何認識自己的傷痛。小說主角雪那,性格乖巧、隨和、欠缺自我主張,她習慣一再練習笑容、練習可愛、練習被人拍攝,習慣默默刪去辱罵郵件。她是只能透過夢小說,與喜歡的角色互喊『怎麼能這樣就受傷』的人。怯於受傷、疲於受傷,也因此不曉得怎麼憤怒,需要學習生氣。讓人傷痛的經歷,不全是灰暗的,其中有夢想、有嚮往、有友伴、有肯定,所以去承認其中的醜陋與剝削,才會如此困難。這是一首,述說著被看見也不被看見的孩子內心世界的悲傷小調。」——文學評論人/小部
「這是失去了姓名的小說,也是試圖用小說拯救自己的小說。『夢小說』的特色在於輸入自己姓名,以便沉浸在二創的世界中,但對主角而言,她的『姓名』反倒是最無法代表自己的事物。夢小說看似虛幻無依,卻仍像凝固的奶油般,保護她不被世界摩擦。《未命名 ##NAME##》正是這樣,微妙捕捉到當下社會予人的諸多摩擦力,是相當切合這個時代,充滿細節感,唯有懂的人能懂的一部作品。」——小說家/許俐葳
「這個故事,沒有辦法斬釘截鐵,沒有辦法乾脆俐落,讀者想要寄與的同情、厭惡或憤怒,都很可能找不到確切的目標——那正是這類事件最令人感到痛苦的地方,被本書作者兒玉雨子以精確的方式呈現了其模糊的本質。真的沒有問題嗎?我們要不要再多想一想?那是我花了過長的時間才讀完《未命名 ##NAME##》的原因,也是這個故事之所以必須如此瑣碎又總是讓情節踩在邊界的原因。就像善惡與是非,從來不那麼簡單方便,我們總是需要再多想一想。」——小說家/劉芷妤
「川端康成《睡美人》描述一家旅館,專門把貧農少女下藥昏迷,放在被窩中,供應給陽痿的老人過夜,禁止性交或弄傷少女,賣點是她們對發生的事一無所知。《未命名 ##NAME##》寫出了現在像這樣的創意私房裡,少女醒來看到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她會悲憤、反擊,還是想忘掉?讀者意外的是,她發現自己才是輿論攻擊的對象。而她只有加入敵營一起攻擊她自己,才能免於崩潰。那麼,難道這個社會不是更大的創意私房嗎?」——作家/盧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