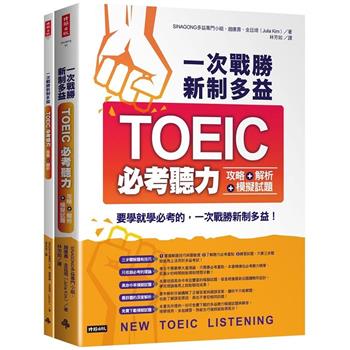序
不廢江河萬古流∕何英傑
惡浪滔滔,逝者如斯。雲散月明,不逝者如斯。
先生生於動亂,長於動亂,本應是在學術界大放異彩的人物。不料青壯之年,流放二十年,與家人分離,與種種美好的人生追求分離。連走避的念頭和機會都不曾有,便捲入了絞碎一切的黑洞裡。這不單是一國災難,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浩劫。清初薙髮,號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此則薙腦,是「留頭不留腦,留腦不留頭」。萬里山河,邊疆農村,轉眼成了巨大沒有圍牆的集中營。營裡關的不是戰犯、不是政敵、不是異教徒,而是思想有罪的知識份子。而陷人入罪者,竟是身邊左右怎麼也想不到的親友同事。反右以降,江山如焰。
先生有言:「當民族文化遭到摧殘或將瀕於泯滅,其痛切之情,尤深於亡國亡身。」此真英雄語。偏偏大禍臨頭者,正是此等人。林沖夜奔,恨天涯一身流落。蘇三起解,未曾開言心內慘。假戲且賺人熱淚,那麼百萬人夜奔、千萬人起解的一幕真戲,又該如何唱演?我嘗想,換作是我,耐不耐熬?熬出的是怎樣一條命?熬過來會怎樣恨世恨人?孟子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諸葛亮言「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心經》言「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我無法臆測,若孟子、孔明、觀世音躋身右派,將如何自全?如何傳道?還是也如學者馬一浮的下場,在紅衛兵抄家時乞憐一方硯臺,卻賞得一記耳光?
書中甚少敘述這些磨難,僅〈右派情蹤後記〉、〈鬚眉走出小兒狂〉兩篇稍見。一述夫妻情深,一述落難知交,均是隱隱文字,憂愁風雨。但此書到底不是傷痕之作,而是學者之書,總共收存了四類篇章。一是詩論,有黃宗炎詩、潘天壽詩、杜牧〈張好好詩〉之探討。二是劇評,有《西樓記》、《爛柯山》、《千金記》、《蝴蝶夢》、《臨川夢》、《燕子箋》、《風箏誤》等諸曲漫談。三是序札。四是交遊軼事。先生工於詩詞戲曲,一生學問在此。雅士方家,不難見其治學態度與藝術上的琢磨功夫。先生蒐文成集,訂名「瓿齋文存」。「瓿」是瓦罐,取意「覆瓿」,謙稱此書沒有價值,只能用來蓋住盛水盛醬的瓦罐。我想,若此書合該「覆瓿」,也該是拿來覆在近代中國這隻動亂的大瓿上!先生厚愛,囑我作序,曰:「此書有周有光、周汝昌書跡,又有沃興華題簽。若加上你,則老、中、青三代備矣,豈不有趣?」我本不敢當,聞言則不敢辭。
先生文章,透著一種史論精神,一種面對歷史與人物的觀點。〈黃晦木吳游即事詩考釋〉明為論詩,實則論人。〈聽天閣詩淺探〉的「詩為心聲、書為心畫」,乃在人格風格之間立論。〈「有竅」與「無竅」〉,描繪了張漣的幽默,譏笑吳偉業的降清事。〈「英雄泣下淚無聲」〉,則以虞姬不離項羽的橋段,寫錢謙益與柳如是的愛情與志節。篇後追憶韓不言、林鍇,閱其事,讀其詩,如見其人。這原是中國讀書人非常在乎的主題:面對變局,時代感受是什麼?自我分際與自我選擇是什麼?後人讀其事,正該看清前人的治亂興衰,究竟是源於如何的人物賢奸?
譬如歷來鬥爭下的受難者,如今死則死矣,老則老矣,眼看著身名俱滅,加害者愧疚了嗎?右派改正,加害者改正了嗎?往事如煙,零落成泥。他們一生被浪費了,時間到底站在誰那邊?倖存者於國於民,早已有心無力。對照他們日益銷減的影響力,加害者贏了嗎?明清之後,政體益趨專制。民國內憂外患,繼續加劇了軍閥集體主義的獨裁,乃至文化大革命達於六百年來的高峰。往下呢?近代西方人揭櫫了人權與民主,為二十一世紀立下法度。中國敗,學術先敗。中國要興,學術也該先興。當代中國人準備拿出什麼像樣的人道主義眼光,為此後百年國運與人類社會立下法度?
這是衰世之書,所記衰世之事,但也不妨是衰世轉盛世之書。因為歷劫之餘,仍有不肯屈服的人心品質。我讀先生文章,想到他所在乎的藝術,想到他在牛棚中偷偷讀書,想到他事過境遷,依然回到自己鍾愛的所學上,把生命完全融入一個傳統之中,樂此不疲—我知道加害者沒有贏。或為先生抱屈,一等才學,只酬得文章數十篇。但人各有命,顏回也無一詩一句流傳。孟子說:「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人活著,就這身風骨。薄薄一書,先生盡了餘力。他透過此書告訴我們,在那樣的動亂時代中,他的心還如「蒸不爛、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響噹噹的一粒銅豌豆」。至於損失,那是國族損失,是人類文化的損失,不是他個人的損失。
頂天立地,堂堂正正,便是人物。是為閱讀心得,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