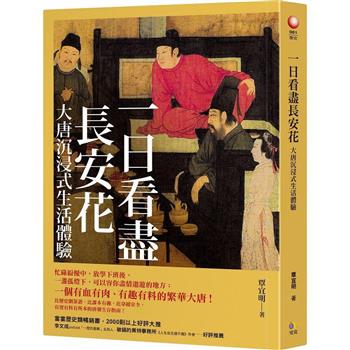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遺神的圖書 |
 |
遺神 作者:吳鈞堯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4-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5 |
文學小說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小說 |
$ 315 |
台灣文化/民俗 |
$ 315 |
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50 |
文學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吳鈞堯的《火殤世紀》,寫金門族人的百年史,在野史中滲入正史的「實錄」;《遺神》則描繪金門的千年「神族」譜,在正史中融入大量稗史的虛幻傳奇。吳鈞堯鋪寫金門歷代神祗,重新定位金門在歷史中的位置—地處邊陲的金門人參與了歷史的締造,是中華文化的必要組成。《遺神》並非奇幻神話,如此才能理解吳鈞堯的自述:「我想訴說金門更長的時間,透過風獅爺尋找身世,上溯千年,探討人跟神。」名為寫神,根底仍落在「人」身上,是《火殤世紀》的深層延續。
──張清芳,山東魯東大學教授
作家的書寫往往逃不開故土的滋養,對吳鈞堯來說,這既是鄉土情懷的釋放,也是宣講金門故鄉的勇氣與抱負。在《遺神》這樣難寫的題材,吳鈞堯反而肆意揮灑,呈現大量獨創的想像性情節。吳鈞堯很有創意地站在了神的角度,神靈會撒嬌,會調皮,會沮喪,會猶疑,會感恩。時至今日,我們不再願意相信什麼,但至少請記得,眾神都在告訴我們,人生不要只經營自己。
──陳美者,福建省文藝理論研究室
這是個追索的故事。一問何為神?再問何為人?在《遺神》中,神與人是互相對應、拉扯的兩股力。神雖為神,卻無法主宰命運。神或人,都籠罩在更巨大的力量中。吳鈞堯在書寫神與人的二重關係時,也記載了金門移民擺盪的歷史。
──黃淑真,東海大學研究生
作者簡介:
吳鈞堯,現職《幼獅文藝》主編。出生金門昔果山,十二歲遷往台灣,就讀光榮國中、南港高工、中山大學財務管理、東吳大學中文所,求學過程多次轉向,最後仍定心文學。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小說獎,梁實秋、教育部等散文獎以及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二○○五、二○一二年獲頒五四文藝獎章(教育類與小說創作)。繪本著作《三位樹朋友》獲第三屆國家出版獎,入圍香港豐子愷兒童圖書獎前十強。金門歷史小說《火殤世紀》,獲二○一一年台北國際書展小說類十大好書、第三十五屆新聞局圖書類文學創作金鼎獎。其中〈泥塘〉一篇亦入圍二○一三年台北書展「華文出版與影視媒合平台」焦點推薦書。著有《金門》(爾雅)、《如果我在那裡》(聯經)、《荒言》(三民)等,及學術論文《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
用千年「神族」譜講述金門人歷史
張清芳
在二○一○年遠景版的《火殤世紀》中,作家吳鈞堯選取一九一一年至二○○四年間的歷史時段,描述出金門近百年的近代史,在風雲際會中勾勒出台灣島、金門、祖國大陸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個人、家族和國家關係,堪稱為史詩性的家族書寫。作為《火殤世紀》的續篇,吳鈞堯在新作《遺神》中,則把目光投向悠遠漫長的金門歷史縱深處,從唐末至今日金門的兩千多年歷史的書寫中,抽絲剝繭地寫出金門島的動蕩、變遷和發展過程,以及不同歷史背景中金門神祗的故事。
與《火殤世紀》側重寫「人」的生...
02夢裡的火
03墓穴與神
04神的聲音(本文獲九歌出版社一百年年度小說獎)
05戲台的戲
06四戰太武
07廢城之火
08孤風行人
09他們說神
10海上聽蟬
11神的鞦韆
12海的遺言
13祠堂的魚
14逮風獅賊
15追神少年
16搭風獅橋
神與人,一起跳 黃淑真
在海島,傾聽神的聲音──讀吳鈞堯的《遺神》 陳美者
用千年「神族」譜講述金門人歷史 張清芳
跋.神有了回音 吳鈞堯
- 作者: 吳鈞堯
- 出版社: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4-18 ISBN/ISSN:978957390842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