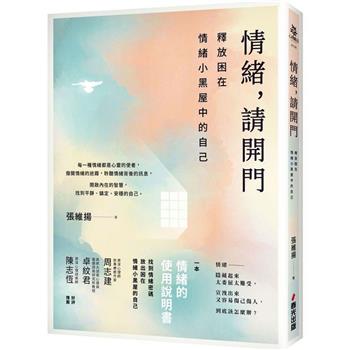從藏書、著錄到鑑賞,書話是一種收藏的趣味
德國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一個收藏家記憶中最精彩的時刻,是拯救一部他從未曾想過、更沒用憧憬的目光流連過的書,因為瞥見此書孤伶伶地遺棄在書市,就買下,賦予它自由。」一如所言,資深編輯吳興文在《書緣瑣記》中從自己開箱整理藏書談起,細數關於藏書的過程與書籍背後的歷史與時代意義。由於工作上的編輯經驗,吳興文在閱讀同時也注意到書籍出版環節中的印刷、裝幀等細節,輔以作家的軼聞故事,讀者看來猶如身歷其境,更明白許多單純閱讀所難以察覺的知識。書中不乏作者多年來的專業見聞,如八○年代牯嶺街舊書攤的黃金時期、早期中國大陸淘書尋寶的樂趣,亦有書籍出版至今的歷史價值,例如原本初版只印一千本的瓊瑤《窗外》、吳濁流《亞細亞孤兒》初版本、朱天文《淡江記》等等。
吳興文談及近年所見的書店風景,也反思現代的讀者究竟需要書店提供什麼樣的服務,書店應如何改變以因應時代潮流。面對網路時代,古書店的傳奇故事與實體新書店的競爭壓力,紙本書與電子書兩者是淘汰抑或是互補?他們有各自生活的小確幸,而書與書店該與怎樣的面貌存續,向讀者傳遞知識?作者在書中自有獨到的見解。義大利文學巨擘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曾說:「藏書是一種自我聊慰、孤獨的現象,你很少找得到人可以分享你的激情。」《書緣瑣記》謹以為記,讓所有愛書、藏書的讀者們得以分享吳興文的淘書之樂;有書,並不孤獨。
作者簡介:
吳興文
1957年生,台北市人,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一個終生以愛書、編書、寫書、藏書為職志的編輯人。現任北京海豚出版社特約總編輯,深圳《晶報》專欄作家。曾任遠流博識網(北京)文化公司總經理、遠流出版公司副總編輯、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特別助理。著有《票趣˙藏書票閒話》、《圖說藏書票:從杜勒到馬諦斯》、《我的藏書票之旅》、《書癡閒話》、《我的藏書票世界》。
章節試閱
《惘然記》初版本
張愛玲的文字好比上海的風土,比較溼潤,除了視覺的效果外,令人聯想到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彷彿「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不知不覺讓人喜歡上她。一個地區的文字如果偏油膩,肯定會喜歡張愛玲。就像民國初年的白話文,是剛解開纏足的大腳,充滿白開水似的形容詞和副詞,到了張愛玲,或《古今》雜誌時期的黃裳,融入古典詩詞,或加上文史掌故的淬鍊,遂使大多數讀者眼睛為之一亮;例如:〈色,戒〉開始描寫王佳芝「胸前丘壑」、「嬌紅欲滴」、「雲鬢蓬鬆往上掃」等詞句。可貴的是,她的小說拆開來讀像散文,值得慢慢地品讀。
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版本,已經成為張迷追逐的標的。她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傳奇》,上海雜誌社,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初版,鄧散木題書名,共收十篇;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再版,增加〈再版的話〉,封面改由炎櫻設計;山河圖書公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出版增訂本,增加新作五篇:〈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前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跋〈中國的日月〉;以上只見初版本在私下交易,不但品相不佳,而且非萬元人民幣不可。以及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國科學公司初版,她自己設計的封面,在網上交易,但品相不好,仍需八千元人民幣(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可見張愛玲是很重視自己的作品,每個階段再版或增訂版都會修改文字,或者交待緣由,值得像奧德雷‧漢納曼編纂《海明威書目大全》般,幫她編成一部現代文學書目的典範。可惜的是,臺灣早期出版的都沒有註明出版年月,以我看到的《秧歌》,只註明封面設計夏祖明。不像瓊瑤《窗外》,只有第一版沒有註明,再版以後都註明,並且註明印數,我才有辦法確認沒有註明出版年月的版本是第一版。
《惘然記》的第一篇〈惘然記〉,應該是代序,交待成書的經過;並在版權頁註明一九八三年六月初版。代序從北宋一幅《校書圖》開始說起,說到一九五○年間寫的三篇小說,〈相見歡〉與〈色,戒〉發表後又還添改多處;〈浪花浮蕊〉最後一次大改,才參用社會小說做法,題材比近代短篇小說散漫,是一個實驗。這三篇小說都曾使她震動,不知不覺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就像「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因此結集時題名《惘然記》。
也許是當時出版時,她已經引起海內外學者注意,並且有人擅自出書,所以在代序結尾:「不得不囉嗦點交待清楚,不然讀者看到雙包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還以為我在盜印自己的作品。」真是無奈!是否因此才在版權頁上註明出版年月?希望有人將她沒有註明出版年月的版本公布出來,那將有助於張愛玲的研究與推廣。
《惘然記》初版本
張愛玲的文字好比上海的風土,比較溼潤,除了視覺的效果外,令人聯想到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彷彿「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不知不覺讓人喜歡上她。一個地區的文字如果偏油膩,肯定會喜歡張愛玲。就像民國初年的白話文,是剛解開纏足的大腳,充滿白開水似的形容詞和副詞,到了張愛玲,或《古今》雜誌時期的黃裳,融入古典詩詞,或加上文史掌故的淬鍊,遂使大多數讀者眼睛為之一亮;例如:〈色,戒〉開始描寫王佳芝「胸前丘壑」、「嬌紅欲滴」、「雲鬢蓬鬆往上掃」等詞句。可貴的是,她的小說拆開來讀像散文,值得...
推薦序
推薦序/這一代的「書苦」 胡洪俠(資深愛書人,深圳《晶報》總編輯)
忽然不想再寫三千字以下的文章了。我剛寫了篇〈臺灣的「一九八四」〉,一萬多字;準備寫的那篇〈壽宴〉,少說也得三萬字。年齡見長,文章亦應更長,這算不算「人與書俱老」的翻版?且說某日,我如此盤來算去,正得意間,不小心接一電話,竟是臺灣的興文兄自北京打來的。他說他的《書緣瑣記》就要出版,其中大半首發於《晶報》「深港書評」,「不讓你寫序,感覺、似乎、好像、難免有些不太對頭。」
我迅速想像電話那端興文兄結結巴巴邊說話邊點頭如點數的樣子,隨即應承下來。不答應寫序確實不太對頭,應承或硬撐下來我又有點撩興。書中他的書話每篇多在千字左右,序文字數理應以不超千字為宜。可是,我忽然不想再寫三千字以下的文章了,這讓我如何是好?
於是我說,先把書稿傳來。
他說,其實你應該都看過了。
我說,我必須再看一遍。
這一「再看」,一篇一篇連起來看,我不期然而別有所悟:以這本《書緣瑣記》而言,別人讀時大可與興文同遊書海,共浴書香,分享得書之喜、淘書之樂,我卻獨獨對其字裡行間瀰漫的「書苦」體會尤深。原來如今愛書可能會愛得很苦;原來一生追尋「書香」的人遭逢互聯網時代,最終心裡裝的也許是「書苦」;原來這讀書愛書聚書藏書寫書出書終究是一件「苦中作樂」的事情。
既然是「苦中作樂」,我就樂得把纏繞吳興文數十載的書香暫置一邊,聚精會神數一數他的「書苦」─
二十世紀六○年代初,臺北藝文印書館嚴一萍先生發願重編並影印《叢書集成》。他優選底本,線裝精印,聚齊四千餘種,費時七年而大業告成。到了八○年代末期,興文購其《酒譜》等書而想見嚴氏其人,誰知先生已然病逝。書在人亡,豈不痛哉。況且這尚在的書,像《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改琦繪《紅樓夢圖詠》,據說也已為大陸書友蒐羅一空了。某日興文兄懷揣思古念舊之情重遊印書館,發現店內雖說古韻猶存,但差不多就剩下滿頭銀髮的老闆娘了。此是一苦。
三十多年前,他上大三,主編一份四開雙週刊校報,常常跑到印刷廠體會活字排版的甘苦。鉛活字,老師傅,繁華街區的小印刷廠,而今安在哉?那時,他還去重慶南路書店街,逛商務印書館,逛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覺得店內陳設俱是老派味道,處處與眾不同,儼然是哪位大藏書家的書房。曾幾何時,而今俱不復識矣!此又是一苦。
臺北牯嶺街舊書攤曾經多麼興旺,可是等到吳興文上高中時,書街已似漸空漸盪的末班車了。即使如此,此地此街,仍是他難以割捨之所。再後來,他的家竟然就搬到了南昌路妙章書店對面的巷弄,自相鄰一條巷子穿過,可直達牯嶺街。巷口右轉十公尺,即是赫赫有名的人文書舍。店內兩排書架面對面,中間路狹,僅可容兩人擦肩而過。他在這裡買過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編印《珞珈》第二十七期「紀念陳通伯教授」特輯,還有一九六九年三月經濟畫刊總社限量重印的《弘一大師永懷錄》。凡此種種往事,隨著人換屋空,如今漸漸湮沒了。興文只好用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2016)的話自嘲─「藏書是一種自慰、孤獨的現象,你很少找得到人可以分享你的激情。」自以為是天下至樂,到頭來只能自樂獨樂。再說此樂香甜,也難掩箇中苦味。
古舊書價越來越高了,冷攤揀漏也越來越難了,近十幾年間吳興文穿梭於北京、臺北之間,眼睛不停尋尋覓覓,心中難免慘慘戚戚。某日在某店,淘書畢,正結帳,目光不知為何就鑽進一張書桌腳下,見光暗處層層疊疊者,雜亂無章者,在在皆是零落殘籍。他抽出一紫色活頁夾,打開,竟是署名曹端群的〈我的練字經過〉散文手稿,寫在「國語日報社副刊稿紙」上。如亂葬崗瓦礫中得一片秦漢瓦當。吳興文長嘆「皇天不負苦心人」。唉,此嘆雖有幾分氣魄,所嘆之人畢竟仍是「苦心人」。
藏書家是與舊時月色打交道的人,其苦其樂都與歲月流逝有關。當年平鑫濤為瓊瑤印《窗外》單行本,料想不會暢銷,只印一千本給作者留個念想。誰知這小冊子自己爭氣,銷量一飛衝天,一週後加印兩千本,然後再加印三千本,再加印五千本,再加印一萬本……一年之內,銷量過百萬。即使在當時,《窗外》初版本也已十分難得,何況今朝。可是人家吳興文竟然輾轉從一位歐巴桑手上得到一冊。雖紙張泛黃,歲月留痕,然觸手若新,幾未曾讀。這該是興文開心時刻了,誰知他又「苦」從中來:英姿少年今老矣,初版青春安在哉?
二十世紀八、九○年代之交,是吳興文獵書生涯中香噴噴的歲月。那時大陸懂書又有財力的藏書者少,臺灣愛書人有機會能來往兩岸者也不多,琉璃廠一帶,海王村店內,在他眼中俱是物美價廉之書。他說:「一九八九年九月,秦賢次、王國良、志文出版社少東與我,連子善兄一起,專門為淘書,從上海轉機到北京。有一天他們爬長城,我乘機溜到琉璃廠淘書,收穫頗豐。」其中淘到的一本書便是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可是,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讓中國書店於一九九三年拿到一本「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目錄。得聞此訊,吳興文心知不妙,暗暗叫苦,料定大陸舊書物美價廉時代行將結束,他這樣的海外書客北京上海一路揀漏偷著樂的好日子眼看一去不復返了。「果然,」他說,「當年九月,在他們舉辦『北京首屆稀見圖書拍賣會』的目錄,看到和臺北拍賣會的目錄,不但部分書種雷同,而且估價相近。事後北京收藏家回憶:書之底價,均是在中國書店門市部標價後一律加個零。」今天憶及此節,他仍是別有一番苦味在心頭。
吳興文獵書的舞臺不是拍賣會,而是大大小小新新舊舊的書店。書店越少,書店裡的書越少,他所嚐收藏之苦就越大。苦處越多,就越是不甘心。所以近些年他對兩岸書店的興衰最敏感,對拯救書店的思考也獨多。他逛臺北永漢書店,很不滿意這家過去標榜「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的書店,面積不僅比從前縮小五分之一,主體區域也變了味道。他逛臺北一○一大樓的PAGE ONE書店,發現其營業面積也縮小不少,門面局促於一隅,宛如隱藏在迷宮般的商場。於是他以救苦救難之菩薩心,拋出普度書店之方略:全球化大都會在社區書店和重要商圈之外,都更需要地標書店,如巴黎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紐約高談書集(Gotham Book Mart)、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City Lights Booksellers & Publishers)等;書店如紙質媒體,需具有一己之個性。營造書和人相遇的場所,誘使顧客留下來,拿起書來,多在書架前流連;書店不只是賣書而已,書店應該將聚集在那裡的資訊重新加以包裝,進而產生創意,創造出新的商品……
我原以為,像吳興文這樣的重症書痴,趕上這樣一個到處有人預言「紙質書即將消亡」的碎片時代,迷戀書籍雖飽嚐前輩愛書人不曾體會的種種苦處,晚上作起夢來,總應該是香甜的吧。他的室內、床上、身邊,環繞著情色美人藏書票、木刻石板插圖本、稀見絕版珍本書,還有竹刻硯臺紫砂壺,美夢的元素俱已齊備,待夜深人靜,酒意正濃,睡眼初閉,精神恍惚間,似有佳人擁書而至,一時間多少書香氤氳,多少書緣聚合,什麼美夢作不出來?可是,他卻在書裡說,他常常作惡夢。
俞曉群有書名曰《這一代的書香》,吳興文其實應該再寫一本書,名字不妨就叫《這一代的「書苦」》。如果真的要寫,興文兄又讓我寫序,我就不這麼費勁寫幾千字了。我只需把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改編如下:
善本如聚,
價格如怒,
牯嶺廠甸無歸路。
望拍場,
意躊躇。
傷心網絡經行處,
古今萬卷都做了土。
興,書人苦;亡,書人苦。
寫至此,話已盡,無奈還不到三千字。食己言而肥己,這種事幹不得。好吧,結尾處我們再話說從頭:我和興文兄是如何認識的?且說第一屆香港國際舊書展上,我正和董橋先生聊天,晃悠悠過來一人,和董先生點頭寒暄。董先生見我對此人反應平平,大為奇怪,問道:「洪俠,你不認識他嗎?」我說我不認識。「你怎麼能不認識他呢?」董先生呵呵笑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吳興文啊!」
一晃,這都是十年前的一幕了。
推薦序/這一代的「書苦」 胡洪俠(資深愛書人,深圳《晶報》總編輯)
忽然不想再寫三千字以下的文章了。我剛寫了篇〈臺灣的「一九八四」〉,一萬多字;準備寫的那篇〈壽宴〉,少說也得三萬字。年齡見長,文章亦應更長,這算不算「人與書俱老」的翻版?且說某日,我如此盤來算去,正得意間,不小心接一電話,竟是臺灣的興文兄自北京打來的。他說他的《書緣瑣記》就要出版,其中大半首發於《晶報》「深港書評」,「不讓你寫序,感覺、似乎、好像、難免有些不太對頭。」
我迅速想像電話那端興文兄結結巴巴邊說話邊點頭如點數的樣子,隨即...
目錄
推薦序/這一代的「書苦」 胡洪俠
一 閱讀與編輯之間
漫遊者─我的閱讀告白
閱讀的第三種選擇
《開箱整理我的藏書》
在家與書為樂
編輯作為一種志業
圖書編輯的守、破、離
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
胡愈之與裝幀藝術
張靜廬的簽名本
沈公進京工作六十年
《臺灣地名辭典》簽名本
功夫在旅行之外
為學術和著述的人
陳正祥、臺北市與我
永遠的活字
名片、小本和ZINE
從《書的歷史》繪本說起
圖畫書中書
古書鎮與手工裝訂
愛上圖書館
《紙之路》的聯想
二 紙本收藏的世界
聚散無常,不如刻書
藏以致「富」的古書市場
近代藏書家暨出版家
牯嶺街尋寶
初版的「超現代」現象
搜與藏的博弈
「黃跋」的魅力
「黃跋」的可貴在友誼
前朝夢憶‧徽派絕響
悠遊天下─明代文人的樂活方式
永恆和一日─憶黃裳
前塵‧書影‧新錄
《蠹魚篇》vs.《書痴的樂園》
梁思成‧陶湘‧《營造法式》
《環翠堂園景圖》
從一份手稿說起
傅斯年致王世杰函
傅斯年《東北史綱初稿》
《女兵》日譯本開天窗
趙麗蓮編《北平景光》
話劇本《桃花扇》
《翠吟樓遺集》
孫立人與第四軍官訓練班
蔣經國與政工幹部學校
李登輝的菜單
《夢書之城》的異想世界
藝術市場的兩個世界
三 徘徊現代與當代
盛成‧黃扶‧徐悲鴻
他是個學者,其次是詩人
李霽野與《四季隨筆》
昔人已乘黃鶴去
花木叢中─周瘦鵑的後半生
覃子豪與《東京回憶散記》
和風四海已紛吹
女人的另一種唇,會說話
《性史》(1980)
千年綺夢
缺乏愛的時代
試說「那話兒」
一千本的《窗外》
歐巴桑的書之二:《魯冰花》
《籃球情人夢》
送給玲麗的《中國詩選》
張深切的抗日與知日
一本被遺忘的回憶錄
《惘然記》初版本
《淡江記》中的老靈魂
《古春風樓瑣記》贅語
「林志玲現象」背後
回想李麗華
戴國煇與《亞細亞的孤兒》
何妨是書生:張充和與周策縱
隨喜與心得
四 推動書店新型態
推動書店新型態
文字淵源不窮盡
與友人論實體書店
這一代的香港書展
書店不死
誰還需要舊書店?
小確幸的書店時光
新浪漫主義價值觀
另一種書店風景
分眾書店的時代
我是平凡單純的讀者
看到更多的生活風景
《偷書賊》與《愛書狂賊》
沒有人是孤島
跋 書話是一種收藏的趣味──從藏書、著錄到鑑賞
推薦序/這一代的「書苦」 胡洪俠
一 閱讀與編輯之間
漫遊者─我的閱讀告白
閱讀的第三種選擇
《開箱整理我的藏書》
在家與書為樂
編輯作為一種志業
圖書編輯的守、破、離
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
胡愈之與裝幀藝術
張靜廬的簽名本
沈公進京工作六十年
《臺灣地名辭典》簽名本
功夫在旅行之外
為學術和著述的人
陳正祥、臺北市與我
永遠的活字
名片、小本和ZINE
從《書的歷史》繪本說起
圖畫書中書
古書鎮與手工裝訂
愛上圖書館
《紙之路》的聯想
二 紙本收藏的世界
聚散無常,不如刻書
藏以致「富」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