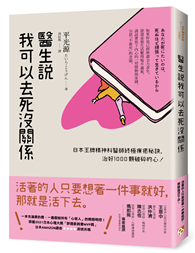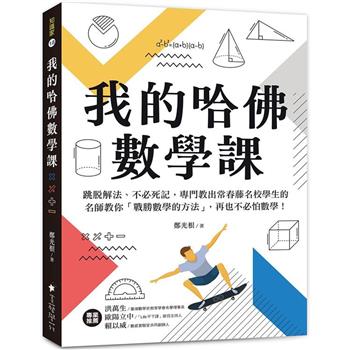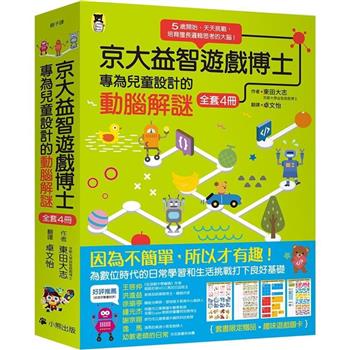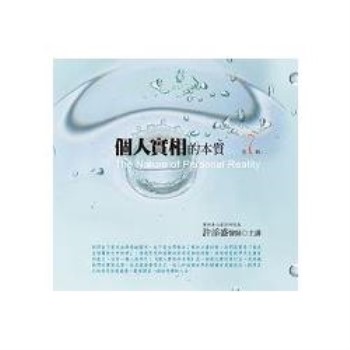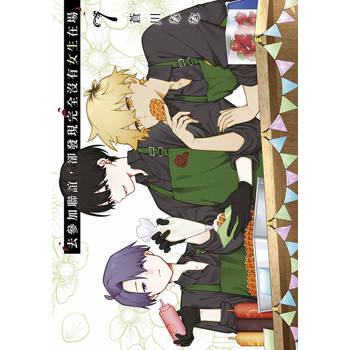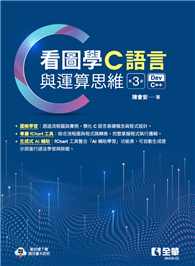第一章、七等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臺灣1960年代,可以說是充滿青春的騷動與壓抑的張力的年代。政治上尚是國共對峙的高壓冷戰階段,經濟上並未進展到以工業與城市集中為主,然而文學界同人雜誌紛出,各種形式實驗將文學藝術的純粹性與神聖性張顯到相當的高度,而洋風洋味也洋溢在臺北的咖啡館與文藝圈。這些特色尤其呈現在以七等生及其參與《文學季刊》出版時期的1960年代中期。七等生之不茍合於人群與文藝圈,與其和《文學季刊》的分合有正相關性,這些關係與其中轉折,在其小說中有不少呈現,也正隱喻著整個時代的特質。因此,其小說不僅呈現出七等生獨特的思維,也透顯了時代的幽微與褶曲面。而其小說中的許多天使形象與友誼敘述,更可以讓我們找到認識這一位充滿哲思的創作者的特殊進路。本書將由1960、70年代時代氛圍切入,拉到七等生的寫作,尤其將七等生文學內外友誼書寫與互動的連帶作為本書重心,並拉到與七等生交誼多年的另一位重要小說家沙究的文學探討,切入天使與橋者形象意義的核心命題。
一、1960年代政治的外張內弛與青春咖啡館
1960年代,對大多數的臺灣年輕人來說,距今超過五十年,早已是比上個世紀末都要久遠很多的「石器時代」。對很多臺灣文化人來說,那也是個壓抑而蒼白的階段,比如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中便以「無根與放逐」來形容戰後第二代作家如陳若曦、歐陽子與王禎和等人。認為這幾位作家「都是土生土長的,光復後接受本地教育到大學的第一代,不幸他們開始也都是『無根與放逐』的」。葉石濤認為他們不但未能接受大陸過去文學的傳統,同時也不了解臺灣三百多年被異族統治被殖民的歷史,且對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更缺乏認識。「他們跟文化傳統雙重的隔絕,使他們同樣陷入『真空狀態』。」
這樣的說法確有其實。在政治上,從戰後1940年代的兩次政治肅清到1950年代的高標反共、戒嚴統治,到1960年代外在仍然充滿壓抑的張力,內在卻因難以觸摸的縹緲現實而飽漲青春的騷動不安,成為一個外張內弛的特殊年代。整個政治的局面是臺灣處於不斷在面臨「即將戰爭」、「準備戰爭」的情境之中,然而島內戰爭卻始終只存於外島或遙遠的遠方。1953年韓戰結束後,臺海局勢日益緊張,1954年起中共陸續發動大小不一的砲戰,使得臺灣處在一種惶惑不安中,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兩岸建立了「單打雙不打」的「默契」,直到1970年砲戰模式結束。而國際上,1950年韓戰爆發,1962年古巴危機,1965年越戰開打,美蘇兩大強權的長期軍事對峙左右了世界的局勢,使全世界都處在鼓譟不安之中。確實,這是一個充滿戰爭的年代,然而,戰爭看似迫近,其實又非常的遙遠,季季在〈擁抱我們的草原〉中透過一個成天無所事事,只會看三流小說和低級電影的小女孩─即小說敘述者們,告訴我們戰爭在當時的虛幻性存在:
那時我們心裡沒有故鄉,我們除了背英文單字和歷史的諸雄紛爭,對霸王們的豔史感興趣外,只會在課堂打瞌睡。……那時我們心裡真的沒有故鄉思念,我們只知道在金門砲戰時,把零用錢一次一次又一次地送出去,而不知道送出去的理由。我們只曉得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有戰爭發生,而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是為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於是,當她不經意在明星咖啡館和另位一樣無所事事的女孩相遇,她說著:
怎麼又碰到妳了呢,真奇怪。
我在她旁邊的座位上坐下來,我沒有回答她什麼話,德弗札克的新世界傳出了戰爭的聲音,一陣又一陣。
是妳點了這張唱片嗎?
她說:是的,不錯,是我。我只能從那裡試著想像戰爭的氣氛,只能從那裡聽到戰爭的聲音。
妳渴望戰爭嗎?
不錯,我渴望。我希望馬上有戰爭,我的愛人已在戰地作了戰爭的食物,我希望有戰爭。
這些敘述刻畫了臺灣島民生活周遭中雖不斷聽聞著戰爭,卻又只能在咖啡館中廢弛地想像著戰爭的虛無茫然。
因為虛無,談論哲學也成了咖啡館的一種流行,如張系國在《昨日之怒》中描繪的一群大學生「他們在馬路上逛了一陣,終於又踱進明星咖啡屋。明星裡擠滿和他們類似的青年……大家高談著世界的荒謬、人性的自由和自身的失落。胡偉康扯著一頭厚厚的黑髮,大聲狂呼。『我們有什麼理由快樂?我們被投入了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失落了!』」
劉大任即曾透過《浮游群落》一書,呈現一群知識青年想要突破現狀做點什麼卻又無計可施的窘況。他們「像包裹著一層無形無色的薄膜,像一頭望得見外面卻看不透欺騙的蒼蠅,開始鬱悶,開始不安,開始盲目的衝撞,開始無意義的掙扎,而終於無可奈何。」於是只好成日在昏暗的咖啡館裡,隨著古典音樂搖頭晃腦發洩苦悶。
政治如此,經濟上,臺灣直到1970年代之前,仍以農業經濟為主,並未進展到工商經濟的階段;文化上,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下,臺灣社會普遍封閉貧乏,仍以封建倫理道德為主。然而,就在這個社會封閉貧乏、政治獨裁壓抑的年代,學者邱貴芬告訴我們,那也是一個充滿異質聲音與影像的豐富年代,當時不僅有日本、美國的舶來影片,也有臺語、黃梅調等各式電影,南腔北調的聲音與影像充斥在臺灣的空間中。從文學角度來看,當時有一群需要發洩青春騷動的文學青年,生產出一些如今看來無比重要的刊物,包括《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往往只因幾位創作同好號召,一個文學刊物便組成了,於是一期接一期,一篇接一篇、一首接一首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甚至散文、戲劇、論述……,就在這種求新求變、勇於開拓探索的氛圍中完成。
本章將以臺灣1960年代文壇氛圍為主要重心,說明其中明星、田園、野人、文藝沙龍等咖啡館及公共空間所具有的生產性意義。尤其將聚焦在當時與七等生及與其較有互動的幾個重要文藝人物,在這些空間裡的活動情形,以帶入整個時代氛圍。七等生與後來文學創作最為相關的《文學季刊》中,如姚一葦、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雷驤、沙究等人,兼及一些成為傳奇般的情愛故事,與文壇創作之間的關係,也將以此作為後面章節敘述七等生及小說中的友誼的引言。
二、明星咖啡館:台北文學地標
臺北武昌街一段七號,就在城隍廟對面,1949年,一個十八歲的建中畢業生與六個年紀比他大三輪的俄羅斯人,開啟了明星一甲子的璀璨歲月。
在這群具傳奇身分的明星創辦人中,唯一的臺灣人、也是明星靈魂人物的老闆簡錦錐的說法,明星的整個故事要從更早說起。1917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一位出身貴族的俄國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跟著軍隊奮戰不敵之後,一路輾轉流亡到上海。此時他的同鄉布爾林於上海霞飛路七號開設「明星咖啡館」,後來艾斯尼跟隨國民政府到了臺灣,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當時年僅十八歲的簡錦錐先生,結為忘年之交,且跟幾個俄國同鄉,包括布爾林在內,於1949年在臺北武昌街一段七號合作經營「明星西點麵包廠」,並於麵包店二樓開設「明星咖啡館」。「明星」名稱原是從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來,「Astoria」是俄語「宇宙」之意,此名意味著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麗的那顆星」。
早期的明星咖啡館只靠著販賣俄羅斯風味簡餐與咖啡,後來配合明星麵包店的俄式麵包與西點,以異國風味吸引著臺北人。每天下午四點、五點,不少外國使館與達官貴人的黑頭車紛紛來到武昌街,等著在第一時間購買剛出爐的麵包回去,場面蔚為奇觀。加上來自俄國的蔣經國夫人蔣方良當年時常造訪明星品嘗家鄉味,她每回必嘗的是「俄羅斯軟糖」,即當年俄國皇室御用的點心。這些故事都讓明星在臺北人的心中增添不少神祕的傳奇色彩。
明星一開始吸引的是中國來的高官、商人,絡繹不絕,還有郎靜山、陳景容、楊三郎、顏水龍等藝術家,都常來此聚會。到了1959年,詩人周夢蝶在咖啡館樓下騎樓擺起小小的書攤,引來一些愛好文藝者聚集。往後二十一年,直到它曾歇業的1989年12月11日止,這裡成就為一則動人的臺北文學傳奇。時光雖然匆匆,明星騎樓下削瘦的黑衣詩人周夢蝶一度餓昏倒地,經簡先生伸出善意援手供熱食,而傲骨詩人卻堅持自己買單。只能喝得起一杯咖啡的往事,卻讓文壇至今津津樂道,引為美妙無比的文壇傳奇故事。
考據起來,尉天驄曾經指出明星與文壇的結盟其實另有比周夢蝶更早的起源。原來是戰後有幾位從大陸來到臺灣的文人,如臺靜農、黎烈文及孟十還等,其中臺靜農是魯迅的大弟子,黎烈文及孟十還也是魯迅的抬棺弟子。黎烈文當時任教臺大外文系,翻譯過很多法國小說名著。孟十還曾經留學蘇聯十年,發表過很多俄國翻譯文學,也曾與魯迅合作翻譯《果戈理選集》,因此來到臺灣之後成為政治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的系主任。那時幾個文人聽說西門町開了一家俄羅斯咖啡廳,就邀孟十還一同前去開開洋葷,順便試試他的俄語是不是真有那麼厲害?孟十還果真秀了一口流利的俄語,從點菜交談與俄國人溝通無礙,從此這群文壇人士常到明星聚集,若真要說明星的文學歲月,這些人來得比周夢蝶更早。
以上文字出自明星創辦人簡錦錐的《明星咖啡館》回憶錄,簡錦錐表示,確實在1950年代初期,明星出入的不只俄國人還有一些文人打扮、會說俄國話的大陸人,那時明星就與文人結緣了,後來又因周夢蝶帶來更多作家與藝文人士。他更提到,當時有些咖啡廳會與「黃色」、「晦暗」畫上等號,有時警察拿著手電筒進去照著客人的臉查緝是否有不檢點的情事,但明星卻走出一條自己的藝文道路。
白先勇曾回憶說:「臺灣六十年代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館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地萌芽、開花。」據說白先勇最愛二樓樓梯口靠近櫃檯的座位,面對一屋子眾生群像。他的小說代表作《臺北人》筆下所描述的一個個鮮活臉譜,或許也曾乞靈於穿梭過明星咖啡館的身影。而許多作家更把明星當作第二個家,例如初為人父的黃春明,還曾在咖啡館的桌上為寶貝兒子換尿布呢。整個裝潢帶有古樸歐風風采的明星咖啡館,彷彿是近代臺灣的文學沙龍。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天使與橋者: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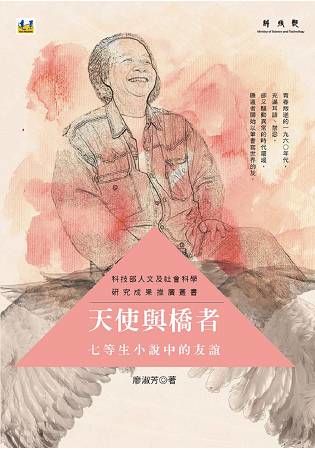 |
天使與橋者: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 作者:廖淑芳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6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華文文學研究 |
$ 252 |
華文文學研究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使與橋者: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
充滿熱情的經典作家七等生
如何閱讀,才能認識他筆下的「天使」與「橋者」?
這本書便是遊走書中天上人間的地圖
科技部為推廣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鼓勵學者專家與出版事業機構合作,以科技部補助之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計畫重要研究成果為主要素材,創作並出版普及性叢書。為了引領讀者進入作家的心靈世界一探究竟,本叢書以深入淺出的評析來閱讀經典,將臺灣文學論述推介給大眾,並把當代文學的發展軸線及向度緩緩舒展於眼前,留下時代的見證。藉由本套叢書的出版,與社會大眾分享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本書作者廖淑芳希望從七等生小說作品中具豐富意涵的「天使」、「橋者」所涉及的形象書寫意涵,及其變異性為探討重心,借用宗教敘事學裡論虛構敘事中的「結尾的意義」,往往涉及啟示錄意涵;及以德希達與布朗蕭等論友誼及禮物的交換經濟學層面為進路,探討其文中「天使」「橋者」所具有的宗教性與人間性的雙重意涵。同時,由於其中往往涉及天使在人間的多重變異面貌涵,將搭配友誼學與敘事學,以深入解讀其形式與內涵之間的相連關係,以進一步深究七等生作品中相當多片斷破碎,看似多餘、不能融入敘事結構中的形式成分的文本,其中可能具有的認識論意義。
作者簡介:
廖淑芳
清華大學博士,任教於成功大學。專長領域戰後台灣小說、現代主義文學、當代文學理論。著有學術專書《鬼魅、文學敘事與在地性─戰後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七等生文學現象為核心》、《七等生文體研究》。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七等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臺灣1960年代,可以說是充滿青春的騷動與壓抑的張力的年代。政治上尚是國共對峙的高壓冷戰階段,經濟上並未進展到以工業與城市集中為主,然而文學界同人雜誌紛出,各種形式實驗將文學藝術的純粹性與神聖性張顯到相當的高度,而洋風洋味也洋溢在臺北的咖啡館與文藝圈。這些特色尤其呈現在以七等生及其參與《文學季刊》出版時期的1960年代中期。七等生之不茍合於人群與文藝圈,與其和《文學季刊》的分合有正相關性,這些關係與其中轉折,在其小說中有不少呈現,也正隱喻著整個時代的特質。因此,其小說不僅...
臺灣1960年代,可以說是充滿青春的騷動與壓抑的張力的年代。政治上尚是國共對峙的高壓冷戰階段,經濟上並未進展到以工業與城市集中為主,然而文學界同人雜誌紛出,各種形式實驗將文學藝術的純粹性與神聖性張顯到相當的高度,而洋風洋味也洋溢在臺北的咖啡館與文藝圈。這些特色尤其呈現在以七等生及其參與《文學季刊》出版時期的1960年代中期。七等生之不茍合於人群與文藝圈,與其和《文學季刊》的分合有正相關性,這些關係與其中轉折,在其小說中有不少呈現,也正隱喻著整個時代的特質。因此,其小說不僅...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臺灣在世界地理環境與人文社會發展上,本是亟待發掘之研究主題,近年來,由於本土化研究導向之趨勢,促使臺灣研究蔚為風氣,加以政府之重視、學者的投入,漸漸使「臺灣學」成為學術研究之重要課題,大專校院臺灣研究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鄉土文史工作室、民間史料採集、鄉土教材編寫等的蓬勃發展,甚至成為國際新興之焦點議題。
本書由應鳳凰教授所書,聚焦於文藝雜誌,並以之探討當時文學生態。方法是將文藝雜誌依其性質傾向區分成三大類型,企圖透過不同傾向內容的文學雜誌與聚集的作家群落,描繪六○年代臺灣文學場域的概略...
本書由應鳳凰教授所書,聚焦於文藝雜誌,並以之探討當時文學生態。方法是將文藝雜誌依其性質傾向區分成三大類型,企圖透過不同傾向內容的文學雜誌與聚集的作家群落,描繪六○年代臺灣文學場域的概略...
»看全部
TOP
目錄
作者序│七等生的書寫意涵
第一章 七等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一、1960年代政治的外張內弛與青春咖啡館
二、明星咖啡館:臺北文學地標
三、明星咖啡館與《文學季刊》等文人之互動
四、其它文學咖啡館
五、七等生曾經供職的「文藝沙龍」
第二章 魔幻城市與七等生小說中的隱遁者形象
一、七等生的創作、入城與《文學季刊》
二、充滿爭議的城市寓言:〈我愛黑眼珠〉
三、「洪水」災難:城市的「震驚」經驗
四、在回到小鎮的橋上:附魔的吶喊者「亞茲別」
第三章 七等生文學及其小說中...
第一章 七等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一、1960年代政治的外張內弛與青春咖啡館
二、明星咖啡館:臺北文學地標
三、明星咖啡館與《文學季刊》等文人之互動
四、其它文學咖啡館
五、七等生曾經供職的「文藝沙龍」
第二章 魔幻城市與七等生小說中的隱遁者形象
一、七等生的創作、入城與《文學季刊》
二、充滿爭議的城市寓言:〈我愛黑眼珠〉
三、「洪水」災難:城市的「震驚」經驗
四、在回到小鎮的橋上:附魔的吶喊者「亞茲別」
第三章 七等生文學及其小說中...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廖淑芳
- 出版社: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2-01 ISBN/ISSN:978957391013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14.8*21
- 類別: 中文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