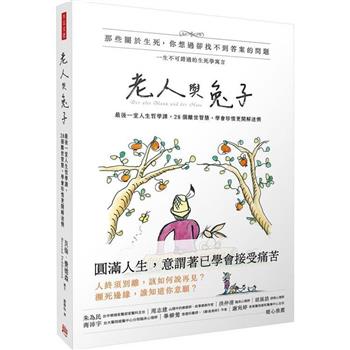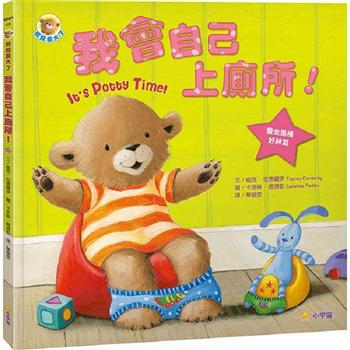認識鍾肇政一生懸命的文學
用一生寫下文化的起點
見證民族史詩的執拗又純粹,溫暖且謙卑
用一生寫下文化的起點
見證民族史詩的執拗又純粹,溫暖且謙卑
科技部為推廣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鼓勵學者專家與出版事業機構合作,以科技部補助之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計畫重要研究成果為主要素材,創作並出版普及性叢書。為了引領讀者進入作家的心靈世界一探究竟,本叢書以深入淺出的評析來閱讀經典,將臺灣文學論述推介給大眾,並把當代文學的發展軸線及向度緩緩舒展於眼前,留下時代的見證。藉由本套叢書的出版,與社會大眾分享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本書作者錢鴻鈞因為一場文學獎頒獎典禮與研討會,開啟了鍾肇政文學研究的序幕。他根據鍾肇政與文友的書簡及作品,查究出鍾肇政世代的臺獨認同意識、日本精神、心靈故鄉及寫作的背景。在白色恐怖氣氛濃厚的一九六○年代,鍾肇政透過文壇社與幼獅文藝集中出版臺灣本土作家作品兩大叢書,掩護偷渡的用心,存在編者言的字裡行間。錢鴻鈞將研究鍾肇政的論文彙整,出版此書《大河悠悠──漫談鍾肇政的大河小說》,以見證鍾肇政的文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