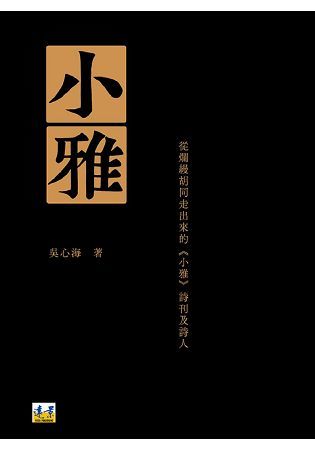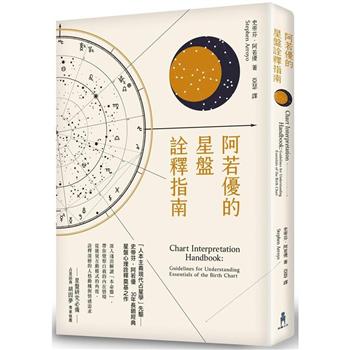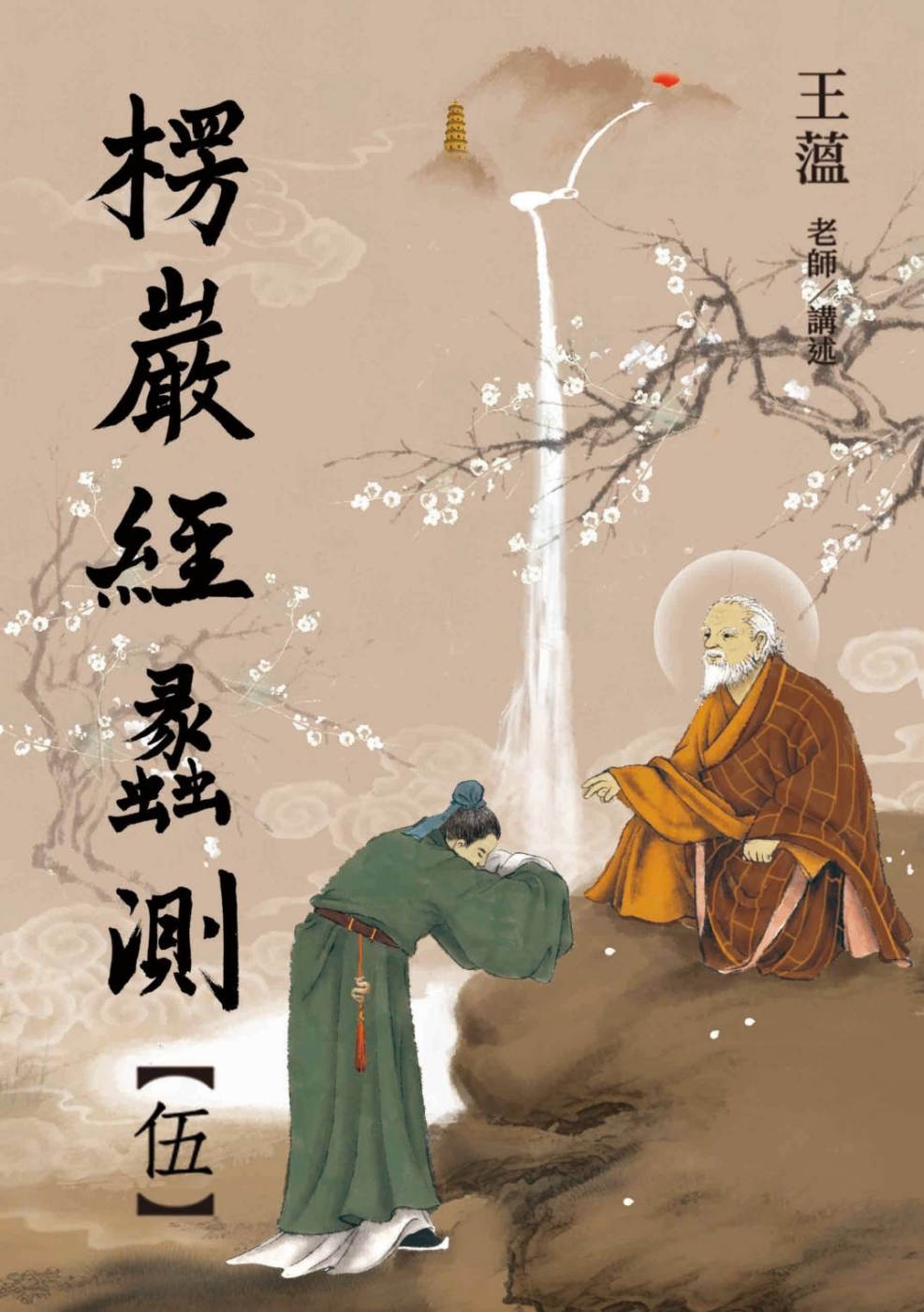序
《小雅》復刻本序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是從白話小說和白話詩揭開序幕的,白話小說以魯迅《狂人日記》的發表為標誌,白話詩也即新詩則以胡適《嘗試集》的出版為標誌。一九二二年一月,署「中國新詩社」編輯的《詩》月刊創刊,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詩雜誌,實由葉聖陶、劉延陵主編,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然而,整個一九二○年代,專門的新詩雜誌寥寥無幾,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詩鐫》當然是專門的新詩刊物,但是《詩鐫》是副刊的專版而並非雜誌。
進入一九三○年代以後,新詩雜誌開始爭奇鬥豔,徐志摩主編的《詩刊》先聲奪人,朱維基主編的《詩篇》和左翼的中國詩歌會主編的《新詩歌》隨後跟上,接著還有土星筆會的《詩帆》和戴望舒主編的《現代詩風》,後者創刊即終刊。 直到三○年代中期,新詩雜誌才迎來令人欣喜的繁榮期,中國新詩壇形成了戴望舒等主編的《新詩》、路易士與韓北屏主編的《詩志》和吳奔星與李章伯主編的《小雅》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這三種新詩雜誌中,《小雅》問世最早,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于北平,次年三月出至第五、六期合刊後終刊。四個月後,《新詩》在上海誕生,堅持出版了十期。又過了一個月,《詩志》也在蘇州呱呱墜地,但僅出三期就無以為繼。 《新詩》名家薈萃,壽命最長,自然影響也最大,研究中國新詩史的大都會提到它。《詩志》因路易士去臺灣後不斷憶及,也不能說毫無聲響。唯獨《小雅》,儘管詩人陣容強大,因流傳甚少, 反而最不為人注意。而且,儘管從文學期刊史角度視之,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兩年對中國新詩進程頗為重要,文學史家卻一直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再加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裡,對非主流的新詩創作和刊物幾乎棄之不理。由於這些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小雅》差不多湮沒了,不要說一般的新詩愛好者,就是專業的新詩研究者,也幾乎都不知道新詩史上有這麼一個《小雅》詩刊的存在。
從這個意義講,復刻全套《小雅》實在是太有必要了。《小雅》的重見天日,將會為我們重新審視新詩史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綜觀六期五冊《小雅》,至少有以下數點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這是編者十分用心的一個專門的新詩雜誌,雖小卻頗具特色。它以發表成名或無名新詩作者的原創詩作為主,輔以戴望舒、李長之、柳無忌諸家的譯詩,也有關於新詩的理論探討,包括對新詩的內容和本質、「明白話」與「真感情」的關係,以及新詩可否有「白話化的文言句子」等問題展開爭鳴,在當時的新詩刊物中自樹一幟。
其次,編者在創刊號《社中人語》中明確宣告「反對」當時「詩壇上多派相互攻訐」,強調「我們的編輯方針,對於任何一派的作品,都一律看待,予以榮發的機會。」顯然,《小雅》從一開始就顯示一種開放的姿態,只重「質的精選」而不問其他。儘管如此,刊物在成長過程中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或者換言之,成為了編者後來自己所揭櫫的「作風為縹緲」的「法國詩風派」 的發表園地。
何謂「作風縹緲」?可以見仁見智。發表在《小雅》上的長短新詩,儘管也有《北洋軍閥》(斵冰作)這樣觸及時政的作品,但絕大部分是寫平民的日常生活,寫遊子的喜怒哀樂,古城洋場,晨曦月色,春殤冬暮,歎時光之流逝,抒失戀之傷感,這是《小雅》眾多詩作的基調,像吳奔星的組詩《秋天》,就有〈秋午〉、〈秋山〉、〈秋葉〉、〈秋雨〉四首,觀察之細緻,詩句之清新,可謂另有一功。這是不同於所謂激進的新詩主流的另一種新詩,以前往往被人視為小資情調、無病呻吟而詬病,現在看來仍不失為一群年輕的對未來生活充滿憧憬的新詩愛好者發自內心真情實感的流露。更何況這些詩作大部分是自由詩,大都注重古典資源的汲取,注重詩句的錘煉和獨特意境的營造。所以,《小雅》上的詩是新詩寫作的又一種有益的嘗試,理應得到積極的評價。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小雅》的作者,除了當時已經成名的新詩人,如李金髮、施蟄存、林庚、路易士等,更多的是詩壇新秀。有的在《小雅》上亮相後,逐漸走向成熟,已在新詩史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記,如侯汝華、林英強、吳興華、陳雨門、甘運衡等。還有一些,或英年早逝,如沈聖時、史衛斯;或後來很少甚至不再寫詩,如錫金、陳殘雲、韓北屏等;或因多種原因淡出文壇,如李章伯、林丁、吳士星(吳仕醒)、常白等,他們的名字,有些我們熟悉,更多的是感到陌生,但有趣的是,他們共同組成了《小雅》作者群。這個新詩創作群體的功過得失,正待文學史家重新考量。
後來者研究前輩作家的文學成就,採取的方法通常是閱讀分析他們的作品,從單行本到文集到全集,還蒐集他們的集外文,以求更完整更全面地進行評估。也有更進一步從研究對象的文學活動切入,包括探尋他們的編輯生涯和文壇交遊,等等。吳心海兄從研究乃父吳奔星先生的文學道路起步,擴大到對奔星先生主編的《小雅》的關注,對《小雅》作者群的追蹤,正是循著這一路徑不斷深入的。《小雅》的五十多位作者中, 心海兄考證了三十餘位詩人或詩作者的生平、創作歷程及其與《小雅》的關係,已超過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幾乎每期都有作品發表的《小雅》主要作者,都被他一網打盡了。這是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艱鉅而又漫長的發掘文墓之旅,心海兄這些年來堅定不移地努力著,查明了侯汝華、沈聖時、林丁的下落,考定了史密斯即後來的戲劇家方瀅,糾正了關於李白鳳的種種誤傳,還厘清了路易士和路曼士、吳士星和吳奔星、蔣錫金和蔣有林三對兄弟的《小雅》詩緣……。這一切,他都做得可圈可點,令人信服。新詩史上的這一段以前鮮有人關注的空白,由於有了心海兄這位有心人,終於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填補。
今年是《小雅》終刊八十週年,更是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年,這是兩個很值得紀念的時間節點。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為《小雅》在今年重印鼓掌,為吳心海兄對《小雅》作者群卓有成效的考證工作叫好,也期待中國新詩研究界能夠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揭示中國新詩史的多種面向。
陳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