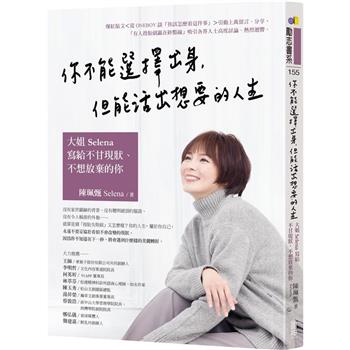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唐棉》是廖淑華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輯一以小鎮人文為背景,小鎮人物為藍本,從作者自小成長的雲林故鄉人物故事發想,細細書寫過往與現在的故事;輯二則以作者自1997年上台北至今,在職場生涯中周遭人物的故事漫擴,描寫在大台北營生的異鄉人日常卻深刻的生活景致。
儘管書寫日常,鄉鎮人物的樸實形象、敦厚的情感不斷從字裡行間表露而出,讓我們一再得見小鎮獨特的味道,人物的投足扭身、街巷屋舍、生活起居……等等,好似為我們追回那段令人眷戀的年代,誠如作家方梓所說:「作者以樸實的文字,沉靜的語調,從小鎮出發再現小鎮歷史,也開創小鎮的新視野。」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唐棉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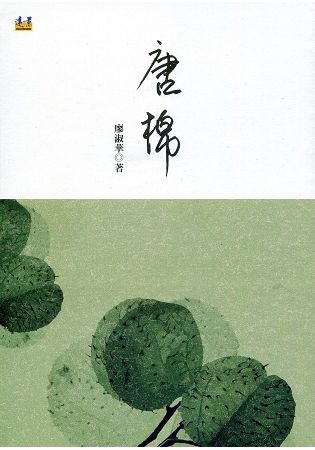 |
唐棉 作者:廖淑華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1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文書 |
$ 221 |
現代小說 |
$ 22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46 |
小說 |
$ 252 |
小說 |
$ 252 |
現代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唐棉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廖淑華
雲林縣斗南人。現任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秘書長,並擔任寫作班老師。作品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優等獎、懷恩文學獎社會組首獎、宗教文學獎小說二獎、新北市文學獎散文組二獎、雲林縣文學創作獎短篇小說佳作。著有散文集《鷺鷥飛入山》。小說集《唐棉》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創作類補助。
廖淑華
雲林縣斗南人。現任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秘書長,並擔任寫作班老師。作品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優等獎、懷恩文學獎社會組首獎、宗教文學獎小說二獎、新北市文學獎散文組二獎、雲林縣文學創作獎短篇小說佳作。著有散文集《鷺鷥飛入山》。小說集《唐棉》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創作類補助。
序
推薦序
平凡的魅力讀《唐棉》/方梓
談都市文學,對位就是鄉村/鄉土文學,就像黑白一樣,十分兩極沒有中間地帶。其實在都市和鄉土文學的夾縫一直有「小鎮文學」的存在,但早期多數被歸屬在鄉村。小鎮,這個介於都市與鄉村的地域,既兼有都市的某些便利機能,又有鄉村的樸實熱情,在書寫情調上也比較多元。這一、二十年來小鎮文學萌發,最具代表的小說便是陳雨航的《小鎮生活指南》,詳實描述小鎮的地誌、文化、歷史,再現小鎮風華。
小說是從日常的經緯佈局出發,去展現平凡/普通性的魅力。廖淑華《唐棉》輯一以小鎮書寫,輯二是從小鎮出發至北部/他鄉謀生的故事,但繫牽著小鎮生活。她由小鎮的一家一戶,逐漸拉出一條街,一方小鎮的樣貌。年代由一九六○年代開始,細寫小鎮的人物、景象。小鎮裡每個家庭都有一、二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二個比較「活潑」的人,不管是「雞事一樁」,還是「西藥店的兩個老婆」,小鎮就靠這些活潑生趣了。
文學的第二種力量就是它的再現力,一切都應有它本身的味道。在本書第一篇〈那一年,國雄的夏天〉廖淑華開宗明義定調起小鎮地理位置、環境,「小鎮從火車站前的中山路切成兩半,一半稱新市,一半叫做舊市,說話時大家習慣加個『ㄚ』的尾音。舊市ㄚ這一半就屬福德街土地公廟周圍最聚市、最熱鬧,正對土地公廟的一排房舍後方有條大圳溝,圳水來自鎮外的大溪……」。《唐棉》輯一的幾篇小說都展現了小鎮獨特的味道,人物的投足扭身、街巷屋舍、生活起居,廖淑華寫來彷彿活脫脫呈在讀者眼前,如影像播映,琇雲的溫婉、阿連的男人女相、阿英的乾瘦、小街的樣貌、餅舖、西裝店的陳設…一目了然,宛如回到一九六○年代。
細節藏著功夫,小地方看格局;廖淑華擅長描述細節,「小鎮清早的街市,三三兩兩行人,女人家小心托著月桃葉上的豆腐,稍急步伐扭動的身軀如手上剛出鍋的豆腐一顫一抖地;老人拎著藺草綁著的油條,走過路口的土地公廟時仍不忘虔誠合十拜了拜。」大半的作品,廖淑華都細述景與人的互動,以及人物特寫去彰顯情節的演繹,以小托大,厚實了小說的豐富、可讀性。
《唐棉》輯一、輯二大半以女性做為主要敘述,廖淑華剔盡了女人的心思,〈阿英孵蛋〉透徹了偏房處境、生與不生的兩難;〈回家〉入骨了「她」的寂寞及悲思、反諷女人的「回家」;〈唐棉〉中女人的靭性與無奈……
寫作從廢墟出發,從無到有創造了新境界;廖淑華以樸實的文字,沉靜的語調,從小鎮出發再現小鎮歷史,也開創小鎮的新視野。
平凡的魅力讀《唐棉》/方梓
談都市文學,對位就是鄉村/鄉土文學,就像黑白一樣,十分兩極沒有中間地帶。其實在都市和鄉土文學的夾縫一直有「小鎮文學」的存在,但早期多數被歸屬在鄉村。小鎮,這個介於都市與鄉村的地域,既兼有都市的某些便利機能,又有鄉村的樸實熱情,在書寫情調上也比較多元。這一、二十年來小鎮文學萌發,最具代表的小說便是陳雨航的《小鎮生活指南》,詳實描述小鎮的地誌、文化、歷史,再現小鎮風華。
小說是從日常的經緯佈局出發,去展現平凡/普通性的魅力。廖淑華《唐棉》輯一以小鎮書寫,輯二是從小鎮出發至北部/他鄉謀生的故事,但繫牽著小鎮生活。她由小鎮的一家一戶,逐漸拉出一條街,一方小鎮的樣貌。年代由一九六○年代開始,細寫小鎮的人物、景象。小鎮裡每個家庭都有一、二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二個比較「活潑」的人,不管是「雞事一樁」,還是「西藥店的兩個老婆」,小鎮就靠這些活潑生趣了。
文學的第二種力量就是它的再現力,一切都應有它本身的味道。在本書第一篇〈那一年,國雄的夏天〉廖淑華開宗明義定調起小鎮地理位置、環境,「小鎮從火車站前的中山路切成兩半,一半稱新市,一半叫做舊市,說話時大家習慣加個『ㄚ』的尾音。舊市ㄚ這一半就屬福德街土地公廟周圍最聚市、最熱鬧,正對土地公廟的一排房舍後方有條大圳溝,圳水來自鎮外的大溪……」。《唐棉》輯一的幾篇小說都展現了小鎮獨特的味道,人物的投足扭身、街巷屋舍、生活起居,廖淑華寫來彷彿活脫脫呈在讀者眼前,如影像播映,琇雲的溫婉、阿連的男人女相、阿英的乾瘦、小街的樣貌、餅舖、西裝店的陳設…一目了然,宛如回到一九六○年代。
細節藏著功夫,小地方看格局;廖淑華擅長描述細節,「小鎮清早的街市,三三兩兩行人,女人家小心托著月桃葉上的豆腐,稍急步伐扭動的身軀如手上剛出鍋的豆腐一顫一抖地;老人拎著藺草綁著的油條,走過路口的土地公廟時仍不忘虔誠合十拜了拜。」大半的作品,廖淑華都細述景與人的互動,以及人物特寫去彰顯情節的演繹,以小托大,厚實了小說的豐富、可讀性。
《唐棉》輯一、輯二大半以女性做為主要敘述,廖淑華剔盡了女人的心思,〈阿英孵蛋〉透徹了偏房處境、生與不生的兩難;〈回家〉入骨了「她」的寂寞及悲思、反諷女人的「回家」;〈唐棉〉中女人的靭性與無奈……
寫作從廢墟出發,從無到有創造了新境界;廖淑華以樸實的文字,沉靜的語調,從小鎮出發再現小鎮歷史,也開創小鎮的新視野。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