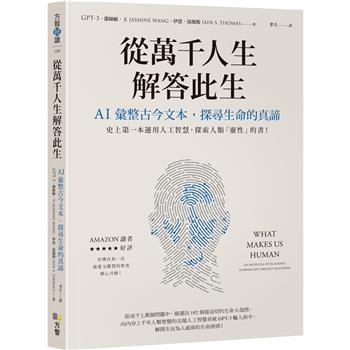繡 花 鞋
少小離鄉,細數歲月,與母親常相左右不過二十餘載,算是情緣不夠深吧。
長期未能伺親,母親年邁時期,步履蹣跚拄著拐杖影子牢牢烙印心底,為表內心不安,經常利用午休空檔逛城中市場,市場裡面應有盡有,尤其是老年人衣物用品,舉凡吃的、擦的、暖的、涼的、洗的、曬的林林總總,經常逛到流連忘返,寒天該為雙親購置羊毛內衣褲,酷暑該購置麻製背心,有些時候連洗衣精都想帶回浯島,如果您也度過那個年代;物資缺乏交通不便,回娘家真是艱難大事,不是乘登陸艇就是搭軍機,可以想像為人子女的我,多麼想用物資掩飾自己的不孝。
就在武昌街有兩家賣繡花鞋,一家在武昌街上,一家在巷弄裡,逛著逛著就想為母親買雙繡花鞋,總是特意選購繡著鮮艷花朵或艷紅色彩的緞面鞋,回到家裡,會哄著母親,沒有人會看您的腳,來!穿穿看;當然母親為讓我開心也會歡歡喜喜穿上。棉襖也是,我喜歡母親穿有顏色的衣服,如果穿件棗紅棉襖,那就更佳了,往往為了母親穿上新衣走出家門,內心竊喜著,鄰人會看到母親穿有顏色的衣呀鞋呀,順便挑釁一下上一代女性不是灰色布衫就是藍色布衫的無色彩社會。可是母親靦腆,純樸農村怕過於招搖,
經常應付我卯個景,而後高掛衣櫥裡,我仍然固執要買花俏的。
父親比較不挑剔,給啥穿啥,我幫他買的功夫鞋他最愛,偶爾也要來雙皮鞋配上長大衣,應女兒要求摩登一下,可多年下來,皮鞋依然嶄新。
皮包裡長年放著父親、母親鞋長的尼龍紅繩,因而任何時候想為他們挑選一雙鞋子,丈量紅繩長度買回必定合腳,當女兒的似乎只有這一件事可做。
從西區到東區商場上拚戰,事隔十多年竟對城中市場有些許模糊。去年上半年公司遷址由東區再到西區,整理衣物,翻到兩條紅色尼龍繩,凝視良久,父母往生多年了,無緣再為他們購買衣物,這兩條尼龍紅繩藏了這麼久,多麼想再為母親挑一雙繡花鞋,最好鞋面是牡丹花鑲著珠子,亮晶晶的那種,母親穿在腳上一定美極了。
猶記每一年端午節過後回家,會看到母親把所有棉鞋、布鞋、繡花鞋,一雙一雙羅列在天井曬太陽,在她腦海裡衣物通通是小女兒買的,我不敢居功厥偉,因為後期姐姐們移居台灣,也常常分頭採買,因而衣物算是豐盛,心裡明白盡孝不僅是物質而已,能陪著說話、陪著散步、陪著吃飯、陪著燒香拜佛;幫著換裝棉被、幫著收納衣物、幫著曬曬鞋子、幫著搥搥背……
啊!似乎什麼也沒做;身為父母親的么女兒,得寵最多,孝道盡得這麼少,悵然。即便到今天年紀一大把,經常想起父女、母女緣分應是深的,可怎麼相處時日如此短暫?當年稍不順心,撒個嬌總會稱心如意;如今,父母不在,向誰撒嬌?今兒,走過繡花鞋店,一位前中年女子,東挑西撿端視繡花鞋兒,佇立她背後思索半晌,很想與她說些話,或問她母親如何?猶疑著,終究是陌路,不好搭訕,寥落離開。心想女子必在為她母親挑一雙合腳的繡花鞋。
年關在即,若能為母親挑一雙繡花鞋,親手為母親穿上,陪著母親在門口走一段,再走遠一點,到城裡觀音亭燒香拜拜,母女同行,多美好啊。記憶裡唯一一次與母親攜手逛街,應該是就讀高一的時候,母親年近花甲,女兒初長成,帶著女兒到后浦街上買了一件桃紅領子的黑外套,母親從內衣口袋掏出皺皺的幾張紙鈔,無疑的存了些時日,年少的我卻大剌剌為了一件外套把它給花了,時光忽悠,若是今日必定告訴母親一起逛個街就好,外套不必買。領悟到這道理卻是成年後的事了。
初次旅台,渾渾噩噩約莫半年,回家是唯一想做的事。暑假一到即刻搭了柴慢火車八小時趕赴高雄十三號碼頭,等了數日艦艇,欲搭乘返回母島,又是風浪又是船期,一再延宕,折騰了些時日,船終於啟航,一抵料羅灣,三步做兩步是如何到了慈湖畔的湖下村一三二號已不復記憶,只記得當下母親不在家,撲了空的心,跌到谷底,得知母親到后浦觀音亭拜拜,整個人急著往慈湖路跑。半路,就在半路碰著前方緩緩行來的母親,母女倆抱著頭痛哭,半年不見我親愛的阿母就在這一刻淚流滿面,到底離開母島為哪樁?直叫無語問上蒼,時至今日仍未清明。
心不甘情不願的又必須離開雙親,兩老百般不捨,母親從床舖底下取出兩瓶年代久遠的高粱酒,瓶身沾滿灰塵,商標些許模糊,父親用抹布拭擦,再用尼龍紅繩把兩個瓶口呈八字形綁緊,嘴裡交代:「孩子,到了台灣人生地不熟,緊要關頭,可以當伴手禮,讓人家事情好做些。」眼眶含淚,這樣每回兩瓶的酒,累積十數瓶,無論遇到什麼困難,萬不得已我不拿出來,對我而言,酒豈止是酒而已。
只有一次例外,大哥生病躺在台大醫院,弟弟與我,兩人都未滿二十歲,也不知哪來的勇氣與世故,拎著兩瓶有年份的大麴到台大醫院找主治醫生,懇請他為大哥盡力。許是誠意,許是純樸的兩張臉,許是酒精發酵,該醫師對大哥及家屬親切和藹,雖未挽救到大哥,大哥臨終說了對家人沒有任何遺憾,大夥都盡力了。
因著繡花鞋,想起母親,想起高粱,想起大哥,想起家鄉點點滴滴,記憶長河深邃、無聲,似醇厚高粱流過喉嚨,一溜煙全都陳年往事了。
眼下人來人往,選購繡花鞋的女子已然離去,望著鞋攤上每一雙鞋都映著母親的臉。
海邊的風
所有回憶不管是悲是喜,如意或不如意,經過時光洗禮,總會令人有一股淡淡的哀愁。
時光長河是一江春水,父母親老了走了,手足成家立業,不再同一屋簷下嬉戲,隔壁童年玩伴失聯,種種原因都是深入靈魂的記憶。
風沒有老,微風陣風強風暴風仍日日夜夜輪番吹著,春天拂面吹過,夏日經常烈日當空,風往往停在樹梢不動,待到了傍晚時分或有些微的騷動,或多或少搧出一些風兒,秋日的風帶著秋意掃著落葉,冬日北風颯颯,所有的風均從空隙強烈吹過。迄今,唯有大自然的奧妙亙古不變。
家裡土灶有個煙囪,燒著柴火的時候,隨著風向炊煙裊裊,是家的座標,不管玩耍到那,抬頭看著一縷青煙,心裡會有一陣陣暖意,阿母必定在燒著柴火煮飯。
阿爸是忠厚老實的莊稼人,阿嬤不讓他下南洋,他就老老實實守著這家園、妻小連帶弟妹一併照顧。和村落裡男女老少一樣看顧著幾分薄田以及淺海沿岸魚貨為生。他的人生像老鼠爬竹竿,一節一節往上爬,這是阿嬤找算命先生所論出阿爸的命,字面上看也不算壞,節節上升的嘛。
尋常百姓,過著尋常生活。阿公早逝,阿嬤是家裡的權威。阿爸隨著時序看顧全家三餐,很少有機會閒適恬淡的看雲看海,通常是觀看天象或雨或晴,對農作物是否有助益為要務。也沒看到父親有何種娛樂,只有夏日晚飯過後帶著孩子們在櫸頭屋頂吹吹銅管,講講北斗星在那之類,專注幾千栽紅土的田,隨著二十四節氣播種收割等等。
整個村莊男女老幼都這樣過生活,無從比較。日子像一杯井裡取出的清水,清淨解渴,卻沒什麼味道,偶有插曲,肯定戲劇張力十足。
先說阿嬤,她有些不修邊幅,終年綁一條頭巾,說是頭風之故,頭巾正中間縫一個福字玉佩。腰間常年圍一件圍兜,圍兜上面有二只口袋,阿嬤把手插在口袋,站在廊前,指揮一家大小。阿嬤鼻頭飽滿,看起來不是很威嚴,但全家對她老人家極盡孝順與敬畏,寒冷冬天只見她鼻水直流,她可以拇指與食指揑著鼻頭,把鼻涕一擰往旁邊一摔,看著日久我也學會這絕招,因為兄弟姐妹大半都遺傳了阿嬷過敏的鼻子。可全家食衣住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即便沒啥收入與錢財,她卻也能從有限物資取得一家溫飽。
某個午后,寒風冷颼颼,村裡一片靜謐,除了狗吠及桌子底下黃白相間大黃貓微弱咪咪聲,沒有新鮮事。阿嬷手揷口袋,食指指著前方人家:「那家孩子偷了我家鷄囡?中午午睡前我還餵了牠們,現在少了一隻」。「誰哪偷了這隻鷄會有報應」。阿嬷表情極生氣,聲音因生氣而顫抖。
鄰近小孩過來圍觀,看著阿嬤氣呼呼漲紅著臉,顯然阿嬤意有所指,應該是影射前鄰文顯嬸家,高吭嗓音震慄左鄰右舍,好比武林高手裡的姥姥掌門人,前廊一站,龍頭杖往地上一頓,威風凜凜,前後左右叔公嬸婆無一出聲,無非想著我家並沒有多一隻鷄,互相凝視不敢出聲,左鄰阿土叔說:「阿嬸妳是否查看糞坑裡是否有鷄毛,前二時辰我彷彿看到妳小兒子和妳的孫子他們追著鷄群跑」。
天下可真沒有秘密,阿嬤把心頭肉小兒子擰著耳朵追問:「説,怎麼回事?」
小叔:「下午太陽那麼大,無處可去,聽到鷄隻咕咕咕吵死了,我跟志忠說不如抓來烤著吃。」「阿娘,以後不敢了」。
我的小叔與大哥大姐面面相覷,因為鷄己被他們三人給殺了,並在後山像烤地瓜般烤著吃掉。
阿嬤硬生生把一肚子氣給壓下。
有點懂事以來,阿公就不在了,阿爸讀了幾年私塾,所有人倫道理特別遵守,唯嗓門特大,每次從海上魚撈返家,一上岸和人打招呼、聊天,三百公尺外的兒女都知道他要收工回家了。
也因為嗓門大救了頂西廳大房進財叔的命。
當年日本佔據浯島時,對浯島百姓百般欺凌,家家戶戶日子忒難過,爸媽説地瓜簽煮地瓜,上層漂著細小蟲屍,照樣煮來吃,貧窮是揮之不去的宿命。
話說進財叔得罪日本人,從海邊潛回村裡,因為霧季,海上一片霧茫茫,朦朧中伸手不見五指,走著走著也沒了方向,老天有眼,進財叔聽到遠處阿爸說話聲音,尋聲而來,看到父親,噗通跪倒在「蚵都腳」旁的海上泥濘,恰似大海抓到一塊浮木,心想有救了。
我的阿爸這會忽然有了心機壓低嗓門,趕緊三下兩下把進財引回村裡。在路上即想好要把進財安置在前鄰枯井裡,因此先帶回家,把梯子繩索準備好,到了深夜偷偷把進財順著繩索放進井底。
沒有向任何人提起,早晚偷送吃食及水,用籃子把食物吊進井㡳。
阿母及阿嬤每天找不到食物,一碗麥糊明明記得放灶上,總是找不著,疑神疑鬼以為家裡到底有何不乾淨鬼魂。當然父親裝聾作啞不回應。
說起日本鬼子阿爸心裡也是有恨。想起年前與大房堂兄被日本鬼子冤打一頓,恨意襲上心頭。堂兄是巡官,阿爸也讀了些書,族裡有漢奸,向日本鬼子密報阿爸堂兄弟不是順民,日本兵在島嶼上也不過千把人,卻耀武揚威,一點風吹草動即抓來拷打。
家以外地方三三兩兩日本兵荷槍實彈搜索,風聲鶴唳。
過了一個多月才稍安靜,日本兵死心不再找,阿爸才把進財弄出井底,稍微易容趕緊找人幫忙下南洋。
總之,歷經這場驚濤駭浪的救人戲碼,真正只有天知地知阿爸與進財叔知。
攸關性命,多年以後説與孩子們聽也就一則故事而已。
村子裡女孩子讀到小學畢業屈指可數,右邊鄰居有七個女兒,每個都沒上學,但是田裡海裡都熟門熟路,我經常羨慕她們姐妹何以如此能幹。村裡沒幾個女生要上國中,沒有同伴的日子讓我非常憂愁,幸好物資不豐也沒讓我自卑,看著哥哥們玩自己用芭樂樹枝做的陀螺,爬到樹上抓「大咧」,我則端了同學借我的漫畫,坐在苦楝樹下,陣陣風兒掠過。任憑它吹亂頭髮。
阿爸説浯島人的命像地瓜,韌性夠,什麼環境都能活,且可以在最困苦時把人給養活。對待地瓜要用虔誠的心,對待這塊土地更要尊敬。
有限的常識,也只能就平常最接近的事物做回憶的描繪;有些畫面跟著血液自然流動,最喜清明時節,倒也不是慎終追遠之類老祖宗留下來的祖訓,對小女孩有多大影響?勿寧説是蚵仔肥了,有七餅可以吃了,姐姐嫂嫂在清明前一晚切了一籮筐一籮筐的芹菜丁、蒜丁、荷蘭豆絲、菜球絲……隔天加上蚵仔丶豆腐絲丶肉絲炒成一盤盤敬祖的菜。用七餅皮包著,好滋味讓每年這一季節變的這般美好。
脫下厚重的棉襖,跟著父親上山種花生,最有趣的是父親丟下兩粒「土豆仁」在鬆軟的泥土上,用腳掌自然踩上去,我的小腳丫疊著阿爸的腳印往前行,他偶爾回頭溫柔的看著我,這一刻是我們父女共同的記憶。玩累了在田邊休息,享受春風輕拂。
家裡種著地瓜、高梁、小麥、花生,以及退潮時下海採收蚵仔,圍捕一些小魚、小蝦、小螃蟹。這是我整個童年的世界,大人男性閒暇做做手工藝品:編竹籃子、籮筐及簡單木凳。每戶人家的男人都有一些本事做竹子、木頭等器具,説是多才多藝也不為過,因左鄰右舍的伯父叔父們做這些家事都很熟練,也會補破網,通常我是蹲在旁邊看。
八二三炮戰剛結束,姑媽與大姐決定偕伴赴台,因姑丈下南洋非常久,已然不回浯島,傳回的信息已經娶了番婆,生了番子,姑媽心冷了。大姐夫被炮彈打死,姐姐沒有依靠,兩個勇敢的女人,決定遠離故鄉,離開這傷心地,尋求屬於她倆的新生活。
我無法理解大人的世界,只是阿母整天在房內啜泣,好長一段時間家
裡氛圍悶透了,我仍喜隨阿爸到海邊,阿爸挑粗桶在田裡施肥,我則吹著海
風,想許多心事,很煩惱為何每日要走那麼遠的路上學?
日子因著兄姐成人,經濟稍微好轉,蓋了一棟堅固的二層樓房。
每日無所事做,捧本小說在二樓陽台吹風,偶然機會讀了瓊瑤小說,鄰居賣麵缐的女兒因家裡經濟好,每本小説都買,我奉她如神,必須向她借。之後讀了《紅樓夢》、《鏡花緣》、《未央歌》、《飄》、《張愛玲全集》,至此竟然無緣由的寂寞起來。
少女情懷憂憂愁愁,想鄰居七姐妹的討山討海生活,偶爾自覺慚愧。
離鄉那晚,對台北的憧憬高過離愁,興奮雀躍的忘了細看爸媽的表情,阿母至少會一段時間食不下嚥,然而只是興奮,輕狂的一群少女期待到寶島,認為會有俯拾皆是的機會,急著當離巢的鳥兒。到了料羅灣,一輪明月照在沙灘上,軍人、百姓、學生排排坐,數都數不清的人頭等著上開口笑的登陸艇,擠上登陸艇的那一剎那,幾位女同學抱在一起痛哭,心裡明白此行江湖險惡,無憂無慮日子從此將告別。前途像開口笑下的大海,一片汪洋,無邊無際,不到二十歲的女生該有什麼想法?船艙底下除了悶熱,加上一股
說不出難聞氣油味汗味伙食味,各種氣味雜陳,加上登陸艇顛顛簸簸,許多人都吐了,女生們躺在那動也不敢動的到了十三號碼頭,雙腳踏在台灣土地,仰望蒼穹,豈是哭字了得?
初時,對繁華的台北感到新鮮,內心好奇勝過恐懼,急著看新奇的事物,搭火車、逛百貨公司、逛夜市,忘了生活的艱難,也經常寫信給大哥、二哥抱怨阮囊羞澀,他們三百、五百接濟我,暗自慶幸有長我許多歲的兄長真好。
走在水泥叢林,抬頭仰望,高樓林立,我,有一日會成為這裡一份子?
我,有一日在這都市會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安身立命的房子竟成為人生的目標。
當一個人由少女到少婦到職場呼風喚雨,這樣轉變歷經十數載,午夜夢迴,自己常常被驚醒,走入㕑房那日開始,柴米油鹽佔滿所有空間,追逐是生活型態,每日急歩追著公車、追著捷運、追著所有的數字,總希望後面加個零,接著被孩子追,這麼長的日子充滿不安與挫折。
某個晨間攬鏡自照,啊,魚尾紋加銀閃的髪絲,這怎麼回事?
沒有了夢,倉皇望著四周冷冰冰的水泥牆,急欲尋找失落的……失落的屋頂燕尾璀璨交趾琉璃?三合院?櫸頭?曾經想過最美的儀式應是在女兒牆內拋個繍球,是的,就這些夢,何以在水泥森林裡汲汲營營,感覺異常悶熱,一點風都沒有,也見不著星星和月亮。
青春換來生活的無虞,很想回頭尋找失落的曾經,故鄉不變,或有日暮鄕關的錯覺,可爸媽不再回頭望我,是我曾經為了人生目標忘了仔細撫看雙親的臉,很長一斷時間忘了回顧阿爸與我的約定:再隨他種一次花生,把腳印疊在他腳印。再陪他看一次阿嬤長眠的田梗,讓他告訴我風從東邊或南邊吹過來,風水好呀。
如今兩鬢已霜白,很想問誰可幫忙追回我們失去的,讓我能看到阿爸在海邊挑著粗桶施肥的背影。
然,只剩海邊的風仍然徐徐吹著。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海邊的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現代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現代散文 |
$ 252 |
現代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252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海邊的風
牧羊女的散文集《海邊的風》,分成「海邊的風」、「砲聲下」、「城市穿梭」、「生活閒情」四大單元。
作者藉著書寫鄉景、鄉情與鄉愁,呈現人生每個階段的不同心境,歷經時空遞嬗,心靈的沉澱,在許多年後,即使再描繪同一座島嶼,同一個家族,以及其風土、人情,也已迥異於過往的青春。
故鄉,在牧羊女的筆下,是一種記憶與味蕾的融合,可以是灶腳、大紅袍、土豆、蚵仔煎……,到了他鄉,即使遇見在城市裡穿梭於小巷裡的咖啡館,也能與家鄉的天空連結。
作者簡介:
牧羊女
本名楊筑君,出生於風光明媚的金門慈湖畔。現任《金門文藝》雜誌總策劃。
十七歲起創作迄今,著有散文集《五月的故事》、《裙襬搖曳》及《島嶼.食事:金門人金門菜》、《時光露穗.浯島紅高粱》等合輯。
曾獲海峽之聲徵文優秀獎、旺報兩岸徵文佳作獎。
作品入選《二〇一五年中國散文精選台灣卷》、《二〇一五年華人女作家文學雙城卷》、策劃報導文學家楊樹清執筆之《金門鄉訊人物誌》一套十冊。
二〇一六年獲評論家黃克全編入《金門現代散文家》。
二〇一七年散文集《海邊的風》出版。
章節試閱
繡 花 鞋
少小離鄉,細數歲月,與母親常相左右不過二十餘載,算是情緣不夠深吧。
長期未能伺親,母親年邁時期,步履蹣跚拄著拐杖影子牢牢烙印心底,為表內心不安,經常利用午休空檔逛城中市場,市場裡面應有盡有,尤其是老年人衣物用品,舉凡吃的、擦的、暖的、涼的、洗的、曬的林林總總,經常逛到流連忘返,寒天該為雙親購置羊毛內衣褲,酷暑該購置麻製背心,有些時候連洗衣精都想帶回浯島,如果您也度過那個年代;物資缺乏交通不便,回娘家真是艱難大事,不是乘登陸艇就是搭軍機,可以想像為人子女的我,多麼想用物資掩飾自己的不孝。
...
少小離鄉,細數歲月,與母親常相左右不過二十餘載,算是情緣不夠深吧。
長期未能伺親,母親年邁時期,步履蹣跚拄著拐杖影子牢牢烙印心底,為表內心不安,經常利用午休空檔逛城中市場,市場裡面應有盡有,尤其是老年人衣物用品,舉凡吃的、擦的、暖的、涼的、洗的、曬的林林總總,經常逛到流連忘返,寒天該為雙親購置羊毛內衣褲,酷暑該購置麻製背心,有些時候連洗衣精都想帶回浯島,如果您也度過那個年代;物資缺乏交通不便,回娘家真是艱難大事,不是乘登陸艇就是搭軍機,可以想像為人子女的我,多麼想用物資掩飾自己的不孝。
...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風中佇立,如此潔淨 ⓪林文義
風吹的方向,應該也是她思念島鄉,不時的深切惦念吧?書題:《海邊的風》如此明確地表白一次又一次離鄉、返鄉的過程。
最初在雜誌上讀到以「牧羊女」作為文章筆名的作者,立即想到前輩作家張秀亞的名著:《牧羊女》。彷彿立即連接的聯想浮翩,這位來自海峽彼方的作者是否就是張秀亞的書迷?青春年代時初習散文的我,不也一樣多麼喜愛張秀亞前之光啟出版、後之爾雅的散文名著:《北窗下》。自然的對這筆名:牧羊女的金門籍作家有著分外好奇的親切之感。
後來有幸在金門籍作家群落的聚會中,黃克全、吳鈞堯...
風吹的方向,應該也是她思念島鄉,不時的深切惦念吧?書題:《海邊的風》如此明確地表白一次又一次離鄉、返鄉的過程。
最初在雜誌上讀到以「牧羊女」作為文章筆名的作者,立即想到前輩作家張秀亞的名著:《牧羊女》。彷彿立即連接的聯想浮翩,這位來自海峽彼方的作者是否就是張秀亞的書迷?青春年代時初習散文的我,不也一樣多麼喜愛張秀亞前之光啟出版、後之爾雅的散文名著:《北窗下》。自然的對這筆名:牧羊女的金門籍作家有著分外好奇的親切之感。
後來有幸在金門籍作家群落的聚會中,黃克全、吳鈞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林文義 風中佇立,如此潔淨
郭強生 期待與祝福
楊樹清 海邊的風,吹過了北方牧場
卷一 海邊的風
父親與北斗星
繍花鞋
灶腳
海邊的風
田邊雜記
正欉大紅袍的記憶
情牽土豆
夢迴四合院
水文嬸的天空
阿才嫂的故事
卷二 砲聲下
漫談食事
濃情蜜意蚵仔煎
紅龜粿的滋味
四弟的喜事
小來週記
砲聲下
天才夢.夢天才
厝邊風采
卷三 城市穿梭
小巷裡的咖啡館
城市穿梭
街角有人在唱歌
夏日二三事
我們的十七歲
秋夜三嘆
卷四 生活閒情
小葉㰖仁、女人、狗
誰説不是愛情
青春戀曲
生活閒情
旅遊小札
訪花都
林文義 風中佇立,如此潔淨
郭強生 期待與祝福
楊樹清 海邊的風,吹過了北方牧場
卷一 海邊的風
父親與北斗星
繍花鞋
灶腳
海邊的風
田邊雜記
正欉大紅袍的記憶
情牽土豆
夢迴四合院
水文嬸的天空
阿才嫂的故事
卷二 砲聲下
漫談食事
濃情蜜意蚵仔煎
紅龜粿的滋味
四弟的喜事
小來週記
砲聲下
天才夢.夢天才
厝邊風采
卷三 城市穿梭
小巷裡的咖啡館
城市穿梭
街角有人在唱歌
夏日二三事
我們的十七歲
秋夜三嘆
卷四 生活閒情
小葉㰖仁、女人、狗
誰説不是愛情
青春戀曲
生活閒情
旅遊小札
訪花都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