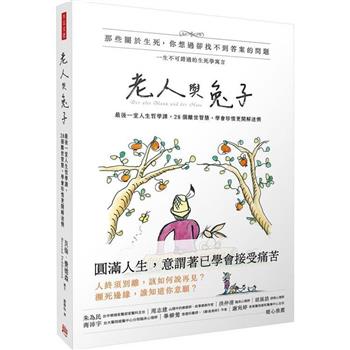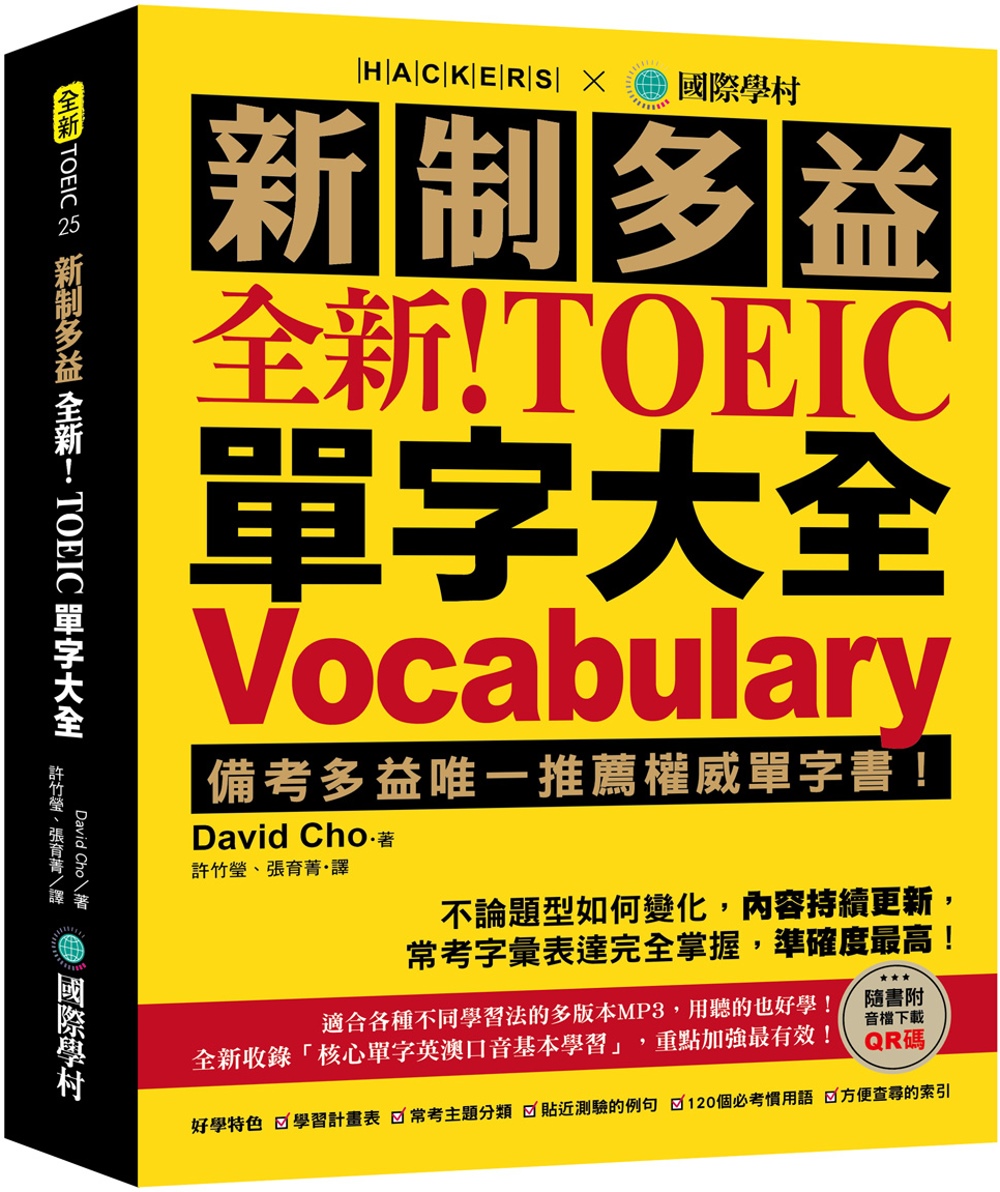出版前言
台灣知名文學家陳映真先生,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作為台灣戰後左翼思想勤勤懇懇的開拓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左翼思想的影響,超越台灣一地及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社會,他的溘然長逝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台灣左翼團體:《批判與再造》雜誌社、前《人間》雜誌同仁、差事劇團、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分別於二○一七年一月七日與二○一七年三月三日,舉辦了「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系列活動。一月七日,主要針對陳映真的思想、精神,進行論述、闡發;三月三日,以具體的文藝創作──詩詞朗誦、戲劇、舞蹈等,呈現陳映真的美學主張(詳細內容,請見本書「輯三──陳映真紀念活動紀錄」)。
這本悼文集,主要收錄了在二○一七年一月七日追思會前後,兩岸三地、日本、美國、漢族、原住民族……,曾經與陳映真共事,並肩作戰的戰友、同志,以及雖未與陳映真有直接接觸,但是在閱讀陳映真的作品,深受感召,進而投入各領域社會變革的青年一代,對於陳映真的追思。這廿餘篇不同年齡、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的文章之中,具體而微呈現了陳映真的人格、思想風貌。
此次台灣左翼悼念映真先生追思活動的總召集人,《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原擬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全面闡釋映真先生的思想淵源,讓世人無論敵友,都能透徹理解這位左翼戰士的思想,提供各界研究陳映真一個新的視野。可惜杜總編輯因諸事纏身,加之對理論文章持慎之又慎的嚴謹態度,故而無法於出版截稿前完成書寫,這是我們最引以為憾的。但也期待杜總編輯的宏文及早完成,一則以撫慰亡靈,一則為左翼陣營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磐。
不同於流俗的「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哲人其萎」的陳詞套語,這本悼文集的出版,旨在能善述陳映真其事,進而善繼其志。我們在哀思中,希望召喚同志承接陳映真點燃的篝火,攜手同行,為人的全面解放,進行不懈的奮鬥!
山崩海頹──敬悼陳映真先生 ◎方聞
早就遠道傳聞,陳映真先生已經臥病十年之久,而且病勢沉重,但是,驟然傳來陳先生過世的噩耗,還是震驚不已。連續多日,一種無法言喻的寂寞和難以排遣的悲愴之感,洶湧而來。
余生也晚,加上海峽阻隔,我並沒有機會結識陳先生。但二十年來,通過他的作品,陳先生卻成了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一大支撐。在〈我的文學和創作與思想〉一文中,陳先生說過:「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給予失望的人以希望,給遭到羞辱的人撿回尊嚴,使被壓抑者得到解放,使撲倒在地上爬不起來的人有勇氣用自己的力量再站起來,和戀愛快樂的人一同快樂,給予受挫折、受辱、受傷的人以力量,那樣的文學才有意義。」
確然如此,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論文,一直以來,都是我汲取希望、力量和勇氣的重要源泉。
(一)尋找失去的視野
如今想來有點不可思議,陳先生是小說名家,但我最早讀到的卻是他的一篇政論文章。我步入大學校門的一九九○年代,正是國際格局發生大變動的時期,蘇東劇變,紅旗落地,西方政要和學者彈冠相慶,「歷史終結論」喧聲震天。中國大陸在一九九二年之後,經濟上全面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接軌」,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大批倒閉和出售為標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快速瓦解,只剩下一層薄薄的意識形態油彩。在這一路線的指引下,一時之間,經濟總量一路飆升,但是,很快地,這種飲鴆止渴式的發展的惡果就暴露無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下崗,生計頓失;資本與權力相互溫存,導致少數人一夜暴富;貧富急劇分化,社會矛盾激增;吏治腐敗、環境污染、倫理崩壞……
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年少無知的我,對於這樣的問題,懷著揮之不去的疑問卻又苦苦難以索解。而當時主流的報刊和講壇,幾乎一邊倒地成了西方教條主義獨霸的天下。「革命」和「社會主義」成了過時、保守的代名詞,備遭奚落。少數堅守理想的革命前輩、理論家和學者,則迅速被邊緣化,而且,他們所慣常使用的、凝固化了的「馬曰列云」式的表達方式,也早已不為大多數的年輕人所接受。
正是在這樣思想苦悶的時刻,我讀到了陳映真先生的文章〈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文章從全球的、結構性的觀點,從第三世界的觀點,從亞洲的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經緯,並對大陸提出懇切的期望和忠告。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識的淵博、析理的明澈、視野的開闊,都是我素所未見的。梁啟超在談到龔自珍時說:「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陳先生的這篇文章,給我的就是同樣的震撼。尤其可貴的,雖然這是一篇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但充滿了人的體溫,讀來毫無枯燥之感。作者熱情誠懇,娓娓道來,不僅發人深思,而且令人感動。
對於一九八○年代以來的大陸知識份子,文章也提出了尖銳而深刻的批評:「和六○、七○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知識份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Compradore litebourgeois intellectuals),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後』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緣於民族的素質,緣於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
讓我訝異不已的是,作者這裡所寫下的幾乎每一個字,都可以和我自己當時的切身感受相印證。
多年以後,我偶然讀到大陸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鄧力群一九九一年六月卅日的一次講話:「最近,臺灣作家陳映真寫了一篇文章,在臺灣的《海峽評論》上登載……很值得大家看一看。陳的文章中一個小題目叫『尋找失去的視野』,寫得可不一般,充滿激情,很有見地。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激勵。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建設、改革開放很有成績,可是在我們中間有些人慢慢地把階級鬥爭的視野丟掉了,慢慢地把第三世界的視野也丟掉了。他希望我們不要丟掉階級鬥爭的視野和第三世界的視野。」
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表明,我當時的感受,實在並非一人的私見。
(二)一個時代的追問
從此,我開始熱心地搜羅陳先生的作品,只要能找得到的,都不放過仔細拜讀的機會,也一次次地從中收穫啟迪、感動、鼓舞和激勵。
讓我欣喜不置的是,在我所就讀的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的、全套十五卷的《陳映真作品集》。但因為沒有副本,所以只限於在館內閱讀,不許出借。有一段時間,只要課餘有暇,我都會待在保存本閱覽室,從第一卷小說《我的弟弟康雄》讀起,順序而下,一直到彙集他人對陳映真作品的評論的最後一卷《文學的思考者》。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在一篇題為〈鞭子與提燈〉的序文中,作者回憶他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投獄,篤信基督教的父親第一次前去看他的情景──在那次約莫十來分鐘的晤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
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
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這些話送給你,擺在羈旅的行囊中,據以為人,據以處事……。
記得我是包含著熱淚聽受了這些話的。即使將「上帝」詮釋成「真理」和「愛」,這三個標準都是不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這些話才成為我一生的勉勵。
當時,我讀完這段話,霎時之間,也不禁眼熱鼻酸,感動之情,不能自已。多年來,我常常想,父子兩人這樣的胸襟、擔當和持守,在當今之世,恐怕日漸少有了,而千百年來,中國人所稱道的滿門忠烈,恐怕也無逾於此了吧。
在陳先生的小說〈鈴璫花〉、〈山路〉、〈趙南棟〉和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中,我第一次遇見了「五十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臺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遇見了「把一生只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的一代人。自願接下「看牛仔班」、為了窮人的孩子挺身而出的老師高東茂;立志給叛賣同志的二兄贖罪、冒充被捕殺的革命者李國坤的妻子,為烈士養老撫幼的少女蔡千惠;在死刑之前,看到天邊的一輪皓月依然無限驚喜的林添福;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殺而數十年屍骨難尋的徐慶蘭和黃逢開……這一串串閃光的、虛構或真實的名字,讓我的心情久久激動難平。
在〈山路〉的末尾,蔡千惠臨終前給自己當年真正的未婚夫、同樣投身革命而長期系獄、僅免一死的黃貞柏留下一份遺書。其中寫道:「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不時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我迄今仍難以忘懷,第一次讀完這段話時,靈魂的巨大戰慄。二十年來,有無數次,每當眼睜睜地看著大陸的社會主義根基一點點動搖時,這些話就會不停地在我的耳邊迴響。
實際上,蔡千惠發出的這個驚心動魄的追問,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追問,是包括一九五○年代撲倒在臺灣刑場上的、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的兩千多萬名烈士的追問。是啊!如果中國的革命墮落了,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步入歧途,如果底層的勞苦大眾再遭背棄,如果社會重回數千年來「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的舊軌,那麼,長眠地下的先烈如何能夠瞑目?而作為後死者的我們,又何顏面對他們的英靈?每一個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理想的人,言念及此,都不能不感到至深的痛苦。
(三)「不!」
但是,一個無法不去面對的現實是,在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的確陷入了低潮。蘇東陣營土崩瓦解,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幾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早已面目全非。以解放全人類為職志的無數革命者,不惜拋擲頭顱所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十年,在一兩代人之後,在自己子弟的手中就先後歸於潰敗?
在小說〈趙南棟〉中,趙慶雲和宋蓉萱夫妻一個為理想從容赴死,一個在大獄中遭囚錮數十年。但是,這對革命者的下一代,對於父母的志業和追求已經全然無法理解,而且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聲色犬馬之樂甘之如飴。長子趙爾平從一個發誓「立業濟世,答恩報德」的有志少年,到心安理得地收受賄賂、狎養情婦,一步步滑入「成功入世」的、富裕、貪嗜而腐敗的世界。次子趙南棟則沉醉於肉欲、吸膠,「讓身體帶著過活」「他喜歡吃,喜歡穿扮,喜歡一切使他的官能滿足的事物……但是,舉凡一旦得手的,不論是人和物品,他總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喪失熱情」。〈趙南棟〉寫作於一九八七年,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在全球佔據半壁江山。但陳先生當時就敏銳地寫出了革命者所面臨的這個巨大悲劇。今天,讀來愈加觸目驚心。
革命者的子弟背離父輩的理想,在中國大陸,更是普遍而巨大的存在。尤其是在最近的卅多年裡,我們看到,從中央到地方,陳先生筆下的這一切,以更加龐大的規模,更加戲劇性的方式,每一天都在人們面前上演。在中國革命史上,多少人放棄安富尊榮的生活,冒著破家亡身的危險,像飛蛾撲火一般地投身革命。但不旋踵間,他們的後代,就徹底脫離了普通百姓,儼然以「紅色貴族」自居,不擇手段地追逐財富和權勢,在百米衝刺式奔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縱情狂歡。
進一步講,在比喻的意義上,可以說,隨著革命的一代逐漸凋零,在大陸的十多億人中,幾乎全都是革命的後代,而且大部分人都曾經分享革命帶來的恩惠。但是,不知不覺之間,有多少人還能記得父輩的理想?在改革開放以來「致富光榮」的政策導引下,多少人熱心嚮往自己心目中的西方資本主義富足安樂的生活,而將社會主義的理念和信仰棄若敝屣?
陳映真先生在小說中描述趙爾平的蛻變時這樣寫道:「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也許作者當時並未意識到,從某種意義上,這不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生動寫照嗎?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確是中國大陸「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而有意無意間,中國革命的「少年時代」對於一個新的、公平的、窮人得解放的社會的熾熱嚮往,也幾乎「崩解淨盡」了。
從世界範圍看,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不同,從蘇俄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國家獲勝的。這就註定了,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後,必須「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但如何保證在這一過程中不「喪心失志」?這或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所必須面對的考題吧。
出獄之後痛感「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臺詞」的趙慶雲,在彌留之際懷想自己的難友,他不禁問道:「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的、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不!」
那時候,趙慶雲常常在沈思中這樣地怒吼過。
的確,縱使歷史的長河有曲折,有回流,但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而不惜肝腦塗地的一代人,絕不會只是一個微末的波瀾。然而,只有後來人高擎他們手中的火炬重新出發,吸取過往的一切經驗教訓,為社會主義探求一條全新的出路,這樣,才能夠讓這一聲怒吼山鳴谷應,氣壯山河。
(四)與歷史對弈
與他筆下的「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一樣,陳映真先生畢生英勇地追逐光明。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他奮不顧身,以自己的靈心與善感、以自己的深思和敏銳、以自己的勇氣與無畏,與黑暗搏鬥,雖百折而不稍屈撓。
在白色恐怖時期,他曾作為政治犯入獄七年,出獄之後,在臺灣,無論國民黨執政,還是在民進黨上臺,他都是「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他畢生嚮往社會主義,追求國家統一,但是,「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同樣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越來越深切的不滿」。
他寫文章、編雜誌、辦出版社、參加社會活動,勇敢地揭破那「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蔑」歷史,不懈地為臺灣、為中國、為世界探索一條更加美好的道路。
謙抑為懷的陳先生曾經說過:「我也知道中國跟世界文學史裡面的一些巨匠,他們,一尊一尊的巨匠站在那裡,我抬頭的時候,如果我戴帽子,帽子一定要掉下來──那麼偉大的作家,想起這些作家,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覺得我怎麼斤斤計較要跟人家講我這段在寫什麼,為什麼這樣寫,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但實際上,他的創作、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已經讓自己成為堪與這些文學巨匠為伍而無愧色的一員。而且,他不僅是中國在魯迅之後,很少見的身兼文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人物,而且是一個戰士,一個抱著淑世的情懷,憂國憂民,畢生「為良心、愛、正義而熱烈地生活、創作和戰鬥」的戰士。陳先生一生的德業和言行,已經為他在歷史上樹立了一座高聳入雲的豐碑。
然而,最後,無情的病魔擊毀了他。在〈趙南棟〉中,陳映真先生寫道:「每回有人被叫出去,我在押房裡唱過:安息吧,親愛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我們走的時候,老趙,你們也這樣唱,」蔡宗義無限緬懷地說:「快四十年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我們,為之生為之死的中國,還是這麼令人深深地擔憂……」
在北京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式上,他的親朋好友同樣用這一首《安息歌》為他送行: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現在是我們的責任 去爭取民主自由
是的,我想,恐怕直到病倒的那一天,對臺灣、對中國、對世界,陳映真先生都還懷抱著深深的憂慮吧。
陳先生竭盡平生的心力與智慧,與歷史對弈。而在他的身後,一場新的歷史棋局已經悄然展開。一度響徹雲霄的「歷史終結論」已經證明不過是淺識者的囈語。隨著二○○八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方資本主義的積弊暴露無遺,美國霸權動搖,歐洲復甦乏力。雖然新社會的萌芽仍未露頭,但舊制度的堅冰開始消融,世界進入未定之天,這也再次全世界的進步人士,提供了一個反思歷史和打造未來的機會。
如今,陳映真先生過世了。我想,只有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接過他手中的旗子,贏得這一場勝負未分的棋局,才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二○一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遠行的左翼戰士:悼念陳映真文集的圖書 |
 |
遠行的左翼戰士:悼念陳映真文集 作者:范綱塏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10-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Others |
$ 270 |
作家傳記 |
$ 270 |
社會人文 |
$ 270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遠行的左翼戰士:悼念陳映真文集
他的人間,走在一個時代的前方,
映出台灣社會的眾生相……
生前被徐復觀譽為「海峽東西第一人」,台灣知名文學家陳映真,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作為台灣戰後左翼思想勤勤懇懇的開拓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左翼思想的影響,超越台灣一地及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社會,他的溘然長逝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不同於流俗的「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哲人其萎」的陳詞套語,這本悼文集的出版,旨在能善述陳映真其事,進而善繼其志。除了情感的追念,也是提供學術、文化、思想界,認識陳映真的另一種視野。
我們在哀思中,召喚著同志承接陳映真點燃的篝火,攜手同行,為人的全面解放,不懈的奮鬥!
作者簡介:
范綱塏,桃園人,1988年生,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畢業。
因「〈我的弟弟康雄〉,有誰還沒有讀過?」一句,正式進入陳映真的小說世界。
編有《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記錄文集》(人間出版:2016)、《路有多長──差事劇團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南方家園出版:2017)。
現為自由工作者。
章節試閱
出版前言
台灣知名文學家陳映真先生,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作為台灣戰後左翼思想勤勤懇懇的開拓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左翼思想的影響,超越台灣一地及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社會,他的溘然長逝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台灣左翼團體:《批判與再造》雜誌社、前《人間》雜誌同仁、差事劇團、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分別於二○一七年一月七日與二○一七年三月三日,舉辦了「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系列活動。一月七日,主要針對陳映真的思想、精神,進行論述、闡發;三月三日,以具體的...
台灣知名文學家陳映真先生,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作為台灣戰後左翼思想勤勤懇懇的開拓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左翼思想的影響,超越台灣一地及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社會,他的溘然長逝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台灣左翼團體:《批判與再造》雜誌社、前《人間》雜誌同仁、差事劇團、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分別於二○一七年一月七日與二○一七年三月三日,舉辦了「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系列活動。一月七日,主要針對陳映真的思想、精神,進行論述、闡發;三月三日,以具體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出版前言
輯一 映真身影
輯二 悼念文章
方 聞◎ 山崩海頹──敬悼陳映真先生
印鐵林◎ 追憶思想家陳映真兄
林瑞含◎ 為我打開台灣第一道門的陳映真
金寶瑜◎ 懷念一個奮戰不懈的左翼戰士──陳映真
施善繼◎ 悼念詩三首
胡清雅◎ 悼念陳映真
范振國◎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
倪慧如◎ ﹁人間﹂路上,送別陳映真
梅丁衍◎ 恨晚成了雋永──緬懷陳映真
郭建平◎ 別了!我的尊師!我們永遠的家人!──敬悼陳映
真先生
陳美霞◎ 紀念陳映真──邁向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輯一 映真身影
輯二 悼念文章
方 聞◎ 山崩海頹──敬悼陳映真先生
印鐵林◎ 追憶思想家陳映真兄
林瑞含◎ 為我打開台灣第一道門的陳映真
金寶瑜◎ 懷念一個奮戰不懈的左翼戰士──陳映真
施善繼◎ 悼念詩三首
胡清雅◎ 悼念陳映真
范振國◎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
倪慧如◎ ﹁人間﹂路上,送別陳映真
梅丁衍◎ 恨晚成了雋永──緬懷陳映真
郭建平◎ 別了!我的尊師!我們永遠的家人!──敬悼陳映
真先生
陳美霞◎ 紀念陳映真──邁向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