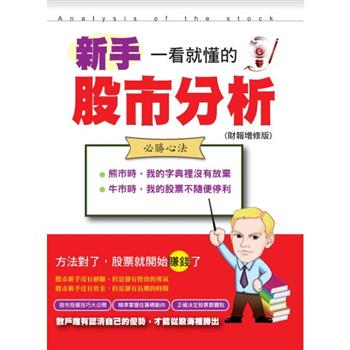當劇場、民眾與文化行動被連結起來時,我們面臨了三項提問。首先,民眾是誰?而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最後,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
民眾是誰?基本上,可以被劃為兩種狀態。一種涉及法國哲學家傅柯所言的「被當代資本與國家的神經系統所征服或安撫的民眾,到底如何抵抗的問題。」那麼,自外於這控制體系下,具備階級對抗位置的稱作「諸眾」(multitude)的民眾,又如何在劇場中,尋找文化行動的抵抗呢?舉例而言,在一個資源豐富的社區與在備受空汙脅迫下的台西村農民,展開庶民戲劇工作坊與表演,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但,即便是後者,在失喪左眼的台灣社會,仍然很難是一種劇場所帶動的文化覺醒。更多的是底層農民的登台,在大眾傳媒中成為一股另類的風潮,驅動社會開展環境運動是階級運動的討論。
這時,滋生了階級處境的思考與實踐方案。並也進一步驅動我們展開田野調查的「蹲點」。我們總是透過「蹲點」,在實際的作為中,開展從自我到他者的參與式觀察。當這樣的作為漸漸讓隔閡消彌,並產生親近的關係時,他者的故事便形成彼此共同的故事。這時,我們開始思考,如何以劇場作為文化行動的可能性。故事,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由說故事的民眾親自搬上表現的空間,稱做舞台。
所以,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它能帶來「革命的預演」嗎?或者,較為真實的情境,就是創造「對話」的場域?可以說,在「後革命」年代,雖然革命顯得那般不入當代的鏡頭;然而,幽靈卻因此意欲表現徘徊不去的無所不在。然則,劇場的瞬間表現,並無法容下任何革命的教條。這無論在一個社會或團體的內部如此,就跨越區域所形成的團體而言,應該更是如此。在「革命」與「對話」的辯證中,兩者無法僅取其一而能生產進步的左翼劇場,這也形成亞洲民眾劇場在創造共同場域時,值得參照的核心價值。
作者簡介:
鍾喬
*1956年出生於台灣台中,原籍苗栗三義客家人。17歲,就讀台中一中時,開始寫詩。1980年代初期,研讀戲劇研究所階段,受教於姚一葦老師,並因初識陳映真先生,在他的介紹下進入<夏潮雜誌>與蘇慶黎一起工作,建構左翼國際觀與藝術觀。1986年,在投身底層寫作的年代,進入<人間雜誌>工作,連結藝術勞作與庶民生活對等的視線。1989年,從亞洲第三世界出發,展開民眾戲劇的文化行動,1996年組合<差事劇團>,巡演兩岸及亞洲各國,進行民眾戲劇的串聯。
*2017年台北市第21屆文化獎得獎人。
*第一屆與第二屆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推薦序
中國教育戲劇導師 李嬰寧
認識差事劇團差不多十多年了,當我第一次讀到鍾喬先生的《觀眾,請站起來!》立時受到震撼,因為此前在布里斯班與Augusto Boal短暫交談開始受到民眾劇場的感染,但還並不清楚如何讓作為觀眾的民眾參與進來,真正地站起來!鍾喬先生的「請站起來!」立時打破了鏡框舞臺的觀演關係,讓觀眾參與了進來。
可惜十餘年後的今天,我才第一次見到鍾喬先生,並較深入地互相瞭解了彼此。有幸我又有機會先讀到了這本新作,鍾喬先生在多年親身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在當前世界語境下、在亞洲國家民眾劇場面臨的現實中,提醒我們學習:觀眾,將如何站起來!
許仁豪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劇評家
今天,本土化的庸俗口號充斥大小文化場域,鍾喬老師幾十年來以劇場與身體實踐了本土關懷的實質意義。他的劇場實踐不只是在地的,更是跨國的,他與菲律賓、韓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民眾劇場的串聯,展示了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弱勢文化行動的跨國界可能,也翻轉了全球化的強勢邏輯。
他的劇場實踐即在地也全球,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隙縫中找到突擊的可能。世界發展至今,一連串的事件證實資本主義制度非但無法解決人類生存問題,更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鍾喬老師的劇場沒有走回老左翼的革命教條,在當今複雜的世界政經結構裡,他以劇場美學跟詩意展示了回應時代危機的可能出路。向左走的詩人在此時此刻必然是孤獨寂寞,但是大音希聲,在喧囂沉默處,我們才能靜心領會詩人對時代的箴言。
汪俊彥 戲劇學者 劇評家
在戒嚴時期,如果「民眾」的身體是作為反抗冷戰的支撐點,那至今後冷戰身體的著力點又是何處?鍾喬老師所領導的差事劇團,一方面繼續堅持記憶於漫長廿世紀尚未清理的帝國、殖民歷史,另一方面,身體已經親臨災難、環境、工農、受刑者等種種臺灣之於現代性體制的創傷口。如同他的劇場一樣,鍾喬老師的散文不僅是再現,除了一次次重複抵抗太過選擇性的歷史以及太容易被抹除的記憶,更是他念茲在茲的使能/培力(empowerment),意在將文字視為身體,號召與喚醒讀者被隱藏的情感與必須期待的辯證。
李薇 差事劇團 資深演員 帳篷劇及舞踏演員
鍾喬是我進入民眾劇場的啟蒙導師。在他的引導下,我才能開始一點一滴地去尋找/追索我的第三世界身體。在每篇文章中不斷提及的歷史與第三世界,是提醒我/我們的身體不是單一個人的,我們必須從歷史與想像中去尋找!從馬尼拉濕熱的「jeepney」車廂到台灣彰化飽受六輕汙染的海邊小村台西村,在一晃眼進入劇場多年的我,也因著鍾喬才得以一步一步地去發掘這個表象世界底下的現實,真正被屬於的我/我們的身體!
那是擁有豐富想像力與解放可能性力量的存在。書中〈揭開新南向文化的帝國面紗〉一文中寫道:「族裡流傳著這樣的神話──每當族人要逃脫外來者的魔障時,便會在森林裡,變身做馬、虎、象……,以動物之身脫離原本居住的地方。」 我想,作為一個劇場工作者,變身是我們用以反抗/表現/溝通/甚而連結的途徑。在這本書中不同的篇章中也能看到許許多多亞洲進步團體/人民的變身!
李哲宇 差事劇團團員 研究劇場社會學
想是鍾喬把劇場拋錨在具象的社會歷史進程,又把社會歷史進程凝縮在虛幻劇場的實踐姿態,這集子在沒有了劇場專業化的論述規約下,模糊了劇場與社會的邊界,也碎裂著台灣社會走過戒嚴、解嚴、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線性發展想像。
鍾喬的書寫,已使表演不只是舞台上演員與觀眾之間的熱鬧,還劃出冷戰戒嚴體制歷史與高度資本化現實下的門道。沿著亞際間的劇場交流、劇場工作者與民眾之間的對等對話、劇場文化行動、文化生產,與書寫者的自我回望,我們終將窺見鍾喬與差事劇團的夥伴們,於近三十年的實踐下仍視劇場為一種打造新共同體的介面。窘迫而無懼地一次又一次地於當代,重新定焦後革命年代的社會想像與社會實踐。
吳思鋒 戲剧評論人
一直以來,我對鍾喬是不滿的,既不滿意也不滿足,因為他組建的差事劇團在拓展左翼劇場的深廣度其實有遲緩的跡象。但既然左翼在台灣一直是被消失的,我的不滿便也是反映一個晚於鍾喬約二十年出生的劇場後生,如何透過差事劇團看見背後更蕪雜、荒漠般的劇場生態、社會語境,進而重新發現。因此在這本書裡,我在閱讀時本書樣稿時,更注意的是文章中遺漏、還沒提到的什麼,那裡隱蔽著台灣的匱乏與空缺,我們必須伸手去指。
中國教育戲劇導師 李嬰寧
認識差事劇團差不多十多年了,當我第一次讀到鍾喬先生的《觀眾,請站起來!》立時受到震撼,因為此前在布里斯班與Augusto Boal短暫交談開始受到民眾劇場的感染,但還並不清楚如何讓作為觀眾的民眾參與進來,真正地站起來!鍾喬先生的「請站起來!」立時打破了鏡框舞臺的觀演關係,讓觀眾參與了進來。
可惜十餘年後的今天,我才第一次見到鍾喬先生,並較深入地互相瞭解了彼此。有幸我又有機會先讀到了這本新作,鍾喬先生在多年親身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在當前世界語境下、在亞洲國家民眾劇場面臨的現實中,提醒我...
作者序
觀眾,如何站起來?
多年以前,我曾以「觀眾,請站起來」為題,在「民眾劇場」的領域發表言論。現在回想,當觀眾不斷被期許為民眾時,民眾也漸漸在網路社媒的時代,失去作為具備階級認同身分的民眾,而消失在新自由主義無限擴張的消費市場中。然而,我們依稀在「民眾性」與「美學性」的辯證中,企圖掌握劇場如何讓民眾站起來的關鍵性。
且從自身工作的場域,作為探討的起點吧!「差事劇團」有兩只翅膀。一只是稱作年度製作的專業劇場演出;一只是前往民眾生活的現場,運用戲劇工作坊,讓民眾登場的演出。現在回想,會出現這樣的機制,前者這只翅膀,既是表現的慾望,也是公共性的參照。亦即,透過藝術性的想像力,讓現實的問題得到美感的提升。例如,圍繞在2004—2005年的「潮喑」(Silent Wave)與「敗金歌劇」(The Corruption Opera),都是針對當年現實政治上,台灣國族民粹論的批判。與此同時,為了增加藝術觀賞能量,加入更多從日本櫻井大造的帳篷劇,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學習來的想像力;至於,回到民眾主體位置的這只翅膀,則是當劇場與民眾相遇時,會出現知識份子為民眾「代言」的反思。為了處理這樣的質問,便也很熱衷地將九○年代初期,在菲律賓與進步劇場夥伴學習的方法,放進重要的參照系統中。並閱讀與奧格斯特‧波瓦(A. Boal)「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相關的理論與實務的書籍,在實踐的誤區踩踏文化地雷,逐漸自行完備化的一套系統。
其實去除「代言」,在討論法國1968 年5月風暴的政治美學時,是一種重要的指標。主要在於以無產階級的人民性,剝除資產階級的美學性。有著高度的政治解放的美學內涵。但,九○年代台灣的社會氛圍,主要以反思80年代,社運知識份子與民眾的對待關係為主。在當時,我們發現,若要走向底層民眾,須展開不以功利或立竿見影為出發的草根進駐。於是,翻閱並共讀保羅、弗萊爾(Paulo Freire)的 〈被壓迫者教育學〉(Padagoge Of The Oppressed)成為一種當下的功課。特別是探討相關「對話」以「世界或社會」作為中介的章節。這樣的解放教育學是進行庶民戲劇工作坊的主要思想參照。大體上說來,讓民眾登場的戲劇工作坊與演出,政治批判性的自覺與高度,其實是成人教育學的借用。亦即,導引民眾發現問題與生產問題意識的身體表現;進步性上,距離人的解放的政治美學,尚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2000年前後,在深化與日本帳篷劇---櫻井大造的交流中,開始反思亞洲民眾劇場的「東方主義異國風情」疑慮。於是,以「差事劇團」的名義,開始較有計畫地展開具生產性的劇場創作,以及在社區中進行襲自亞洲的民眾戲劇的工作坊。對於質疑所產生的行動,必然帶著困頓的痕跡!劇場,作為文化再生產的元素,如何在紮根社會的同時,生產亞洲的連帶?身體,或說劇場美學的身體,終究要回到特定時空下,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中,才得以浮現存在的經緯。換言之,亞洲第三世界劇場有其低度發展社會,做為支撐的背景;時空移換,回返明治維新時期,曾以「脫亞入歐」換身現代性的日本,以及同在「獨裁下的經濟發展」擠身亞洲現代化的韓國與台灣,如何開展自身的劇場表現,進而形成得以返身並前行的劇場文化?這是存在於亞洲劇場內,最具張力的提問。
當劇場、民眾與文化行動被連結起來時,我們面臨了三項提問。首先,民眾是誰?而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最後,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
民眾是誰?基本上,可以被劃為兩種狀態。一種涉及法國哲學家傅柯所言的「被當代資本與國家的神經系統所征服或安撫的民眾,到底如何抵抗的問題。」那麼,自外於這控制體系下,具備階級對抗位置的稱作「諸眾」(multitude)的民眾,又如何在劇場中,尋找文化行動的抵抗呢?舉例而言,在一個資源豐富的社區與在備受空汙脅迫下的台西村農民,展開庶民戲劇工作坊與表演,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但,即便是後者,在失喪左眼的台灣社會,仍然很難是一種劇場所帶動的文化覺醒。更多的是底層農民的登台,在大眾傳媒中成為一股另類的風潮,驅動社會開展環境運動是階級運動的討論。
以上這個提問的發生,主要是為了釐清劇場作為一種自主的文化,在與性質有別的民眾發生關係時,如何找到恰當的存在。這就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有關。簡言之,即是劇場的發生和民眾的辯證關係是什麼?也就是,不同情境下的民眾,在劇場發生的過程中,將顯現不同狀態的(empowerment),這個字眼一般中文翻譯為「培力」;有一位朋友黃福魁先生譯作「使能」,即「使自己能也使他者能」。相關於這方面,便涉及劇場工作者(在這裡,不稱為藝術家)與民眾的對等關係如何被建構。這裡稱對等關係,不稱平等關係。因為,對等是一種流動對話關係。它將涉及從自我到他者,交互「使能」的來回互動,不斷相互聆聽、學習與表達的過程。這樣的探索,讓我們得以回返民眾生活的現場。然而,重點在於,我們一般地並不滿足於只以「懷舊」或者「復古」的心態,去面對處於弱勢或被壓迫狀態的民眾。
這時,滋生了階級處境的思考與實踐方案。並也進一步驅動我們展開田野調查的「蹲點」。我們總是透過「蹲點」,在實際的作為中,開展從自我到他者的參與式觀察。當這樣的作為漸漸讓隔閡消彌,並產生親近的關係時,他者的故事便形成彼此共同的故事。這時,我們開始思考,如何以劇場作為文化行動的可能性。故事,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由說故事的民眾親自搬上表現的空間,稱做舞台。
所以,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它能帶來「革命的預演」嗎?或者,較為真實的情境,就是創造「對話」的場域?可以說,在「後革命」年代,雖然革命顯得那般不入當代的鏡頭;然而,幽靈卻因此意欲表現徘徊不去的無所不在。然則,劇場的瞬間表現,並無法容下任何革命的教條。這無論在一個社會或團體的內部如此,就跨越區域所形成的團體而言,應該更是如此。在「革命」與「對話」的辯證中,兩者無法僅取其一而能生產進步的左翼劇場,這也形成亞洲民眾劇場在創造共同場域時,值得參照的核心價值。
這將近二十多年來,相關於亞洲民眾劇場的交流。最早起始於法蘭茲‧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 白面具》中,對於西方以資本帝國出發,延伸的文化霸權的抵抗;並進而思考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文化「被殖民」或「自我殖民」的交錯現象與本質。歸根結柢,現代化的誘因與現代性的民族想像,是最終須被面對的問題本身!劇場,畢竟是生活與生命經驗的藝術表現,反應或撞擊著日常的提升之外,並在實質與象徵層面,不斷朝向共同體的方向,挑戰參與者對於共構一處有別於空間的「場域」的可能性。
這「場域」有人的時間感具存期間,因此顯得必非只是一個固態的空間,而是流動的對話「場域」。這當然是有意思且相當關鍵的。主要在於,除了表演做為工作成果的一項重要元素之外,過程如何被共同完成,是劇場之所以稱之為劇場,並具備共同體性質的關鍵因素,幾乎無可稍稍忽略。亞洲民眾劇場連線在對應這個「場域」的同時,共同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應該是「場域」如何與「共同體」產生辯證關聯的要點。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交流是以表演呈現為主體,或以重視過程的互動為主體,又或兩相辯證產生的結果,才是得以被討論的課題。
因此,亞洲劇場連線是區域共同體在發生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話機制,既是「發生的」,也是「現場的」,更是「當下的」!在區域對話的身體行動過程中,超越了個別劇場藝術家的參與,更有別於以國家作為單位的競比或動員。這樣的思維底下所形成的互動關係,是以參與者相互間的互動與對話,做為考量基點。藉此達成區域共同體的彼此關照與看待。這同時,也在這前提下,針對表演與觀眾間的互動,展開對話式的交流。亦即,不僅僅展現演出成果,而且在觀眾面前,將形成演出的方法與美學並呈於公共空間,即劇場中。而後,與現場觀眾建構對話關係。
這樣的亞洲民眾劇場,從「亞際」(inter—asia)出發,顧名思義即亞洲之間的意思。強調的是一種:對等交流的流動狀態。一旦,固化,則失去相互以世界為中介的「對話」情境。這是亞洲交流,是「去文化殖民化」語境下的核心命題。怎麼說呢?在「解殖」、「去冷戰」、「去帝國」需三位一體對待的亞際交流中,民眾的異中求同是:解脫官式威權與國際霸權的不二法門。這在亞洲各國家或領域,幾乎是不待明言的共識。
有時,論及劇場與民眾,題外的聯想,會是更有意思的。這就讓我再次想起,魯迅在〈野草〉一文的 題辭上說: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如果,劇場之於民眾,是一種啟蒙的關係。劇場便已經不是劇場,而是講堂。因為如此,每一次的「使能」(Empowerment),都是死亡後的新生。民眾戲劇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對自身、對他者、對融入後演變為民眾的觀眾。雖說,很可能就是稍縱即逝覺醒與變身,延續的,卻是創造對話的平台,在梳理革命記憶中,重新繪製另類的第三世界文化藍圖。因為,這裡勾勒的世界,並非金字塔的權力建構,基盤遠非在於成就上對下的穩固關係。所以,每一次劇場的發生,似乎都可比喻成:死亡,因為曾經存活而成過去;腐朽,讓我們知道並不空虛。
因此,我對死亡與腐朽皆有大歡喜!
觀眾,如何站起來?
多年以前,我曾以「觀眾,請站起來」為題,在「民眾劇場」的領域發表言論。現在回想,當觀眾不斷被期許為民眾時,民眾也漸漸在網路社媒的時代,失去作為具備階級認同身分的民眾,而消失在新自由主義無限擴張的消費市場中。然而,我們依稀在「民眾性」與「美學性」的辯證中,企圖掌握劇場如何讓民眾站起來的關鍵性。
且從自身工作的場域,作為探討的起點吧!「差事劇團」有兩只翅膀。一只是稱作年度製作的專業劇場演出;一只是前往民眾生活的現場,運用戲劇工作坊,讓民眾登場的演出。現在回想,會出現這樣的機制,前者...
目錄
推薦文
自序:觀眾,如何站起來?
輯一劇場民眾亞洲連結
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
劇場,亞際作為交流的向度
東亞民眾戲劇的另類視野
冷戰風雲下的客家運動
帳篷劇是想像力的避難所
在東亞核心現場移動的舞踏──魂之結
誰是說故事的人──跨越邊界的《鏡花轉》
揭開新南向文化的帝國面紗
來自南方的劇場──與泰國民眾戲劇的重逢
魔幻寫實的瞬間──拉丁美洲攝影展
輯二劇場,改造世界的文化想像
劇場能改造世界嗎?──亞際民眾戲劇的反思
劇場、社區共同體與變身──兩種劇場、民眾與社區
劇場,革命與對話──探查「被壓迫者劇場」
劇場作為看見彼此的場域──《亞瑟,不一樣》與《歐菲斯星球》
1895,火燒庄──怎樣的抉擇?
身體革命:新工人劇場
血與汗──《我的詩篇》,紀錄電影與詩歌的對話
反戰,2003──街頭行動劇
一個劇作家的誕生與死滅
《明白歌》──敘事、說唱與民眾參與劇場
輯三劇場作為文化行動
文化行動的入徑──從「回到里山」到「返鄉的進擊」
返鄉的進擊──在台西村的文化行動
回到里山的文化行動──從美濃到大地藝術祭
劇場,以文化行動現身
說出故事的人
變身的哪吒──寫給囚禁中的非行少年
在文學、思想與行動中──悼映真老師
輯四劇場與文化生產
在後現代的避走中反抗
近身的虛構或真相──夜長夢多
《夜半鼓聲》敲響的是什麼?
儀式、夢境與救贖的危機──〈美國民主〉的美學聯想
劇場與作家的思想對話──關於《另一件差事》
漢生海賊王
輯五轉身前行
轉身──寫給母親
父親的舊鞋
撿骨
血液的旅途
〈來甦〉的山路上,送你遠行──追思陳映真先生
在右外野的草叢中──1970
後記
推薦文
自序:觀眾,如何站起來?
輯一劇場民眾亞洲連結
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
劇場,亞際作為交流的向度
東亞民眾戲劇的另類視野
冷戰風雲下的客家運動
帳篷劇是想像力的避難所
在東亞核心現場移動的舞踏──魂之結
誰是說故事的人──跨越邊界的《鏡花轉》
揭開新南向文化的帝國面紗
來自南方的劇場──與泰國民眾戲劇的重逢
魔幻寫實的瞬間──拉丁美洲攝影展
輯二劇場,改造世界的文化想像
劇場能改造世界嗎?──亞際民眾戲劇的反思
劇場、社區共同體與變身──兩種劇場、民眾與社區
劇場,革命與對話──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