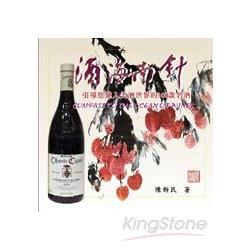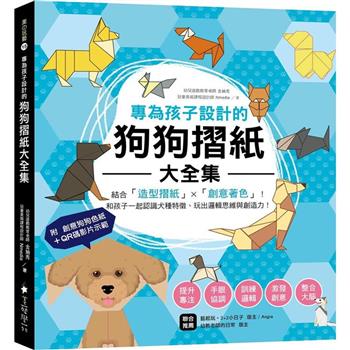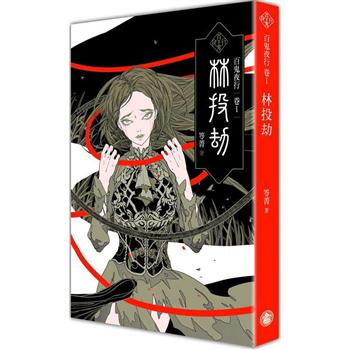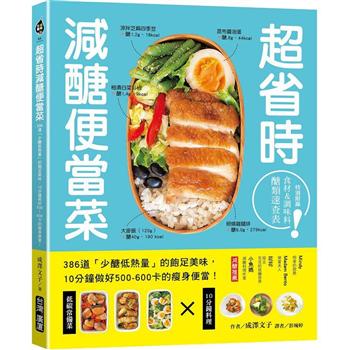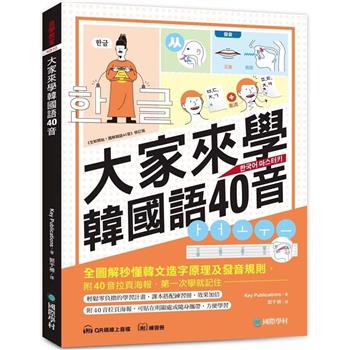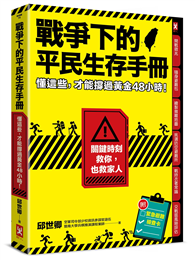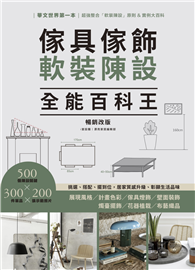葡萄酒怎麼喝?怎麼品嚐?其背後的故事又為何?
本書為作者累積三十餘年品酒經驗及酒學知識,薈萃出來之品酒心得,介紹全世界信價比最高的葡萄酒,共分100個產區與葡萄品種,每種三款共計300瓶,款款都有極高的評價,而且價錢都在新台幣2000元以下,值得愛酒人士細細閱讀。
本書特色
◆精選全世界各國300瓶價格在2,000元以下的葡萄酒
◆詳細介紹酒莊歷史、地理風土
◆充份釀酒葡萄品種、釀酒方法
◆以三十年品酒經驗,說明各葡萄酒特色並推薦延伸品嚐、進階品嚐相關葡萄酒。
作者簡介:
陳新明
為國內著名的公法學者與葡萄酒書作者,其撰寫之「稀世珍釀—世界百大葡萄酒」、「酒緣彙述」及「揀飲錄」普受國內外品酒界的重視與歡迎。「稀世珍釀—世界百大葡萄酒」及「酒緣彙述」並榮獲2008年馬德里世界美食美酒圖書大展(世界酒類)之首獎。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一日須傾三百杯
/ 楊子葆
新民兄又完成一本葡萄酒新書。書中暢談他心目中價位合理,能突顯葡萄品種、產地特色,並已獲得公允評價之好酒一百種,共三百款,跨越新舊世界,涵蓋歐美亞非,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令人情怡心曠,神馳欲醉。也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襄陽歌》中傳唱千古的名句:「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
當代詩人余光中論述李白時曾歡喜讚嘆道:「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一個人,一杯酒,幾句詩,就撐起半個盛唐氣象;而同樣另一個人,一本書,選出三百款名酒,評點全球葡萄酒如畫江山;時間雖然相差一千三百年,卻有一樣的氣勢與自信,並同樣讓我們大開眼界。
遙想詩仙當年事蹟,李白應該嘗過、而且喜歡葡萄酒的。回顧歷史,中國有關葡萄酒的最早記載應該是司馬遷的《史紀‧大宛列傳》,書中提到西漢張騫在西元前一三九年出使西域時,在大宛國發現盛產的葡萄酒,驚豔之餘將葡萄種植與釀造技術帶到中原,這應該也是歐亞中葡萄(Vitis Vinifera)首度引進中國的紀錄。
漢代引進的葡萄酒,到了唐代開始深入本地社會。唐朝大將軍侯君集滅西域高昌國(現今的新疆吐魯番)凱旋,也帶回當地的葡萄品種與釀酒技術,很多人相信現在已經被視為中國特有釀酒葡萄品種的「蛇龍珠」(Cabernet Gernischt),就是在這個時候引進的。唐代詩人李新頎作品〈古從軍行〉裡,就有「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這樣的句子,而其中的「蒲桃」即為葡萄之古名。作為一個開放富裕的社會,唐代不僅貴族之間流行品嘗葡萄酒,民間釀製與飲用葡萄酒的情形也很普遍,詩人王績的五言絕句《過酒家》:「竹葉連糟翠,蒲桃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後爲誰空。」將本地出產的竹葉青與外來的葡萄酒並列,可見當時的流行風尚。
輾轉到了我們的這個時代,葡萄酒成為全球流行的文化商品之一,而亞洲社會,或者華人社會,除全盤西化之外,似乎應該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品味座標。事實上,在法國兩位記者蒙度(Aymeric Mantoux)與桑瑪(Benoist Simmat)合著的新書《葡萄酒戰爭》(La guerre des vins, 2012)裡,就將「二○一一北京品酒會」(Le jugemebt de Pékin 2011)與帶動美國加州納帕谷地葡萄酒在世界市場上崛起的「一九七六巴黎品酒會」(Le jugemebt de Paris 1976)相提並論,葡萄酒的華人觀點顯然越來越受到重視。
這樣的趨勢,我們可以在日本看到:一九九五年奪得「世界最佳侍酒師大賽」(Meilleur Sommelier du Monde)第一名的日本侍酒師田崎真也(Tasaki Shinya),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壯舉」之一是,他在二○○一年初的日本《Wine Life》雜誌裡,為紀念進入二十一世紀推薦了「世界之Best Wine 64」六十四款葡萄酒,其中法國酒有二十五款,佔了總數的四成,但被譽「葡萄酒之后」的波爾多葡萄酒,居然連一款也沒有入選!這分名單一經公佈,彷彿在葡萄酒世界裡投下一枚原子彈,轟然爆破,餘波至今蕩漾。
而韓裔葡萄酒大師李志延(Jeannie Cho Lee)所撰寫的《亞洲味蕾》(Asian Palate, 2009)或新加坡葡萄酒作家蘇恩(Edwin Soon)的《葡萄酒與亞洲菜的搭配》(Pairing Wine with Asian Food, 2009),一方面擴大亞洲的視野,一方面也為全球化的葡萄酒文化提供在地化的元素與新意。
新民兄的葡萄酒著作,從《稀世珍釀》、《酒緣彙述》、《撿飲錄》,到這一本《酒海南針》,在我看來,正是在同樣的脈絡裡越見精采的努力。從書中讀到一些自己曾有幸欣賞過而且深愛的葡萄酒,例如法國布根地樂花酒園的紅花與白花、波爾多的無憂堡、朱哈的礦石酒,或是奧地利的綠維特林、南非的康斯坦斯…,總讓我陷入美好的回憶;而更多迄今無緣品嘗的好酒,則令人心生嚮往,恨不得立刻找來一探究竟。新民兄的新書,竟勾起我們對白居易「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某種烏托邦境界的無限想望。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但是葡萄酒文化的美好,卻不妨微醺,甚至暢飲至醉。新民兄為我們推薦三百款葡萄美酒,且讓我們忘卻身外無窮事,一日傾滿三百杯!
名人推薦:一日須傾三百杯
/ 楊子葆
新民兄又完成一本葡萄酒新書。書中暢談他心目中價位合理,能突顯葡萄品種、產地特色,並已獲得公允評價之好酒一百種,共三百款,跨越新舊世界,涵蓋歐美亞非,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令人情怡心曠,神馳欲醉。也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襄陽歌》中傳唱千古的名句:「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
當代詩人余光中論述李白時曾歡喜讚嘆道:「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一個人,一杯酒,幾句詩,就撐...
章節試閱
天、地、人的完美結合—布根地杜卡匹酒莊地區級酒
Bourgogne,Bernard Dugat-Py
一、不知不可Something You May Have to Know:
法國紅酒博得舉世聞名的兩大功臣,正巧和德國汽車聞名於世,都是「雙B」:後者是Mercedes Benz和BMW;前者則是布根地Burgundy(法文Bourgogne)與波爾多(Bordeaux)。
布根地酒與波爾多酒有許多的差異,正如同牛肉之於羊肉或是河鮮之於海鮮。套一句英國著名的酒評家諾曼(Remington Norman)的話:「兩者相差達400哩」。這一句英文形容詞,正貼切地符合一句我國諺語:「相差十萬八千里」。
除了風土條件的差異(波爾多靠近大西洋,容易受到海洋氣候的影響;布根地則無此影響)外,最重要的差別乃葡萄品種與釀製方式。波爾多以三種葡萄為主:赤霞珠葡萄(Cabernet Sauvignon)可譯為卡伯耐.蘇維濃。中國早在清末引進此葡萄時,以其鮮紅色澤美如晚霞,故稱之為「赤霞珠」,沿用至今。另外一款為赤霞珠的近親-卡伯耐.佛蘭(Cabernet Franc),也有中文譯名「品麗珠」,故本書也採此美麗譯名。及美洛葡萄(Merlot)。同時釀造方式採取混釀,即按照各地區各種葡萄成熟的先後,依照其色澤、口感豐厚及芬芳度…,以一定的比例調配,以求色香味都達到最好的標準,例如以波爾多左岸為例,便所謂的「波爾多調配模式」(Bordeaux Blend)。依法律規定,這是許可以5種葡萄來調配,且這種調配依各酒莊及各年份都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例如在梅多區多半是可以下述模式顯示出來:
赤霞珠(60%至70%)+美洛(10%至20%)+其他小配角之品麗珠(Cabernet Franc)、小維多(Petit Verdot)及馬貝克(Malbec)等三種分配其他的比例。
至於波爾多的右岸,則為美洛擔綱主角,取代了左岸赤霞珠的地位,比例為:美洛(70%)+品麗珠(20%)+赤霞珠(10%)。唯一值得一述的例外則是本地天王酒莊:白馬堡(Chevel Blanc)的逆勢操作,以品麗珠70%+美洛30%,讓標準配角的品麗珠翻身成為主角。
至於布根地產酒的酒區主要是沿著第戎(Dijon)往南延綿160公里的狹長地帶。而其精華區則是在北端總共35公里長,號稱「金坡」(Cote d’Or)之處。而金坡又可一分為二:分為「北紅南白」,北邊之夜坡(Cote de Nuits),以釀造紅酒為主;南邊之波恩坡(Cote de Beaune),雖然紅白酒皆釀,但以白酒揚名於世。而葡萄種類,紅酒以黑皮諾(Pinot Noir)為主、白酒以莎當妮為主,皆採單一品種釀製。能夠把「全部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可見得黑皮諾與莎當妮都可釀出一流色澤、酒體強健、濃郁口感及芬芳至極的美酒。
另外經營的方式也透露兩地區絕大的差異。波爾多屬於較晚成名的酒區,工業革命帶來的財富,與大規模資金操作的市場模式,讓波爾多酒可以變成資本集中而經營的酒業,故每個酒莊規模較大,且具有較強的銷售(包括外銷)能力。至於布根地則偏向傳統農業,且屬於標準的「小農制」。因為布根地早至17世紀便成為法國第一名酒區,有限的土地隨著繼承的分割,一代一代的傳下來,造成各酒區的小農林立,每家酒莊擁有幾乎很多都不到1公頃。這種「百鳥齊鳴」的特色,讓每個酒莊各有特色,自然能夠吸引到知音,也因為產量太少(許多酒莊每年不過生產以百瓶計的數量),無法達到外銷規模,優質的布根地酒往往成為行家們珍賞的對象。
因此布根地酒(特別是著名酒區與酒莊的優質酒),在一個地區的銷售標準,正可以作為檢驗該地美酒水準的指標也。臺灣的美酒文化發展路程也印證了這個趨勢:從濃郁且較為容易購得的波爾多酒開始,而後品酒界逐漸地發現布根地酒優雅、稀有的吸引力,而將品酒會的主角轉向布根地酒也。
布根地酒既然是小農制,各酒莊各有存活之道,也各累積了數百年的釀酒工藝之經驗。彷彿春天百花爭豔一樣,布根地酒具有誘人的多樣性。價錢方面,依據市場供需定律,頂級的布根地酒區與酒廠,其價錢多半高得咋人。例如每一年全世界最貴的紅酒,當推羅曼尼.康帝(Romanée-Conti),最差的年份一瓶也要1萬美元!
在此我們也要了解一下布根地的產區四級分級制度。布根地面積接近4萬公頃,年產量可以高達3億3千萬瓶。而最高等級的頂級園區(Grand Cru),只佔總產量的1%,共有33個酒園列入此分級之內(其中8個園區為白酒);位居第2位的一級園區(Premier Cru),佔總產量的11%,列入此等級的酒園則有684個。再下一級則為村莊級(Village),占總產量的23%。至於剩下的屬於餐桌酒水準的地區級(Régionale)則超過65%的總產量。
如果要享受布根地紅酒的滋味,自然要由一級園開始。雖然對布根地紅酒作第一流的享受,當然是選擇老布根地-即年份達到成熟期、出自頂級酒園的老布根地紅酒,才能夠真正地體會出成熟黑皮諾具有熟透烏梅、蜜餞、鮮花甚至中藥當歸的不可思議之香氣。但所有的頂級園的新酒都極昂貴,也超出了本書的選擇門檻。何況成熟的老酒?因此本書選擇推薦的各款布根地酒,可能來自地區級村莊級最高只能出自一級園,但不減可獲得的樂趣也!
布根地酒之所以迷人,乃基於「新老各有韻味」。年輕的布根地酒色澤鮮豔油亮,有如石榴紅豔麗,入口則有櫻桃、桑椹的特徵;成熟的布根地酒色澤轉為橙黃,香氣一變為熟梅、黃李子,洋溢著花香。新酒具有另一個誘因乃是:價錢。故本書推薦酒友品嚐布根地的新酒,如果要「驚豔」黑皮諾葡萄的特色,當然要挑選出自第一流酒莊者。套一句俗話:強將手下無弱兵,即使第一流酒莊生產的最基本款地區級酒,也酒莊釀酒能手親自調配出來的黑皮諾的優點少表現無遺。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國外隨著世界經濟情勢的惡化,對於法國美酒的衝擊甚烈。許多布根地酒莊也感受到國外購買力的降低,因此轉向由基層固本,加強了地區酒及村莊酒的品質。對愛酒之士而言,這毋疑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改變。現在許多鼎鼎有名的大酒莊,如卡木賽(Meo-Camuzet)、格厚斯(A.F. Gros)…的村基本款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
作為本書介紹的第一款布根地酒,這一個「序曲」,當由有布根地「新酒神」-貝納.杜卡(Bernard Dugat)所釀出的「杜卡匹布根地酒」來擔綱演出。
二、本酒的特色About the Wine:
1973年在布根地日芙萊.香柏罈地區(Gevrey-Chambertin)-這可是拿破崙最鐘愛的美酒可見本書第8號酒-一位在此釀酒已經是第四代的皮耶.杜卡先生,給他15歲的兒子貝納買下一片小小的果園,讓他立業。兩年後貝納釀出了處女作,卻獲得成功的迴響。而後貝納陸續收購20餘處小果園,成為今日貝納擁有的「杜卡匹酒莊」(Dugat-Py)的規模(Py是貝納夫人的娘家姓)。
貝納被公認為乃是繼布根地傳奇人物-人稱「酒神」的亨利.薩耶(Henri Jayer)後的另一個傳奇人物,便可知杜卡匹在布根地酒壇的崇高地位也。
至於在2006年去世的亨利.薩耶,其生前所釀製的遺作,每瓶都在拍賣會上敲出令人驚異的高價,例如其一級園區的克羅.帕蘭圖(Cros Parantoux),在最後一個年份(2003年)之前,拍賣價都超過頂級園區的羅曼尼.康帝。所以薩耶酒,絕大多數的酒友只能遙想其滋味矣!
但幸好杜卡匹酒莊的地區酒,可以多少彌補愛酒人的遺憾。本酒莊各款酒全部都是有機栽培。其分散於20餘處的園區中,幾乎全部少於1公頃,其中納入頂級園有5個(1款白酒);1級園有6個(2款白酒);鄉村級的有6個(1款白酒);地區級的有3個(1款白酒)。最頂級的看家本領,則是「香柏罈酒」,由接近百年的老藤所釀成,年產量不足300瓶。這也是選入拙著「稀世珍釀-百大葡萄酒」的一款酒,每瓶新上市高達1500美金以上。
至於量最多的地區級紅酒,年產量也不過6000瓶上下,為頂級香柏罈酒的20倍,但分散全世界,臺灣每年進口不過三、五百瓶左右。葡萄園區總共1.4公頃,葡萄樹齡約為35年。葡萄採收後會醇化12至18個月,只有百分之十為新桶。品嚐時,剛開始有淡淡的鹹味、苦味,夾雜著漿果、加州紅肉李的淡甜與淡酸,但仍覺得十分明顯的酒精度,造成頗有生命力的感覺,彷彿酒液會跳動一樣。這是一款會令人感動的好酒。
雖然每年僅有少量入台,且酒商多半採預售方式銷售杜卡匹酒莊各款酒,酒友們如要體會貝納大師的絕活,恐怕得要勤於和酒商聯繫,爭取這些瓶瓶得之不易的機會也。
三、延伸品嚐 Extensive Tasting:
要找到一瓶能夠PK貝納大師的地區酒,委實並不容易。還好「酒神」亨利.薩耶有個好侄兒艾曼紐.胡傑(Emmanuel Rouget)的酒莊,也釀出了不錯的地區酒。
話說薩耶大師膝下只有2個女兒,都沒有興趣繼承父業,反而是侄子胡傑很早就在舅舅身邊打雜,並學會了釀酒的技巧。大師在1989年宣布金盆洗手後,卻退而不休,從旁協助侄兒的釀酒事業,直到1997年為止。因此胡傑酒莊是名,薩耶酒是實,標標準準的「薩規胡隨」。
胡傑酒莊釀出的克羅.帕蘭圖酒,雖然沒有舅舅的傳奇酒如此的神妙,但也盡得了真傳,每年只產4000瓶,出廠價約在300美金之譜,但在台北市價至少超過4萬台幣(2009年份),也是列入拙著「稀世珍釀」的世界百大行列。
本書推薦其釀製的地區酒。這是一款可以代表布根地優質新酒,且能夠品嚐出黑皮諾新鮮釀成的滋味:優雅、帶點酸味的櫻桃與山楂味。顏色呈漂亮的深石榴紅,香氣活潑但不深沈。陳年的木桶只有25%是新桶,對地區酒而言已經難得可貴也。市價也很合理,在1500元台幣上下。
至於其地區酒中,另有一款Passetoutgrain,這是在黑皮諾葡萄外,另外混釀了較為廉價、專門釀製薄酒萊酒的佳美葡萄,因此口感偏向甜美,酒體的紮實度也隨之降低,似乎與胡傑酒莊纖細優雅的風格背道而馳,可以忽略之。
胡傑的地區酒,新鮮時品嚐固然有其優美的風味,但缺點卻是無法陳年。超過10年以上時,疲態畢露。對於頂級酒莊而言,即使地區酒也應當起碼地具有陳年10年以上的實力。
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本書打算破例多介紹一支「延伸品嚐」酒。
這一款出自於高諾酒莊(Domaine Michel Gaunoux)的布根地地區酒,確有令人吃驚的陳年實力。一般愛酒之士,儘管對布根地酒頗有研究,一聽到高諾酒莊,恐怕腦中也無印象。的確,這是一家成立才20年的酒莊。1990年,當今莊主米謝爾的父親馮雙(François)在波瑪酒村,成立了酒莊,並在附近幾個產區內買下了6公頃園區。父子一起打拼,以釀製量少質優的方針為主。本酒打出的名聲是以白酒為始。其在白酒的產區莫瑟區有3塊1級園區,釀出的白酒可挑戰頂級酒區的品質,很快地聲譽鵲起。
不過其紅酒也相當優異。這一款地區級的布根地酒,上市後便有極為亮麗的深紅色。我特別欣賞其陳年後的表現。本書在完稿前,特別開了一瓶1995年份的地區酒,來考驗其陳年的實力。這款酒沈睡了17年後,有極為清澈的酒質,沒有一丁點的沈澱;酒色呈漂亮的橘黃色,油油晃晃,突出的烏梅味撲鼻而來,乃典型的布根地黑皮諾迷人的香味。入口後有清晰的山楂、草莓與蜜餞味。酒汁殘餘杯中幾分鐘後,還可嗅到當歸味-這是我在幾乎所有第一流的布根地酒中,包括天王級的羅曼尼‧康帝中,都會聞到的味道。
這瓶老酒居然上市時,售價不過1500台幣上下。這也是一款可以和杜卡匹地區酒並肩躺在您儲酒櫃中,一起接受時間之神考驗的不二選擇也。
四、進階品賞 Advanced Tasting:
杜卡匹酒莊上述的地區酒,已經十分精彩。如果想要更上一層樓,而價錢也合理的話,應當試試杜卡匹另一款屬於「單園釀造」的地區級酒-哈理那(Cuvee Halinard)。這是出自僅有0.4公頃的園區,年產量為2500至3500瓶,樹齡由25至75年不等。陳年期間為1年半,橡木桶也一樣只有1成為新桶。
哈理那雖為地區級酒,但已經有晉升鄉村級的水準。但酒質比另一款地區級酒更為纖細,同時酒香也更為集中濃郁。本款酒甚至可以比其他普通酒莊的頂級酒還要出色。台北偶然一見本酒,售價約在2000元上下,剛好可跨入本書抉選的門檻。如果年份好時,酒友為之多付一千元,我也認為值得也。
天、地、人的完美結合—布根地杜卡匹酒莊地區級酒
Bourgogne,Bernard Dugat-Py
一、不知不可Something You May Have to Know:
法國紅酒博得舉世聞名的兩大功臣,正巧和德國汽車聞名於世,都是「雙B」:後者是Mercedes Benz和BMW;前者則是布根地Burgundy(法文Bourgogne)與波爾多(Bordeaux)。
布根地酒與波爾多酒有許多的差異,正如同牛肉之於羊肉或是河鮮之於海鮮。套一句英國著名的酒評家諾曼(Remington Norman)的話:「兩者相差達400哩」。這一句英文形容詞,正貼切地符合一句我國諺語:「相差十萬八千里」。
除了風土條件的...
目錄
001天、地、人的完美結合—布根地杜卡匹酒莊村莊酒
002鐵娘子的堅持-樂花酒園的紅花與白花
003飲中增德—布根地波恩及夜坡濟貧醫院酒
004拼酒、而不拼命的—布根地品酒騎士團
005產自黑皮諾葡萄酒麥加聖地的沃恩.羅曼尼村莊酒
006想起「屠龍勇士」-飛復來酒莊「聖喬治之夜」
007香柏‧木西尼—布根地的貴族品味
008英雄已死、英雄不死—拿破崙鍾情的日芙萊.香柏罈
009布根地的「杏花村白酒」-傑‧莫尼爾酒莊的村莊級白酒「騎士」
010白酒小貴族-普理妮.蒙哈榭
011蒙哈榭家族的另類子弟-夏商‧蒙哈榭紅酒
012魚蝦我所欲也-搭配海鮮不二選擇的拉羅史酒莊一級園莎布里白酒
013秋風乍起薄酒萊 -喬治‧杜寶夫酒莊之薄酒萊新酒
014布根地粉紅酒—格厚斯兄妹園粉紅酒
015嗅覺調配的藝術—波爾多梅多區拉蘭昆堡
016波爾多老式頂級酒的代表—瑪歌區的普利爾.立欣酒堡
017小天使帶來的欣悅-柏美洛的圖能旺酒
018盡展右岸聖特美濃區的風采—多明尼克堡
019強將手下無弱兵—看寇斯酒莊之二軍酒「寶塔」大展雄風
020還我平民本色—無憂堡的「布爾喬亞級」美酒
021波爾多的「萬朵紅梅一樹白」—卡本尼堡的干白酒
022法國式的甜蜜-吉荷酒莊的索甸甜白酒
023力抗「派克魔咒」的隆多克區野馬—多瑪‧卡薩克酒莊
024德裔法籍的阿爾薩斯麗斯玲-葡萄溪酒莊
025阿爾薩斯的香水—雨格酒莊的慶典級香特拉民酒
026隆河的隱士之酒-安內酒莊的賀米達己紅酒「塔拉貝園」
027隆河的賀米達己白酒—塔都‧羅蘭酒莊
028細釀美酒報主恩—佩高酒莊的教皇新堡酒
029老樹蟬聲我意馳—蟬鳴酒莊的教皇新堡白酒
030桃花顏色亦千秋-普羅旺斯的佩漢酒莊粉紅酒
031法國版本的紹興酒—朱哈區的羅勒酒莊黃酒
032美酒王國的遺忘角落—朱哈的礦石酒
033法國後花園的綠葉-羅瓦爾河的桑希酒
034法國後花園的繽紛紅花—甜白酒聖手的波瑪酒莊
035我飲到了星星—侯德樂的無年份香檳
036粉紅色的人生—高聖粉紅香檳
037「錦上何妨再添花」?-羅吉德家族釀製香檳酒的震撼
038文藝復興的聯想—利卡索里男爵酒莊的經典香蒂酒
039翡冷翠品味的唯一選擇-卡薩諾瓦酒莊的夢塔希諾酒
040老幹著新枝-托斯卡納的法國風
041義大利皮孟地的「小家碧玉」—可樂利歌酒莊的巴貝拉酒
042義大利阿爾卑斯山下的「酒后」-巴巴勒斯可酒
043義大利的王者之酒—李那迪.菲理酒莊的巴洛洛酒
044愛情之鄉酒更濃-貴里尼.理沙帝酒莊的阿馬龍酒
045義大利美酒世界的大小金釵-莎維與瓦倫提里酒莊的阿布若白酒
046義大利的歡樂之源-普羅西可氣泡酒
047義大利的雙色跳躍精靈-倫巴迪的紅白氣泡酒
048達成「財富、希望與榮耀」三願望-歌雅酒莊的「第二白」羅西莎
049義大利的浪漫色彩:貝昂第.山第酒莊的粉紅酒
050義大利的「甜蜜人生」-聖酒
051豔陽天下好風光-南義與西西里島的美酒
052窖中無歲月-西班牙利斯卡侯爵園的老派里歐哈酒
053 春風吹進里歐哈—慕佳酒莊的新派酒
054 西班牙黃金酒區的黃金酒莊-費南德茲酒莊之珍藏斗羅酒
055西班牙酒的「新貴階級」-鳥巢酒莊的克里歐酒
056莫道素顏無嬌色-西班牙「鼴鼠園」白酒的千變萬化
057聖誕歌聲飄酒香-西班牙的雪莉酒「東印度」
058西班牙的「甜蜜山中傳奇」-馬拉加的甜白酒
059西班牙的珠玉泡沫-黎卡雷多酒莊的「特別珍藏級」卡華氣泡酒
060葡萄牙的新潮酒-斗羅河的美歐河谷酒莊
061試試葡萄牙釀酒人的「足下功夫」-都摩洛酒莊
062笑傲歲月,唯我波特-葛拉漢10年陳波特酒
063斗羅好漢-葡萄牙酒振興的新組合?
064將麗斯玲葡萄發揮的鬼斧神工的伊貢‧米勒酒莊優質酒
065德國釀酒工藝的牛刀小試-普綠酒莊的「私房酒」
066酒神的惡作劇-遲摘酒誕生地的約翰尼斯山酒堡
067標準的德國「手工嚴選」-弗里茲‧哈格酒莊的精選級葡萄酒
068「瓊漿玉液」的真滋味-鄧厚夫酒莊的「金頸級」葡萄酒
069寒冷冰霜等閒之-冰酒的「三國演義」
070化腐朽為神奇-德國寶霉酒
071書如佳酒不宜甜-德國羅伯‧威爾酒莊的麗斯玲干白
072德國文豪歌德的愛酒—八百年歷史的卡斯特酒莊之法蘭根酒
073萬白叢中一點紅-德國的紅酒
074奧地利維也納森林的精靈-綠維特林葡萄酒與文學巨擘的「沈淪之酒」
-赫曼.赫塞與紅維特林酒
075奧地利的寶霉酒魔術大師-克拉赫與歐匹茲
076血性漢子的血性酒-匈牙利的公牛之血
077「寶黴酒祖國」的再起-匈牙利珮佐酒莊的「5桶級」拓凱酒
078美國精緻酒文化的拓荒者-格吉斯山酒莊
079美國神秘的紅酒-利吉酒莊的金芬黛
080「皮諾爸爸」的傳奇—奧瑞岡艾瑞酒莊的黑皮諾
081開創加州莎當妮新氣象的-牛頓酒莊之「未過濾莎當妮」
082加州天外有藍天-華盛頓州北星酒莊的美洛酒
083史朗貝克酒莊之氣泡酒-美國想要挑戰法國香檳的第一選擇
084澳洲的驕傲—雅拉耶林酒莊的「山下」希拉酒
085澳洲的黑皮諾的先驅—冷泉山酒莊的黑皮諾
086 欲與希拉爭豔的澳洲赤霞珠-飛鷹酒莊的赤霞珠
087試一試葡萄酒大師下海的手藝—蕭‧史密斯酒莊的M3莎當妮
088德國後裔釀製的澳洲麗斯玲-漢謝克酒莊的麗斯玲干白
089百年老藤、笑看春花秋月-澳洲巴羅莎谷的聖哈雷特酒莊
090「美得冒泡」澳洲豔紅氣泡酒-盧‧米蘭達酒莊的百年希拉氣泡酒
091紐西蘭的「當家姑娘」-霧灣酒莊的「蒂蔻蔻」白蘇維濃
092「天涯海角」的葡萄園-紐西蘭阿塔蘭基黑皮諾
093美酒新世界的代表-智利夢特斯酒莊的「紫天使」
094南國多嬌麗-智利赤霞珠的驚豔
095乍光初現的智利陽光-阿基坦尼亞酒莊的莎當妮「陽光中的陽光」
096充滿探戈韻律的美酒-薩巴塔酒莊的「高園」
097安地斯山的小百合-阿根廷美麗的莎當妮「路卡」
098「百年孤獨」的完結篇-南非酒業復興的徵兆
099長伴英雄末日時-拿破崙與南非的「康斯坦斯之酒」
100史瓦特藍的好漢-南非酒改革先鋒
001天、地、人的完美結合—布根地杜卡匹酒莊村莊酒
002鐵娘子的堅持-樂花酒園的紅花與白花
003飲中增德—布根地波恩及夜坡濟貧醫院酒
004拼酒、而不拼命的—布根地品酒騎士團
005產自黑皮諾葡萄酒麥加聖地的沃恩.羅曼尼村莊酒
006想起「屠龍勇士」-飛復來酒莊「聖喬治之夜」
007香柏‧木西尼—布根地的貴族品味
008英雄已死、英雄不死—拿破崙鍾情的日芙萊.香柏罈
009布根地的「杏花村白酒」-傑‧莫尼爾酒莊的村莊級白酒「騎士」
010白酒小貴族-普理妮.蒙哈榭
011蒙哈榭家族的另類子弟-夏商‧蒙哈榭紅酒
012魚蝦我所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