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驥先生,學貫中西,潛心文史,且講學海外多年,深得科學方法之秘,撰成《唐代政教史》。其書,網羅事蹟,窮竟事理,並自抒所得,當不讓陳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論》專美於前矣。
本書且以大唐政教激勵國人,以裨益當今之世,堪以傳世而為人所重。
本書特色
1.本書詳論有唐一代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史事。
2.本書為治史者必備史料。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唐代政教史(全1 冊)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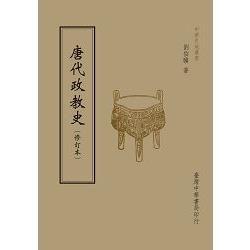 |
唐代政教史(全1 冊) 作者:劉伯驥 出版社: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512 |
人文歷史 |
$ 551 |
科學科普 |
$ 583 |
中文書 |
$ 583 |
隋唐五代史 |
$ 583 |
中國歷史 |
$ 583 |
社會人文 |
$ 583 |
中國歷史 |
$ 583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唐代政教史(全1 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劉伯驥﹐清光緒三十四年生(西元1908年)﹐廣東臺山人。
1937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系﹐曾任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教務主任﹐《廣州日報》主筆。抗日戰爭期間赴美國留學﹐獲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專攻歷史﹐選爲美國教育學榮譽生會會員﹐獲紐約中美聯誼會文學獎。
劉先生學識宏富﹐傾心文史﹑埋首著作﹐主要作品有《廣東書院制度》﹑《春秋會盟政治》﹑《中西文化交通小史》﹑《唐代政教史》﹑《宋代政教史》﹑《六藝通論》等。
劉伯驥﹐清光緒三十四年生(西元1908年)﹐廣東臺山人。
1937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系﹐曾任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教務主任﹐《廣州日報》主筆。抗日戰爭期間赴美國留學﹐獲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專攻歷史﹐選爲美國教育學榮譽生會會員﹐獲紐約中美聯誼會文學獎。
劉先生學識宏富﹐傾心文史﹑埋首著作﹐主要作品有《廣東書院制度》﹑《春秋會盟政治》﹑《中西文化交通小史》﹑《唐代政教史》﹑《宋代政教史》﹑《六藝通論》等。
目錄
黃序
何序
導言
上篇 唐代社會概觀
第一章 政治變革
一、武功開基創業
二、貞觀之政風與治績
三、武韋專政
四、開元之勤政與盛治
五、安史之亂
六、藩鎮之禍
七、元和中興
八、宦官與朋黨之禍
九、大中暫治
十、黃巢之亂
十一、唐室之瓦解與覆亡
第二章 經濟生活
一、糧價與民食政策
二、土地改革
三、租庸調制度
四、兩稅法
五、通貨
六、各種雜稅
七、戶口之增減
第三章 社會風俗
一、京都風物
二、服飾
三、飲食居室
四、婚喪禮制
五、風流韻事
六、嗜好與娛樂
中篇 唐代教育內容
第一章 學校組織與編制
一、中央官學
二、地方教育
三、私人講學與讀書
四、學校行政與管理
五、圖籍與圖書館
六、釋奠─訓導之象徵
第二章 貢擧考試制度
一、官吏銓選制
二、貢擧制
三、貢擧人數
四、考試與放榜
五、貢擧習俗
六、主考官
七、舞弊與懲處
八、貢擧之評論
第三章 教育家與教育理論
一、教育家
二、婦女教育
三、家庭教育
第四章 學藝
一、文學
二、經學
三、史學
四、地理
五、法律
六、書法
七、圖畫
八、音樂
九、醫學
十、曆算
下篇 唐代文化教育之影響
第一章 對宋元明清之影響
一、學校與貢擧
二、各種學藝
第二章 對日本之影響
一、奈良朝
二、平安朝
第三章 對高麗之影響
一、百濟與高句麗
二、新羅
結論
一、建國之特徵
二、教育與貢擧之評價
三、外來思想之接受
四、唐代與羅馬比較
五、對中國文化之貢獻
附插圖一 唐高祖立像
圖二 唐太宗立像
圖三 魏徵像
圖四 房玄齡像
圖五 杜如晦像
圖六 唐太宗納諫圖
圖七 閻立本職貢圖
圖八 則天武后像
圖九 安史之亂用兵路線圖
圖十 郭子儀像
圖十一 陝西馬嵬楊貴妃廟
圖十二 唐代通貨之銅錢
圖十三 長安城圖
圖十四 唐人文會圖
圖十五 唐人春郊遊騎圖
圖十六 韓愈像
圖十七 開成石經
圖十八 唐太宗溫泉銘
圖十九 唐玄宗鶺鴒頌
圖二十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圖二十一 歐陽詢化度寺碑
圖二十二 褚遂良倪寬贊
圖二十四 孫過庭書譜序
圖二十五 張旭肚痛帖
圖二十六 釋懷素自敘帖
圖二十七 顏真卿祭姪帖
圖二十八 徐浩不空和尚碑
何序
導言
上篇 唐代社會概觀
第一章 政治變革
一、武功開基創業
二、貞觀之政風與治績
三、武韋專政
四、開元之勤政與盛治
五、安史之亂
六、藩鎮之禍
七、元和中興
八、宦官與朋黨之禍
九、大中暫治
十、黃巢之亂
十一、唐室之瓦解與覆亡
第二章 經濟生活
一、糧價與民食政策
二、土地改革
三、租庸調制度
四、兩稅法
五、通貨
六、各種雜稅
七、戶口之增減
第三章 社會風俗
一、京都風物
二、服飾
三、飲食居室
四、婚喪禮制
五、風流韻事
六、嗜好與娛樂
中篇 唐代教育內容
第一章 學校組織與編制
一、中央官學
二、地方教育
三、私人講學與讀書
四、學校行政與管理
五、圖籍與圖書館
六、釋奠─訓導之象徵
第二章 貢擧考試制度
一、官吏銓選制
二、貢擧制
三、貢擧人數
四、考試與放榜
五、貢擧習俗
六、主考官
七、舞弊與懲處
八、貢擧之評論
第三章 教育家與教育理論
一、教育家
二、婦女教育
三、家庭教育
第四章 學藝
一、文學
二、經學
三、史學
四、地理
五、法律
六、書法
七、圖畫
八、音樂
九、醫學
十、曆算
下篇 唐代文化教育之影響
第一章 對宋元明清之影響
一、學校與貢擧
二、各種學藝
第二章 對日本之影響
一、奈良朝
二、平安朝
第三章 對高麗之影響
一、百濟與高句麗
二、新羅
結論
一、建國之特徵
二、教育與貢擧之評價
三、外來思想之接受
四、唐代與羅馬比較
五、對中國文化之貢獻
附插圖一 唐高祖立像
圖二 唐太宗立像
圖三 魏徵像
圖四 房玄齡像
圖五 杜如晦像
圖六 唐太宗納諫圖
圖七 閻立本職貢圖
圖八 則天武后像
圖九 安史之亂用兵路線圖
圖十 郭子儀像
圖十一 陝西馬嵬楊貴妃廟
圖十二 唐代通貨之銅錢
圖十三 長安城圖
圖十四 唐人文會圖
圖十五 唐人春郊遊騎圖
圖十六 韓愈像
圖十七 開成石經
圖十八 唐太宗溫泉銘
圖十九 唐玄宗鶺鴒頌
圖二十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圖二十一 歐陽詢化度寺碑
圖二十二 褚遂良倪寬贊
圖二十四 孫過庭書譜序
圖二十五 張旭肚痛帖
圖二十六 釋懷素自敘帖
圖二十七 顏真卿祭姪帖
圖二十八 徐浩不空和尚碑
序
推薦序
黃序
抗戰初期,文山與劉石濤先生初遇於廣州,承以所著《廣東書院制度沿革》見示,展而讀之,覺其對嶺南文獻,如數家珍,欣忭不能自己,當即為修函請王雲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石濤來美,好精研教育學及史學,今且逾十年,又以所著而在台灣出版之《中西文化交通小史》見寄,山見其對六朝隋唐各代間東西交通發展與文化接觸之經過,捃摭遺言,旁證衍引,作系統之敘述,至其搜討之博,條貫之密,求諸東西並世作者之林,實罕其儔。石濤淵淵以思,嘗致函於山,謂我國介紹西方近代文化已亙五、六十年,仿歐效美,或則主全盤西化,雖然採用,多不免張冠李戴,削足適履;或則高談本位文化,而獨對大唐昔日聲教之隆,不唯不繼往開來,發揚蹈厲,抑且數典忘祖,失所依據。石濤既慨乎言之,乃窮數年之力,發奮著《唐代政教史》,書既竣,徵序於文山。山憶二十年前在美讀書,稍稍治中國文化史,其時對英史家韋爾斯(H. G. Wells)初版之《世界史綱》,卓識新見,讚佩莫名。其書對唐代文化之隆,最所重視,認為第七、八世紀中國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國家,其時歐洲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捍盜的堡壘中,正苦於宗教桎梏的黑暗,而中國人民生活已進到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境。中國船隻同時已在海上航行,海外貿易,極為發達。中國人在六世紀時亦已知利用火藥、用煤,此殆較歐洲早進數百年,而橋樑建築,水利工程尤為進步。歐洲人直到一千年後的十六、七世紀,發現了美洲,乃至印刷書籍及教育之廣播,現代科學的發明,然後敢相信自己超邁中國而上之。韋爾斯指出中國文化以唐為最偉大,實可比隆羅馬而未遑多遜之後,嘗進一步追問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時期中,占有領導地位,顧何已轉至現代,不能在文化上、政治上之配世界?世界現代科學之發達,有賴於系統的記錄,合作研究的組織,顧中國學人對此獨多忽略,而純正科學卒不揚,又何故?山對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二十年來始終未能忘懷,國內學人如錢賓四(穆)、羅元一(香林)、嚴耕望等對於唐代文化之偉大,均能在韋爾斯之後,闡揚盡致,但迄今尚未有作精詳之列舉,比較之說明,功能之分析與綜合之研究,今石濤獨能從事於此,將唐代文化之全貌,通盤托出,而對於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亦作直接間接之解答,名言絡繹,故山認是書不僅為學院式之探索而已,而實亦可為光復華夏與建設中國文化呈獻一寶典。
且文山對於石濤的唐代文化研究,認為可以提出若干根本假定,為之評量:
一、 史學最高之理想,在乎對過去事變,作想像上的重建,重建的歷程,在決定上則為科學的,而在表現上則為藝術的。石濤根據科學方法,分析唐代文化,確能達到相當的客觀性,而在藝術的表現上,華實並茂,生氣盎然。過此種重建後,吾人乃深知唐代確能完成一創古未有之大國家,在政府組織上,以中書門下三省制,確立內閣的行政系統,以租庸調制,奠定全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以府兵制,建立健全的武裝,以貢擧治,甄拔人才,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全社會的平民教育。在法律上,《六典》唐律,完成有組織有秩序的社會。至於唐人之詩文、藝術、宗教、哲學、工業,在唐代盛況下孕育出來,凝造成偉大而勻稱的文化體系,經石濤一一指出後,真可稱「經天緯地,震爍古今」。石濤認為自秦漢以來,一切文化質素,至唐實為大綜合,開啟宋元明清四朝之大機運,誠非虛語。亦惟如是,而大唐文化之全貌,乃畢呈於讀者之前,史家之能事,始告成功。
二、 史象因果,素稱複雜,莊生所謂變動不居。中國文化入唐以後,早已由門第社會變為科舉社會,舉凡宗教、文學、藝術、理學、經濟、工業以及一切生活思想,都在變遷,由貴族門第轉而落到群眾之手,儼然成為簇新的文化體系。顧此種文化體系何以在中古時代突興,其因素究出諸物理,抑出諸生物?究出諸心理抑為純文化的表現?曩者傅孟真(斯年)為韋爾斯著《世界史綱》作說明時,則列舉中國自由文化,古典主義,北方勇氣與新血輪之輸入為創造唐代新文化之主要因素。石濤對此一問題之解釋,則異乎是,而謂「唐代文化之發達,實由於唐代文化自己有固定之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之傳入,如非排拒,則為吸收者,揚精棄粕,引為己用,外來文化之傳入,始能咀嚼而消化之。」對於外來文化之接受,則謂「西方宗教及文化思想之傳入,如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祆教、摩尼教,流行無禁,遍於中國。」又謂「儒家政治為治國之準繩,行成一種精神文化體系,由此種文化體系所孕育陶鑄之人物類型,為國家政治社會之領袖。」「全國民性,由唐代聲靈,範鑄為一。」此種看法,實與山多年來在文化學上所主張之文化決定論互相發明。誠以唐代文化為一複雜而勻稱之體系,其變遷原因,蓋出於體系本身,恍如有機體之內在的作用,不斷發生系列的內在變遷,結果不但改變環境,且改變體系自身,而體系的命運,不啻為體系本身內在潛能之次第開展。外在的力量雖然影響文化的構成,但不能根本改變體系的內在潛能及其常態命運。故文化一方對人類的文化行為既有決定的力量,而其自身亦是自己決定的,外在的因素,對於文化體系之影響,所以不是永恆的;體系之愈勻稱、愈合理、愈統整者,其自制之力愈大。唐代文物制度之璀璨,誠如石濤所謂「睥睨秦漢,而示範宋明」,其發生之歷程,似不能求諸地理環境,種族血輪,或經濟條件,而仍應求諸文化因素本身。
三、一種文化體系進至燦爛極盛以後,必漸趨沒落,此殆為史家及文化學者所周知的事實。唐代,經初唐、盛唐、中唐以後,轉入晚唐便造成大時代之沒落,其原因安在?法國漢學家馬伯樂(Maspero)嘗謂中國在八世紀末葉,地主階級僅占全人口百分之五,農民因賦稅繁重,兵役頻數,強迫徵工,債臺高築,乃至一變而為農業的無產階級。格魯思(Grousset)繼起,亦以七八一年至七八三年左右,全國商業頻於破產,長安為印度、波斯與中國貿易交通之起點與終點,至是亦一蹶不振。此種舞臺,乃為導演革命之先聲,黃巢為當時富有活力之知識份子,屢擧進士不第,結果乃發動及組織一空前之農民革命,不數年而襲沂州,過淮南,略襄邑、雍邱。從宣州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趨建州,陷桂管,進寇廣州,會大疫北還。自桂沿湘下衡水,破潭州(長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轉掠江西,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東都,攻潼關,陷京師,群臣迎謁灞上。巢從騎士數十萬,國號大齊。唐以沙陀之援,巢不敵,敗而東,眾猶十萬,東入徐袞,先後七年而亡,而時代遂向另一方趨近,唐代亦至是而中斬,不復保其殘壘。此種解釋,大抵偏於經濟的。石濤異是,曾列擧當時閹豎擅權,藩鎮作亂,黨爭頻仍,流寇作亂,為唐代傾覆之要因。總之,唐經百餘年之昇平,百餘年治亂相乘,卒至魚爛鳥散,吾人從文化學上作比較之決定,相信文化歷程之重演,故無可能,而有一定的限度,其原因在此。故唐代文化之沒落,謂為受文化的有限可能性所限制,誰謂不然?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四、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
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一)一民族的文化,在文化領域上的活動,從數千年歷史觀察,絕不止一次,反過來看,卻可達到二次、三次以上。中國文化,在唐以前之商、周、秦、漢及以後之宋、元、明、清,其文化體系之輝煌,仍為全世界所重視,但均不及唐之恢宏而偉大,凝
(二)成最大的綜合。此種事實,證明斯賓格拉(Spengler)及唐比(Toynbee)所謂每種文化只有一次的真正「艷花怒放」,雖非盡確,亦不無正當根據。
(三)一切偉大的文明,其創造成果,不只顯見諸一個特殊領域,例如印度之於宗教,希臘之於美術,而可以顯見諸多方的領域。試尋繹唐代政教史,便可證明當時的政治、法律、教育、美術、宗教輯哲學思想均有偉大的創造。
(四)然而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當然不會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唐代對於各種文化領域,雖然創詣達於顛點,形成奇造之局,但對於科學的創造力,則薄弱以致不能張其軍。
(五)文化的創造力不會是永恆的,而必然是變動不居,有時如春花艷放,如驚濤拍岸,有時則又如落葉草枯,機運全變。大唐一代文化在粗枝大葉上,可劃分為初唐、中唐、晚唐各階段,便可概見。
(六)整個文化體系的綿遠,必比次文化體系的生命線延長得多。大唐整個文化體系幾達三百年,而法律、兵制、經濟制度等次文化體系之生命,則未及三百年而趨於崩潰。
(七)文化變遷及創造,絕不如馬克思派之所設想,謂物質文化(技術、經濟、生產工具)的創變,必比非物質文化早。在唐代文化的歷程中,總可看出民族文化的創造,首先見諸政治、軍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學,後來然後有工藝(印刷術、茶、糖、陶器)之發達。
(八)由唐代文化的發達,可證明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皆為累積的,而一種新的文化價值,經本民族或集團創造以後,往往可以分播到其他民族或集團。所謂一波纔起萬波隨,唐代法律集秦、漢之大成而加以改進,其影響可以比美羅馬法,曾廣被日本、朝鮮、安南、高昌、于闐、契丹、蒙古,實非偶然。其次,李翱復性論之興起,慧能禪宗之創造,經宋儒攝取其要義,而別創新儒學之理學後,不特支配千餘年的思想界,而且激發歐洲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德國觀念論的哲學,海波盪漾,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均受其影響。至考試制度之被近世英、法、美等國之採取,更為有目共睹之事實。
(九)文化現象在各該領域上之創造,例如政治、法律、教育、藝術、哲學、宗教、文學、戲劇、倫理等,皆互相聯繫,凝成整個的統合的勻稱的文化體系。吾人從唐代文化的輪廓上,總可窺見其調和性、連繫性、交光互涉,不能分離。文化在空間上之分播,有如時間上之傳遞,有其同樣的重要性。因為如此,所以文化分播的歷程,輒引至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與外來質素混合,凝成一致的體系。人類學上所說「刺激的分播」,尤為簇新的文化模式產生之因素。唐代文化模式之創新,一方固然出自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而外來文化之激發固有莫大之助力。天寶盛時,首都人口殆二百萬,殊方民族如猶太人、希臘人、波斯人、韃旦人、敘利亞人、回紇人、突厥人、印度人、日本人、高麗人等皆奔赴來歸,其所輸進之文化質素,模式複雜而眾多,自可推見。至玄奘游印,傳入唯識學,影響整個的文化宗教思想,迄今未替,更無論矣。
以上為文山讀《唐代政教史》所推論而獲知之諸種文化法則。最後文化當切國情而不能無所依據,文山雖亦隨石濤先生而有所覺悟,在抗戰時期且曾以創造民族文化相呼號,然而時至二十世紀的原子時代,誠如英史家唐比所云,吾人由過去偉大的歷史建樹,因而恍然於創造歷史時,吾人實已超過自己的歷史,進而為世界治序之建立,為人類聯合開新路。吾人今日一方向回顧過去,一方瞻望歐美,因而對於過去與現在均有更客觀更圓滿的瞭解,自不能不轉像實證的價值與更新的觀念往前追求,則石濤先生熱情所注,暢談唐代文化,既可為建立現代國家與民族文化楷模,且亦可據以進一步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為世界和平奠永久的基礎。文山讀先生書,循誦再三,附加一言,為新時代祈禱。至先生本書之發明尚多,不一一詳擧,當世君子不難於原著得之。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黃文山於紐約新學院
何序
造史難,造通史尤難,其難,在科學方法之運用耳。其方法為何?分析與綜合是也。法國史學家朗格洛埃(Charles V. Langlois)與塞諾布(Charles Seignobos)二氏著《史學緒論》一書,於歷史科學之方法,獨具創見,發前人所未發,今之治史學者造通史者,多推重之。吾友劉伯驥先生,學淹中西,潛心文史,撰《唐代政教史》,將以問世。余受而讀之,其書,網羅事蹟,窮原竟委,博取精裁,自抒新得,洵為不刊之典,當不讓陳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論》專美於前矣。有識之士,作一書,桓數十年而後定稿,始足以傳世而為人所重。劉先生講學海外,積多年之功,深得科學方法之秘,凡數易稿而書乃成。其用心之審,致力之勤,有如是者!且以大唐政教激勵國人,有裨世道,寧淺鮮哉!故樂為之序,以介紹於讀者。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何聯奎序於臺北
黃序
抗戰初期,文山與劉石濤先生初遇於廣州,承以所著《廣東書院制度沿革》見示,展而讀之,覺其對嶺南文獻,如數家珍,欣忭不能自己,當即為修函請王雲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石濤來美,好精研教育學及史學,今且逾十年,又以所著而在台灣出版之《中西文化交通小史》見寄,山見其對六朝隋唐各代間東西交通發展與文化接觸之經過,捃摭遺言,旁證衍引,作系統之敘述,至其搜討之博,條貫之密,求諸東西並世作者之林,實罕其儔。石濤淵淵以思,嘗致函於山,謂我國介紹西方近代文化已亙五、六十年,仿歐效美,或則主全盤西化,雖然採用,多不免張冠李戴,削足適履;或則高談本位文化,而獨對大唐昔日聲教之隆,不唯不繼往開來,發揚蹈厲,抑且數典忘祖,失所依據。石濤既慨乎言之,乃窮數年之力,發奮著《唐代政教史》,書既竣,徵序於文山。山憶二十年前在美讀書,稍稍治中國文化史,其時對英史家韋爾斯(H. G. Wells)初版之《世界史綱》,卓識新見,讚佩莫名。其書對唐代文化之隆,最所重視,認為第七、八世紀中國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國家,其時歐洲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捍盜的堡壘中,正苦於宗教桎梏的黑暗,而中國人民生活已進到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境。中國船隻同時已在海上航行,海外貿易,極為發達。中國人在六世紀時亦已知利用火藥、用煤,此殆較歐洲早進數百年,而橋樑建築,水利工程尤為進步。歐洲人直到一千年後的十六、七世紀,發現了美洲,乃至印刷書籍及教育之廣播,現代科學的發明,然後敢相信自己超邁中國而上之。韋爾斯指出中國文化以唐為最偉大,實可比隆羅馬而未遑多遜之後,嘗進一步追問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時期中,占有領導地位,顧何已轉至現代,不能在文化上、政治上之配世界?世界現代科學之發達,有賴於系統的記錄,合作研究的組織,顧中國學人對此獨多忽略,而純正科學卒不揚,又何故?山對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二十年來始終未能忘懷,國內學人如錢賓四(穆)、羅元一(香林)、嚴耕望等對於唐代文化之偉大,均能在韋爾斯之後,闡揚盡致,但迄今尚未有作精詳之列舉,比較之說明,功能之分析與綜合之研究,今石濤獨能從事於此,將唐代文化之全貌,通盤托出,而對於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亦作直接間接之解答,名言絡繹,故山認是書不僅為學院式之探索而已,而實亦可為光復華夏與建設中國文化呈獻一寶典。
且文山對於石濤的唐代文化研究,認為可以提出若干根本假定,為之評量:
一、 史學最高之理想,在乎對過去事變,作想像上的重建,重建的歷程,在決定上則為科學的,而在表現上則為藝術的。石濤根據科學方法,分析唐代文化,確能達到相當的客觀性,而在藝術的表現上,華實並茂,生氣盎然。過此種重建後,吾人乃深知唐代確能完成一創古未有之大國家,在政府組織上,以中書門下三省制,確立內閣的行政系統,以租庸調制,奠定全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以府兵制,建立健全的武裝,以貢擧治,甄拔人才,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全社會的平民教育。在法律上,《六典》唐律,完成有組織有秩序的社會。至於唐人之詩文、藝術、宗教、哲學、工業,在唐代盛況下孕育出來,凝造成偉大而勻稱的文化體系,經石濤一一指出後,真可稱「經天緯地,震爍古今」。石濤認為自秦漢以來,一切文化質素,至唐實為大綜合,開啟宋元明清四朝之大機運,誠非虛語。亦惟如是,而大唐文化之全貌,乃畢呈於讀者之前,史家之能事,始告成功。
二、 史象因果,素稱複雜,莊生所謂變動不居。中國文化入唐以後,早已由門第社會變為科舉社會,舉凡宗教、文學、藝術、理學、經濟、工業以及一切生活思想,都在變遷,由貴族門第轉而落到群眾之手,儼然成為簇新的文化體系。顧此種文化體系何以在中古時代突興,其因素究出諸物理,抑出諸生物?究出諸心理抑為純文化的表現?曩者傅孟真(斯年)為韋爾斯著《世界史綱》作說明時,則列舉中國自由文化,古典主義,北方勇氣與新血輪之輸入為創造唐代新文化之主要因素。石濤對此一問題之解釋,則異乎是,而謂「唐代文化之發達,實由於唐代文化自己有固定之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之傳入,如非排拒,則為吸收者,揚精棄粕,引為己用,外來文化之傳入,始能咀嚼而消化之。」對於外來文化之接受,則謂「西方宗教及文化思想之傳入,如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祆教、摩尼教,流行無禁,遍於中國。」又謂「儒家政治為治國之準繩,行成一種精神文化體系,由此種文化體系所孕育陶鑄之人物類型,為國家政治社會之領袖。」「全國民性,由唐代聲靈,範鑄為一。」此種看法,實與山多年來在文化學上所主張之文化決定論互相發明。誠以唐代文化為一複雜而勻稱之體系,其變遷原因,蓋出於體系本身,恍如有機體之內在的作用,不斷發生系列的內在變遷,結果不但改變環境,且改變體系自身,而體系的命運,不啻為體系本身內在潛能之次第開展。外在的力量雖然影響文化的構成,但不能根本改變體系的內在潛能及其常態命運。故文化一方對人類的文化行為既有決定的力量,而其自身亦是自己決定的,外在的因素,對於文化體系之影響,所以不是永恆的;體系之愈勻稱、愈合理、愈統整者,其自制之力愈大。唐代文物制度之璀璨,誠如石濤所謂「睥睨秦漢,而示範宋明」,其發生之歷程,似不能求諸地理環境,種族血輪,或經濟條件,而仍應求諸文化因素本身。
三、一種文化體系進至燦爛極盛以後,必漸趨沒落,此殆為史家及文化學者所周知的事實。唐代,經初唐、盛唐、中唐以後,轉入晚唐便造成大時代之沒落,其原因安在?法國漢學家馬伯樂(Maspero)嘗謂中國在八世紀末葉,地主階級僅占全人口百分之五,農民因賦稅繁重,兵役頻數,強迫徵工,債臺高築,乃至一變而為農業的無產階級。格魯思(Grousset)繼起,亦以七八一年至七八三年左右,全國商業頻於破產,長安為印度、波斯與中國貿易交通之起點與終點,至是亦一蹶不振。此種舞臺,乃為導演革命之先聲,黃巢為當時富有活力之知識份子,屢擧進士不第,結果乃發動及組織一空前之農民革命,不數年而襲沂州,過淮南,略襄邑、雍邱。從宣州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趨建州,陷桂管,進寇廣州,會大疫北還。自桂沿湘下衡水,破潭州(長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轉掠江西,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東都,攻潼關,陷京師,群臣迎謁灞上。巢從騎士數十萬,國號大齊。唐以沙陀之援,巢不敵,敗而東,眾猶十萬,東入徐袞,先後七年而亡,而時代遂向另一方趨近,唐代亦至是而中斬,不復保其殘壘。此種解釋,大抵偏於經濟的。石濤異是,曾列擧當時閹豎擅權,藩鎮作亂,黨爭頻仍,流寇作亂,為唐代傾覆之要因。總之,唐經百餘年之昇平,百餘年治亂相乘,卒至魚爛鳥散,吾人從文化學上作比較之決定,相信文化歷程之重演,故無可能,而有一定的限度,其原因在此。故唐代文化之沒落,謂為受文化的有限可能性所限制,誰謂不然?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四、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
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一)一民族的文化,在文化領域上的活動,從數千年歷史觀察,絕不止一次,反過來看,卻可達到二次、三次以上。中國文化,在唐以前之商、周、秦、漢及以後之宋、元、明、清,其文化體系之輝煌,仍為全世界所重視,但均不及唐之恢宏而偉大,凝
(二)成最大的綜合。此種事實,證明斯賓格拉(Spengler)及唐比(Toynbee)所謂每種文化只有一次的真正「艷花怒放」,雖非盡確,亦不無正當根據。
(三)一切偉大的文明,其創造成果,不只顯見諸一個特殊領域,例如印度之於宗教,希臘之於美術,而可以顯見諸多方的領域。試尋繹唐代政教史,便可證明當時的政治、法律、教育、美術、宗教輯哲學思想均有偉大的創造。
(四)然而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當然不會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唐代對於各種文化領域,雖然創詣達於顛點,形成奇造之局,但對於科學的創造力,則薄弱以致不能張其軍。
(五)文化的創造力不會是永恆的,而必然是變動不居,有時如春花艷放,如驚濤拍岸,有時則又如落葉草枯,機運全變。大唐一代文化在粗枝大葉上,可劃分為初唐、中唐、晚唐各階段,便可概見。
(六)整個文化體系的綿遠,必比次文化體系的生命線延長得多。大唐整個文化體系幾達三百年,而法律、兵制、經濟制度等次文化體系之生命,則未及三百年而趨於崩潰。
(七)文化變遷及創造,絕不如馬克思派之所設想,謂物質文化(技術、經濟、生產工具)的創變,必比非物質文化早。在唐代文化的歷程中,總可看出民族文化的創造,首先見諸政治、軍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學,後來然後有工藝(印刷術、茶、糖、陶器)之發達。
(八)由唐代文化的發達,可證明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皆為累積的,而一種新的文化價值,經本民族或集團創造以後,往往可以分播到其他民族或集團。所謂一波纔起萬波隨,唐代法律集秦、漢之大成而加以改進,其影響可以比美羅馬法,曾廣被日本、朝鮮、安南、高昌、于闐、契丹、蒙古,實非偶然。其次,李翱復性論之興起,慧能禪宗之創造,經宋儒攝取其要義,而別創新儒學之理學後,不特支配千餘年的思想界,而且激發歐洲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德國觀念論的哲學,海波盪漾,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均受其影響。至考試制度之被近世英、法、美等國之採取,更為有目共睹之事實。
(九)文化現象在各該領域上之創造,例如政治、法律、教育、藝術、哲學、宗教、文學、戲劇、倫理等,皆互相聯繫,凝成整個的統合的勻稱的文化體系。吾人從唐代文化的輪廓上,總可窺見其調和性、連繫性、交光互涉,不能分離。文化在空間上之分播,有如時間上之傳遞,有其同樣的重要性。因為如此,所以文化分播的歷程,輒引至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與外來質素混合,凝成一致的體系。人類學上所說「刺激的分播」,尤為簇新的文化模式產生之因素。唐代文化模式之創新,一方固然出自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而外來文化之激發固有莫大之助力。天寶盛時,首都人口殆二百萬,殊方民族如猶太人、希臘人、波斯人、韃旦人、敘利亞人、回紇人、突厥人、印度人、日本人、高麗人等皆奔赴來歸,其所輸進之文化質素,模式複雜而眾多,自可推見。至玄奘游印,傳入唯識學,影響整個的文化宗教思想,迄今未替,更無論矣。
以上為文山讀《唐代政教史》所推論而獲知之諸種文化法則。最後文化當切國情而不能無所依據,文山雖亦隨石濤先生而有所覺悟,在抗戰時期且曾以創造民族文化相呼號,然而時至二十世紀的原子時代,誠如英史家唐比所云,吾人由過去偉大的歷史建樹,因而恍然於創造歷史時,吾人實已超過自己的歷史,進而為世界治序之建立,為人類聯合開新路。吾人今日一方向回顧過去,一方瞻望歐美,因而對於過去與現在均有更客觀更圓滿的瞭解,自不能不轉像實證的價值與更新的觀念往前追求,則石濤先生熱情所注,暢談唐代文化,既可為建立現代國家與民族文化楷模,且亦可據以進一步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為世界和平奠永久的基礎。文山讀先生書,循誦再三,附加一言,為新時代祈禱。至先生本書之發明尚多,不一一詳擧,當世君子不難於原著得之。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黃文山於紐約新學院
何序
造史難,造通史尤難,其難,在科學方法之運用耳。其方法為何?分析與綜合是也。法國史學家朗格洛埃(Charles V. Langlois)與塞諾布(Charles Seignobos)二氏著《史學緒論》一書,於歷史科學之方法,獨具創見,發前人所未發,今之治史學者造通史者,多推重之。吾友劉伯驥先生,學淹中西,潛心文史,撰《唐代政教史》,將以問世。余受而讀之,其書,網羅事蹟,窮原竟委,博取精裁,自抒新得,洵為不刊之典,當不讓陳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論》專美於前矣。有識之士,作一書,桓數十年而後定稿,始足以傳世而為人所重。劉先生講學海外,積多年之功,深得科學方法之秘,凡數易稿而書乃成。其用心之審,致力之勤,有如是者!且以大唐政教激勵國人,有裨世道,寧淺鮮哉!故樂為之序,以介紹於讀者。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何聯奎序於臺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