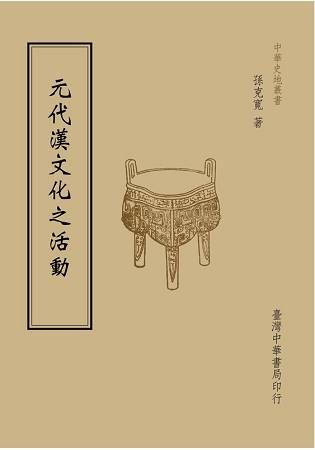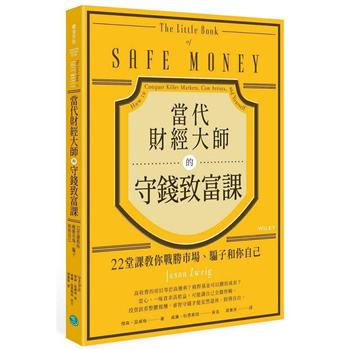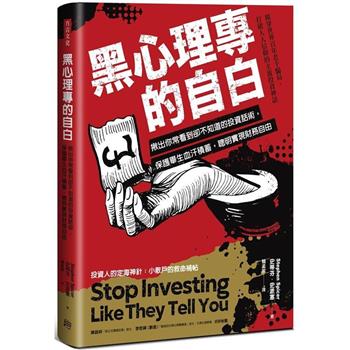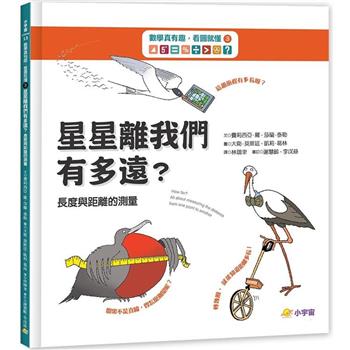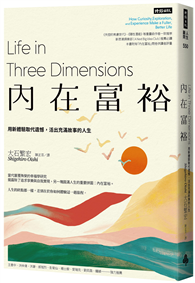元朝一代,蒙古鐵騎橫掃歐亞,中華文化實應瀕臨毀滅,卻日益昌盛,所謂何故?誠為世人所欲知。孫先生以其深諳宋遼金元歷史,乃以漢軍、儒士之漢文化為中心,旁搜宋金元人文集,而作是書,堪為史學界之盛事。
本書特色
1.本書為元代文化史,並詳論漢文化對元朝的深刻影響。
2.是書為治史者必備史料。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全一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42 |
宋元史 |
$ 731 |
中文書 |
$ 732 |
宋元史 |
$ 732 |
中國歷史 |
$ 732 |
中國歷史 |
$ 73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全一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孫克寬先生(1905-1993)
為孫立人將軍姪子,早年學法,熟諳古典詩詞。來臺以後,隱於教職。1955年東海大學創立,因戴君仁先生之邀,前來任教古典詩詞。1972年退休,前往加拿大,仍研究不輟。孫先生研究著重在元代史﹑宋元道教﹑詩學三大領域。
孫克寬先生(1905-1993)
為孫立人將軍姪子,早年學法,熟諳古典詩詞。來臺以後,隱於教職。1955年東海大學創立,因戴君仁先生之邀,前來任教古典詩詞。1972年退休,前往加拿大,仍研究不輟。孫先生研究著重在元代史﹑宋元道教﹑詩學三大領域。
目錄
藍文徵先生序言
自序
第一編 背景
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
附 金將武仙本末考
第二編 儒學
元初儒學
一、元初東平興學考
二、元初儒學之淵源
三、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
第三編 漢軍
元代漢軍人物表
元代漢軍三世家考
一、永清史氏本末
二、張柔行實考
三、槀城董氏本末
附(一)元王橶使宋事補
(二)忽必烈時代南中國人民之反抗
第四編 儒生與其著作
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附 程鉅夫與其雪樓集
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
附 滋溪集文槀別記
元許有壬與其至正集
元集題記
(一)劉秉中之藏春集
(二)郝經之陵川集
(三)王惲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四)魏初之青崖集
(五)趙孟頫之松雪齋集
(六)虞集之道園學古錄
(七)
附錄 晚宋劉克莊研究兩種
(一)劉後村之家世與交遊
(二)晚宋政爭中之劉後村
自序
第一編 背景
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
附 金將武仙本末考
第二編 儒學
元初儒學
一、元初東平興學考
二、元初儒學之淵源
三、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
第三編 漢軍
元代漢軍人物表
元代漢軍三世家考
一、永清史氏本末
二、張柔行實考
三、槀城董氏本末
附(一)元王橶使宋事補
(二)忽必烈時代南中國人民之反抗
第四編 儒生與其著作
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附 程鉅夫與其雪樓集
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
附 滋溪集文槀別記
元許有壬與其至正集
元集題記
(一)劉秉中之藏春集
(二)郝經之陵川集
(三)王惲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四)魏初之青崖集
(五)趙孟頫之松雪齋集
(六)虞集之道園學古錄
(七)
附錄 晚宋劉克莊研究兩種
(一)劉後村之家世與交遊
(二)晚宋政爭中之劉後村
序
自序
當我於三十八年一月間,來到南臺灣的屏東市。在那綠樹蔥蘢,蕉風椰雨之間,恢復了讀書生活,才不幾時的翻天覆地的大動撼,仍然搖晃我的心靈,不斷地有一個思念在腦海衝擊,就是「今後的中華民族與他那深固不易的文化形態,如何在這已到來的大變亂中支持下去?」由今想到古,只好向歷史中求解答。於是我重讀通鑑與畢氏的續通鑑,對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幾次大患難的過程,重加檢視:五胡入侵之永嘉之亂,女真侵華的靖康之亡,一直到崖山之覆的蒙古入主中原。這每一次的大變亂,都不止於國家的瓦解,人民喪亂流離,而且更嚴重的是漢文化的面臨毀滅。可是永嘉亂後,中原士族南遷,禮樂衣冠萃於江左,留在北方的還「用夏變夷」;北朝元魏還盡用漢法,以促進後來隋唐大一統的文化合流,爆出貞觀開元的儒治與文明。靖康之亂,南宋形成了東晉的再翻版,留在北方的文儒,弼佐完顏氏,出現了大定明昌間彬彬儒雅的盛況。而蒙元一代呢?初進長城,勢如疾風暴雨,血洗華北大平原;卻被幾位俘係身分的老儒,談笑嗟嘆之間,使鐵騎止戈,武夫下拜,又出現了中統至元──延祐至順間的儒治局面。這真是不可言說的奇妙!當然要歸功於中華文化的感染力與韌性精神,與中國儒生的「不變塞」、「強哉矯」的剛毅之力。
於此沉酣史籍之中,我不覺地被金元時代一些俠士們、將軍們、黃冠道士們,乃至寬衣博帶的儒士詩人們的「保種存文」的偉大事蹟而吸引住了。於是我向南宋金元間史實從頭研討。我在宋史叛臣李全傳中,發現了金元之際南北紛爭中那些草莽英雄,以孤臣孽子的心情,為漢民族效命。於是我著手寫了「南宋金元山東忠義軍的李全」一文。從這個民兵集團,進而向全元史找尋貞祐崩潰後的那些起陸龍蛇──金末九公,東平嚴實,和河朔史張,這些傳記一一跳入我的腦際;更因讀詩的關係而飽讀元遺山集,發現了這位詩人而兼史家的那樣孜孜不息地游說諸侯,保存文化,招集散亡的文士,向新朝推毂,與另一位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朝野配合,保全氣息緜緜的儒學與文章。於是我寫了一篇東平興學考,來表彰這位漢軍大帥的苦心;更進而探索元使儒臣各傳,而鉤勒出一篇元代儒學的淵源一文;又無意間從宋末人筆記與元人文集中發現正一教士與南宋儒生的因緣,而寫成「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這樣就寫成我第一冊這方面的著作──元初儒學。賴朋友們的推薦而獲得臺灣教育廳四十二年度著作獎助,也因此誘發了我對蒙元時代漢文化活動的研究興趣。四十三年,從屏東移硯臺北,在擾攘市廛裡,奔波不定的生活中,我依然寫了一冊「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打算透視當時蒙古人在歐亞的取勝之道,或有助於今日世勢。以上是我前期的研究過程。
四十四年東海大學成立,我被戴靜山先生延攬在中文系教書,把興趣與時間擘一大半給中國詩方面。生活雖然安定,心情雖然開朗,研究的環境雖然便利,可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卻成了業餘,玩票的性質。十四年來,始終未逾這一課題,閱讀範圍窄狹,而見聞又淺露,以視並時的元史同道們的成就,簡直無法比擬。可是畢竟得有大學當局的鼓勵,與哈佛燕京社的支持,利用研究的補助,仍能寫成了若干篇文章。這幾年又轉注力於元代道教問題,才把元代漢軍,儒學與道教的共同趨向──傳衍漢文化,凝結為一個概念;斷斷續續地寫成研究論著,有的印成專書,如「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宋元道教之發展」;有的寫成專題論文,如「元代漢軍三世家考」……,去年下季,我發狠把一些印成的小冊與已發表的論文編輯在一起,裒然成帙,題名為「元代漢文化之活動」。更承孔達先生推介中華書局,慨允印行,使多年來的苦心致力的作品,呈獻於讀者之前。回首當年,驚濤駭浪般憂惶惴惴的心情,實不禁感慨係之!
關於蒙古人入侵對漢文化的死亡威脅,與中國人苦心奮鬥,屈己徇道的精神,書中各篇,皆有闡說,此處不擬複論。只是我這十幾年來獨學冥行的研究,所以稍有所知者,實在不能不感謝臺灣大學史學教授姚從吾先生,不斷地指示,檢給參考書籍,而他那一不朽的著作──東北史論叢,給予我的幫助、啟示,實在是我的良師與指導者,在這裡我要向他衷心地致謝。
以我的譾陋,加之雜事旁鶩,書中各篇的幼稚、疏陋,勢必所在皆是還望同道與讀者,匡正、原諒。
舒城孫克寬自序
五十七年四月六日於中臺大度山園
當我於三十八年一月間,來到南臺灣的屏東市。在那綠樹蔥蘢,蕉風椰雨之間,恢復了讀書生活,才不幾時的翻天覆地的大動撼,仍然搖晃我的心靈,不斷地有一個思念在腦海衝擊,就是「今後的中華民族與他那深固不易的文化形態,如何在這已到來的大變亂中支持下去?」由今想到古,只好向歷史中求解答。於是我重讀通鑑與畢氏的續通鑑,對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幾次大患難的過程,重加檢視:五胡入侵之永嘉之亂,女真侵華的靖康之亡,一直到崖山之覆的蒙古入主中原。這每一次的大變亂,都不止於國家的瓦解,人民喪亂流離,而且更嚴重的是漢文化的面臨毀滅。可是永嘉亂後,中原士族南遷,禮樂衣冠萃於江左,留在北方的還「用夏變夷」;北朝元魏還盡用漢法,以促進後來隋唐大一統的文化合流,爆出貞觀開元的儒治與文明。靖康之亂,南宋形成了東晉的再翻版,留在北方的文儒,弼佐完顏氏,出現了大定明昌間彬彬儒雅的盛況。而蒙元一代呢?初進長城,勢如疾風暴雨,血洗華北大平原;卻被幾位俘係身分的老儒,談笑嗟嘆之間,使鐵騎止戈,武夫下拜,又出現了中統至元──延祐至順間的儒治局面。這真是不可言說的奇妙!當然要歸功於中華文化的感染力與韌性精神,與中國儒生的「不變塞」、「強哉矯」的剛毅之力。
於此沉酣史籍之中,我不覺地被金元時代一些俠士們、將軍們、黃冠道士們,乃至寬衣博帶的儒士詩人們的「保種存文」的偉大事蹟而吸引住了。於是我向南宋金元間史實從頭研討。我在宋史叛臣李全傳中,發現了金元之際南北紛爭中那些草莽英雄,以孤臣孽子的心情,為漢民族效命。於是我著手寫了「南宋金元山東忠義軍的李全」一文。從這個民兵集團,進而向全元史找尋貞祐崩潰後的那些起陸龍蛇──金末九公,東平嚴實,和河朔史張,這些傳記一一跳入我的腦際;更因讀詩的關係而飽讀元遺山集,發現了這位詩人而兼史家的那樣孜孜不息地游說諸侯,保存文化,招集散亡的文士,向新朝推毂,與另一位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朝野配合,保全氣息緜緜的儒學與文章。於是我寫了一篇東平興學考,來表彰這位漢軍大帥的苦心;更進而探索元使儒臣各傳,而鉤勒出一篇元代儒學的淵源一文;又無意間從宋末人筆記與元人文集中發現正一教士與南宋儒生的因緣,而寫成「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這樣就寫成我第一冊這方面的著作──元初儒學。賴朋友們的推薦而獲得臺灣教育廳四十二年度著作獎助,也因此誘發了我對蒙元時代漢文化活動的研究興趣。四十三年,從屏東移硯臺北,在擾攘市廛裡,奔波不定的生活中,我依然寫了一冊「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打算透視當時蒙古人在歐亞的取勝之道,或有助於今日世勢。以上是我前期的研究過程。
四十四年東海大學成立,我被戴靜山先生延攬在中文系教書,把興趣與時間擘一大半給中國詩方面。生活雖然安定,心情雖然開朗,研究的環境雖然便利,可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卻成了業餘,玩票的性質。十四年來,始終未逾這一課題,閱讀範圍窄狹,而見聞又淺露,以視並時的元史同道們的成就,簡直無法比擬。可是畢竟得有大學當局的鼓勵,與哈佛燕京社的支持,利用研究的補助,仍能寫成了若干篇文章。這幾年又轉注力於元代道教問題,才把元代漢軍,儒學與道教的共同趨向──傳衍漢文化,凝結為一個概念;斷斷續續地寫成研究論著,有的印成專書,如「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宋元道教之發展」;有的寫成專題論文,如「元代漢軍三世家考」……,去年下季,我發狠把一些印成的小冊與已發表的論文編輯在一起,裒然成帙,題名為「元代漢文化之活動」。更承孔達先生推介中華書局,慨允印行,使多年來的苦心致力的作品,呈獻於讀者之前。回首當年,驚濤駭浪般憂惶惴惴的心情,實不禁感慨係之!
關於蒙古人入侵對漢文化的死亡威脅,與中國人苦心奮鬥,屈己徇道的精神,書中各篇,皆有闡說,此處不擬複論。只是我這十幾年來獨學冥行的研究,所以稍有所知者,實在不能不感謝臺灣大學史學教授姚從吾先生,不斷地指示,檢給參考書籍,而他那一不朽的著作──東北史論叢,給予我的幫助、啟示,實在是我的良師與指導者,在這裡我要向他衷心地致謝。
以我的譾陋,加之雜事旁鶩,書中各篇的幼稚、疏陋,勢必所在皆是還望同道與讀者,匡正、原諒。
舒城孫克寬自序
五十七年四月六日於中臺大度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