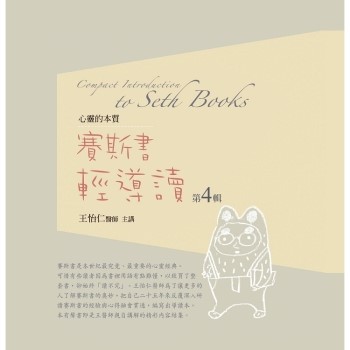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老子要義》前編闡明老子思想內涵;後編為周紹賢教授書法手稿,總述《道德經》每章大意,並逐句解釋之。本書收錄周紹賢教授自序,闡述其著作本書之思想緣起。
本書特色
《老子要義》前編闡明老子思想內涵;後編為周紹賢教授書法手稿,總述《道德經》每章大意,並逐句解釋之。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老子要義(全一冊)的圖書 |
 |
老子要義(全一冊) 作者:周紹賢 出版社: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1-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0 |
中國哲學 |
$ 270 |
中國/東方哲學 |
$ 270 |
道家思想 |
$ 270 |
社會人文 |
$ 270 |
中國哲學 |
$ 270 |
Social Sciences |
$ 270 |
哲學 |
$ 32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老子要義(全一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紹賢教授(1908-1993)
童年師從晚清進士楊玉相,讀五經,習詩文。1933年,就讀於梁漱溟創辦的鄉村建設學院。1949年秋赴臺灣,曾任東吳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教授,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著有《魏晉清談述論》、《道家與神仙》、《老子要義》、《莊子要義》、《孔孟要義》、《荀子要義》、《佛教概論》、《中國文學述論》、《論李杜詩》、《漢代哲學》、《先秦兵家要旨》、《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文言與白話》、《應用文》、《松華軒詩稿》等。
周紹賢教授(1908-1993)
童年師從晚清進士楊玉相,讀五經,習詩文。1933年,就讀於梁漱溟創辦的鄉村建設學院。1949年秋赴臺灣,曾任東吳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教授,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著有《魏晉清談述論》、《道家與神仙》、《老子要義》、《莊子要義》、《孔孟要義》、《荀子要義》、《佛教概論》、《中國文學述論》、《論李杜詩》、《漢代哲學》、《先秦兵家要旨》、《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文言與白話》、《應用文》、《松華軒詩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