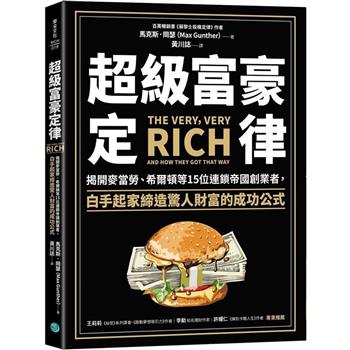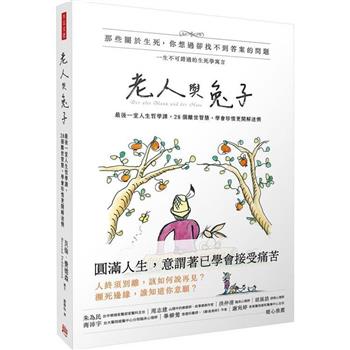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廖宏霖是很獨特的詩人,在浮躁的年代中,他的作品異常安靜與平和,在感情上包容,在爭執中退讓,在喧嘩中靜默。要能夠進入他作品的世界,要善於聆聽,聆聽鏡子碎裂、淚水滴落、火光照亮、牆壁裡的死者音、灰燼的聲音,乃至無聲之聲。他不自覺地營造出的詩意境界,值得期待,《谿山琴況》中形容藝術「中和」的狀態是:「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則音與意合,莫知其然而然矣。要之神閒氣靜,藹然醉心,太和鼓鬯,心手自知。」期待宏霖持續堅持自身的個性,以詩安定這個時代。」──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須文蔚
「透過這些詩,我好像又能輕易回到那個迷惘危疑、卻又透徹明白的生活狀態。黑夜剛剛過去,眼前就是七星潭,風景的線條乾淨簡單,可望而不可及,砂礫與卵石的觸感那麼真實,我們試著形容,然而海深難以想像。」──詩人林達陽
「在這本收錄橫跨十七年作品的集子裡,宏霖一貫溫柔舒緩的語調,作為表象,承載著『其後』的婉曲流動。所謂『其後』,即在愛之後、不愛之後、離去之後,一切的開端之後。詩人寧可令既有的『鄉愁』虛位化,甚至在抽象層次上亦然,從而保有抒情的詰難。」──藝術工作者馬思源
名人推薦:「廖宏霖是很獨特的詩人,在浮躁的年代中,他的作品異常安靜與平和,在感情上包容,在爭執中退讓,在喧嘩中靜默。要能夠進入他作品的世界,要善於聆聽,聆聽鏡子碎裂、淚水滴落、火光照亮、牆壁裡的死者音、灰燼的聲音,乃至無聲之聲。他不自覺地營造出的詩意境界,值得期待,《谿山琴況》中形容藝術「中和」的狀態是:「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則音與意合,莫知其然而然矣。要之神閒氣靜,藹然醉心,太和鼓鬯,心手自知。」期待宏霖持續堅持自身的個性,以詩安定這個時代。」──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須文蔚
「透過這些詩,我...
章節試閱
身為動詞
──給所有為了說話而沉默的人
我們穿越「穿越」這個詞
從後排站起來
我們解散「解散」這個詞
把可以被盤查的一切全部交出去
我們攜帶「攜帶」這個詞
這是唯一可以被留下的證物
我們給出「給出」這個詞
如同編寫一封永遠失效的遺囑
我們不是要磨平言語的鋸齒
而是要讓它吻合某種理想的角度
為了轉動而不是肢解發聲的器官
為了鬆開而不是拴緊想像的瓶子
身為動詞
我們從來不是被困住
而是被「困住」困住
身為動詞
表達就是一種理解
------------------------------
那些細節都走了
“A moose has come out of the impenetrable wood / and stands there, looms, rather, /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 Elizabeth Bishop ‘The Moose’
遠方的樹守護著我們的湖
當夜都走遠了,光也不在眼的背後駐足
死亡在霧的邊緣逡巡
我像一隻從遠方逃走的麋鹿
留下透明的足印在夢的雪地上
如果回憶是一個廣場任人自由來去
然而我願意相信光影和那些被經過的風景
我知道相信是因為忘記
因為忽略了所有把戲的細節
我像小孩專心看著魔術師那般地相信
當廣場的鐘聲敲響一個又一個不眠的夢
鴿群傳遞著恐慌的心情從地面飛向屋頂
牠們談論古怪的天氣、談論昨夜未竟的暴雨
我也知道風吹過時牠們將不再談論風
因為它總是一種過時的東西
而只要我們擁有視力
方向感就會是一件不曾存在過的經驗
彷彿烈日下誰撐起一把透明的傘
被日光遮蔽的眼全都張開
我以為我可以在光的盡頭隱身而去,然而我不行
所以我追問風中的細節
但四周寂然彷彿天地頷首無語
也像是魔術師擺一擺手讓自己墜落消失在舞台的後方
帶走場內所有藏匿好的聲響
留下靜默代表某種信念的成型
你說那些細節都走了
連同風和專心的孩童在清晨的廣場
凝結於傾斜的鐘樓響起一朵如詩般的雨雲
而剩餘的那些話語
神祇也無法說出的字彙全都寫在水面上
我說那些細節都走了
像是正午藏匿在腳下的影子一再試圖走出的詩句
夢境無限延長,只有睡著的人才能夠拾回的細節
醒來之後成為一場不曾發生的革命
廣場上我們遇見此生的第一隻麋鹿
世界靜止像是被熄滅的燈光
彷彿黑暗的舞台上只有我們
等待著這場一無所有的戲
身為動詞
──給所有為了說話而沉默的人
我們穿越「穿越」這個詞
從後排站起來
我們解散「解散」這個詞
把可以被盤查的一切全部交出去
我們攜帶「攜帶」這個詞
這是唯一可以被留下的證物
我們給出「給出」這個詞
如同編寫一封永遠失效的遺囑
我們不是要磨平言語的鋸齒
而是要讓它吻合某種理想的角度
為了轉動而不是肢解發聲的器官
為了鬆開而不是拴緊想像的瓶子
身為動詞
我們從來不是被困住
而是被「困住」困住
身為動詞
表達就是一種理解
------------------------------
那些細節都走了
“A moose has come out o...
推薦序
以布洛卡的吟唱化詩
◎印卡
現代詩歌經驗常常被談到的是精神超越〈transcendence〉,這在世俗經驗出格的詩歌傳統,在台灣的接收史中,也可找到一些例證,例如玄學詩、或是在臺灣今日依舊流行的里爾克、狄金生的詩歌。現代詩歌常常透個一些非理性或是精神性的提升超越感官,並在詩歌中留下了痕跡。狄金生的詩句,「靈魂選擇她自己的社群」許多讀者並不陌生,這樣的秘密是現代詩歌的一條潛流。義大利文學研究學者保羅〈Paolo Valesio〉曾分析過義大利現代詩歌與神祕主義的關係,他提到一種理想主義存在於藝大利的現代詩歌之中,這種理想主義在於重思人與群體之間的理想狀況。這種像是宗教香膏一般的概念在義大利現代詩歌實踐中招喚,取代了安那其的思考,讓義大利的詩歌在左派關懷下形成了一種對抗非人化〈dehumanizing〉的可能。如果保羅的說法或多或少解釋了義大利詩歌在未來主義後,詩歌情境對前一波文學運動的修補,當代哲學家阿岡本處於這樣的詩歌環境中,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重思生命政治的來源是從詩歌開始。
廖宏霖在《ECHOLALIA》這本詩集中所試圖表達的語言觀點,讓我想起多年前,他研究所時期試圖從阿岡本的語言觀點討論著主體與聲音的關係。宏霖曾經如此說著:「『密談』」做為一種私密的、親暱的交談,可能同時也指涉了某種秘密的、難以宣說的言語經驗。」「密談」這個主題在臺灣詩歌中,不難讓人想到夏宇的影響,然而除卻這層次的聯想,從密談出發的語言經驗,受限於極少數的對象,這種親密的溝通方式形成了這本詩集的主調。密談這種主、客體近距離的接觸所產生的倫理姿態,由輕聲與傾聽所結合最趨近無聲的交流與超越,在這本詩集中產生了極誘人的魅力。相較阿岡本《幼年與歷史》一書中提及的語言實驗,談的則是如何從生命的具體經驗去創造語言,揭開了重思人類本身面對災厄與暴力,改變自身的可能性。《ECHOLALIA》不是什麼實驗性強烈的作品,但試圖將讀者與作者的關係封鎖成為一種自我語言誕生的過程,待人如我,就如同〈邊界日記〉描述語言溝通的難處──
於是說話的人被加上了引號
彷彿被困在一個透明的箱子裡
言語僅僅成為某種看見與被看見的姿態
如同我們搬演著亙久的戲碼
在序幕之前遺棄自己真實的名與姓
忘記將近嫻熟的台詞
與一個陌生人相遇
成為他,成為引號外的引號
成為一句拗口的話
重複地說與被說在燈光熄滅之前
這些演練不光是安置語言本身,也是安置語言本身背後的生命政治。語言中的他者如何被理解,首先來自於此種演練。
在《ECHOLALIA》這本詩集中,共收錄二十首詩歌,並以「與你密談」、「與文法密談」、「與我(們)密談」三個主題分類。語言主體、語言文法跟語言溝通的主題中,《ECHOLALIA》一開始就把詩人藏在布洛卡區(Broca’s area)。在神經科學中,有著鏡像神經元的假說。在這個假說中,布洛卡區形成了理解他人的行為、意圖和情緒的可能位置。同時,以人類語言行為來說,運動性語言中樞也位於此腦部區域,一旦損傷,便會罹患布洛卡失語症,只能發出不成文法的短句。也正因為如此,這詩集中的第一首詩〈你要靜靜地等待〉,到最後一首詩〈人的樣子〉把語言的思想推向了生命的現實。
把語言作為透明的,連續的像是高原上強風往復的聲響,音樂性做為殘餘、遺跡在這本詩集中不斷地被提醒。廖宏霖描述與詩人海子一同想像末世與死,這首編列於「與你密談」中的詩歌,〈我請求在早上你碰見埋我的人〉如此說著:「走進詩裡彷彿深夜的海有人無聲躍進/而全部的絕望被迎面而來的速度衝撞成/全部隱喻……」語聲浪頭的幅度上,在速度、形狀、強度與方向全面粉碎的瞬間,詩人到底獲得百科全書般的知識或者是退卻呢?這首詩中,廖宏霖透過了華語詩歌的浪漫主義表達了他文學傳統的接受,而海子自身浪漫主義對於時代的獻身,一方面是語言的無效卻又是允諾的美好。
也彷彿我們的時代是個沒有神的末世。唯有個人在偶然中作下的每個決定可以作為救贖。我們可以在語言中找到所有的開放性,做出自己的決定。在這本詩集中每個矛盾修辭都是對此的提醒。
這本詩集可以說極盡地掩飾真正的慾望與認同。詩人在鏡像神經元的喻象中用詩歌描述語言與同情、共感之密切關係,無論使用「我」或是「你」的人稱,就像情詩所膨大的果實仍舊保留了花柱、子房……等等所有細節,讀者可以從中發現一種抒情節奏的現身。因為充滿情感的詩歌中存在著許多遲疑,彷彿在宏大的意指中躊躇著,例如〈(愛的)靜物〉,愛在這首詩中詩人不斷想掩藏,但靜物(stillness)又與死亡如此貼近。生與死的張力,在這本詩集中是難以得知的前世、腦中的fMRI顯影,是編織的語言一條最開始的線頭,在人生各種劇碼下,最後如同〈同義詞〉最後停在「而死亡的同義詞是死亡」。死亡消滅語言主體被置於優位,也再次提醒生命與語言的關係。
詩集的密談,讀者不妨就把它當作一種作者對愛的獻禮、愛的認識。「你和我說不出的話語將會是圖像上/想像力怎樣也填補不了的一處裂縫」一種全然無法由感官理解的狀態,詩在宏霖的筆下成為一場又一場的事件〈ereignis〉,原初的真理,是〈安娜〉詩中的鑰匙,是詩集中遊蕩於布洛卡區的肉身知識。這些事件關於詩的生成,跨越世界界線的經驗,若以宗教哲學學者奧托〈Rudolf Otto〉曾經用das Numinose來說明,這一類精神性的狀態,就像是透過智性的透鏡看見了不同凡俗的視域。比如〈支離疏〉在這裡,將一切的矛盾傾軋於詩行中,也是這本詩集中最隱晦,如同精神的火焰闡述燃燒的闡述再一次超越自身,讓它形成一種動力。詩歌中自我的受困,看似讓語言受難,卻幾近接近愛,邁向溝通,產生了一種倫理可見的面貌。
但《ECHOLALIA》並不存在頻繁燃燒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看見」。如〈那些細節都走了〉提及了「只要我們擁有視力/方向感就會是一件不曾存在過的經驗/彷彿烈日下誰撐起一把透明的傘/被日光遮蔽的眼全都張開/我以為我可以在光的盡頭隱身而去,然而我不行」,這本詩集中高度地出現光線的隱喻,它暗示著價值的估算,看見看不見的,如人類神秘的第三眼或是慧眼(enlightened eyes)朝向了開放的詩歌。人類不可避免的末世即使存在著,也只是存在於語言。我們可以讀到〈安娜〉的困境在於□□,每刻懸而未決的目的地。一扇又一扇需要被打開的十道門,直到通達了語言所不能描述的真理,放棄不只是僅僅作為語言,而是作為生命破碎顯影的迴聲。
《ECHOLALIA》的詩稿增增刪刪數次,其中直接指涉真實世界的詩〈人的樣子〉,是一首寫給大埔張藥房老闆張森文先生的詩。阿岡本從詩歌出發試圖再一次說出詩歌見證的不可能,歐洲納粹屠殺所帶來的傷口除了倖存者沒有人可以判斷其效力。也許這首詩也是如此。這首詩以棄置人的概念完成了人。
有些人倒下只是為了
被重新目睹成
一個
人
的樣子
而在這一首詩最後的一個詩段、這本詩集的最後一個詩段,讀者再次被扔到了死亡面前,「人」,在這本詩集少數幾首描述社會事件的詩中,用阿岡本的說法,這個場景又被完整地交付於凝視的矛盾中。如同梅杜莎一般的社會,將一切視為犯罪的證物所產生的漠異,是這本詩集最後的控訴。但也留下在詩歌傳統中一再被追問的問題,我們是否還有著一種對語言的天真,重新討論一種生命的理想,進一步從密談中更進一步產生公共領域的可能?這是對於創作者、讀者的提問。燃燒彼此語言的火是否可以產生持續不斷的光明?在我們悲哀望向時代時,正常的世界何時歸來?
以布洛卡的吟唱化詩
◎印卡
現代詩歌經驗常常被談到的是精神超越〈transcendence〉,這在世俗經驗出格的詩歌傳統,在台灣的接收史中,也可找到一些例證,例如玄學詩、或是在臺灣今日依舊流行的里爾克、狄金生的詩歌。現代詩歌常常透個一些非理性或是精神性的提升超越感官,並在詩歌中留下了痕跡。狄金生的詩句,「靈魂選擇她自己的社群」許多讀者並不陌生,這樣的秘密是現代詩歌的一條潛流。義大利文學研究學者保羅〈Paolo Valesio〉曾分析過義大利現代詩歌與神祕主義的關係,他提到一種理想主義存在於藝大利的現代詩歌之中,這種理想主...
作者序
【為什麼要出版這本詩集呢?】
之前在不同的公開或非公開的場合裡被問到這個最令我懼怕的問題,我想我可能只有前兩次(很誠實地)說了我不想說,不過生性怕尷尬,後面大概說了十次以上(像)謊言但又不全然是謊言的的東西。這也是這本詩集沒有作者序的原因,到底要向他人交代什麼呢?作者如生命的犯人,作品已是被自己嚴刑拷打過後的自白,句句不屬實的同時,卻又字字血淚。而真正的犯罪,追根究柢,其實都起源於全然無關或荒謬的動機。
【為什麼要出版這本詩集呢?】
之前在不同的公開或非公開的場合裡被問到這個最令我懼怕的問題,我想我可能只有前兩次(很誠實地)說了我不想說,不過生性怕尷尬,後面大概說了十次以上(像)謊言但又不全然是謊言的的東西。這也是這本詩集沒有作者序的原因,到底要向他人交代什麼呢?作者如生命的犯人,作品已是被自己嚴刑拷打過後的自白,句句不屬實的同時,卻又字字血淚。而真正的犯罪,追根究柢,其實都起源於全然無關或荒謬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