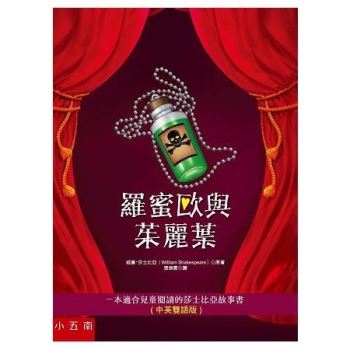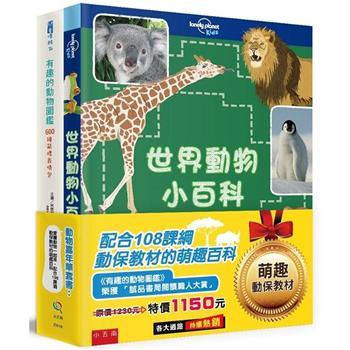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在流放地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29 |
二手中文書 |
$ 240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53 |
散文 |
$ 25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3 |
Social Sciences |
$ 288 |
中文書 |
$ 288 |
現代散文 |
$ 288 |
社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目睹父親在面前死去後的某一天,
她從高中輟學。
那一刻起,她進入了「這個世界」
駐留過在地圖上匿跡的無尾巷,體驗光怪陸離的地下秩序;
原住戶的死亡與暫時失蹤、永久消失在此從不引人竇疑;
她幫人做過半套賺錢也待過酒店,
從八大的內外兩邊窺探最赤裸殘酷的人性;
游移在藥國的邊陲,從毒品與它們屬民的身側,
見證一次次的垂危與毀滅;
她「被自願」的走進了精神病院,
藥物與精神的拉鋸,擺蕩於天才與癲狂的兩極……
——
底層勞工、性產業、毒販、精神病患,走過忽略社會規則的路途,張紹中囈語般的書寫風格,層層疊媾真實殘酷與瘋癲迷幻的兩相世界,重現非常社會的荒謬。
本書特色
★註異文庫年度百人試閱作品,評價兩極爭議之作!
★八年級生自傳式陰性書寫,「倖存者」絕不代言的自白!
★親身經歷第一手社會體察紀錄,直視外人難以親見的地下世界!
讀者好評
「我一直覺得紹中是位時空旅人,從我自己到達不了的時間那裡帶回重要的訊息。娼妓短短一章,卻是橫跨多年,從最早到和這個世界再無相見之間,數不清的彼時的摘要集結。
此時我們需要謹記序言提醒我們的,作者一貫的保留和過量的自我否定。我想大多數讀者都會同意,肉以外的東西當然不是假的(p. 183),這篇文章更遠非毫無意義。相反,它所乘載的意義恐怕是有寫出來的兩倍以上吧?有些片段作者告訴了我們實際所發生的細節,那麼那些沒有詳述的事件呢?有些例如社會資源的破口和資格,我們可以期待會和其他章節有所交會而被補足,像一張網的構成。可也有像網孔一樣,恐怕永遠不會化成文字的部分,像是「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之後 (p. 177)」,這些通往一萬次死亡的過程。
於是我要再次冒誤解作者的危險,批評序言的標題。回憶怎麼會不可能,逃避回憶反倒不可能。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安放回憶。
我想作者已經做得很好了。這個世界應當把她從漂浮的棺木撈起,仔細聽好她所要說和沒說的。」瑞士•Gnezd •化學家
「荒謬卻很有既視感,閱讀以後會因為共鳴而被救贖。是一本寫實而毫無底線的散文。」台北•cya•學生
「有在控訴什麼但世界還是長這個樣子的感覺太引人入勝了,沒有比這種文字更適合放逐魯蛇情緒的地方了。」沙鹿•毛毛太陽•學店生
「他寫這一切的筆法輕巧有如一個人看著一顆蘋果掉落——甚至輕巧勝於一個人看著一顆蘋果掉落;你覺得他在說 : 這一切只是稀鬆平常得要命的事;讓你幾乎要去懷疑這個世界上,終將不會有一個女子,能從性的外在侵犯與內在歡愉所產生的矛盾之下,健康、平安長大。」台南•潔•自由工作者
「初讀時以為是那種「身敗名裂」的小說,實際窺見的卻是一整個世界的沉淪與迸裂。作者以平淡而滲人的口吻,描寫出人類在墜與不墜間、有意與無意間的可能掙扎,以及活在地獄的眾生所齊力跳出的生之舞蹈。」木柵•藏心•學生
「在精神病院的遭遇很深刻,從遭遇衍伸的思考更是容易引起巨大共鳴,忍不住好奇究竟是怎樣的人,能夠對世界有這麼深、這麼精闢的感悟,是很讓人驚艷的作品。」景美•皿皿•學生
| |||
| |||
|
|


 2021/03/24
2021/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