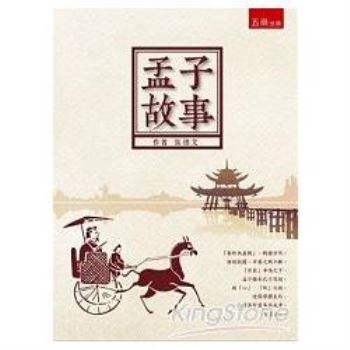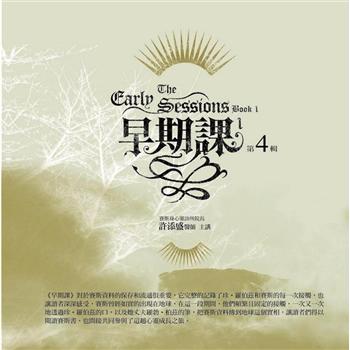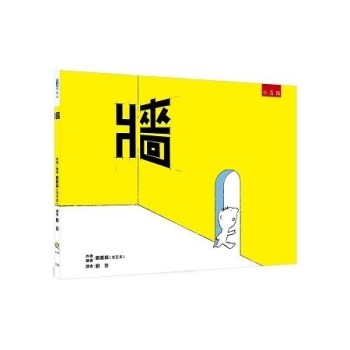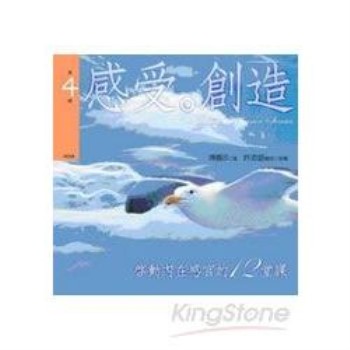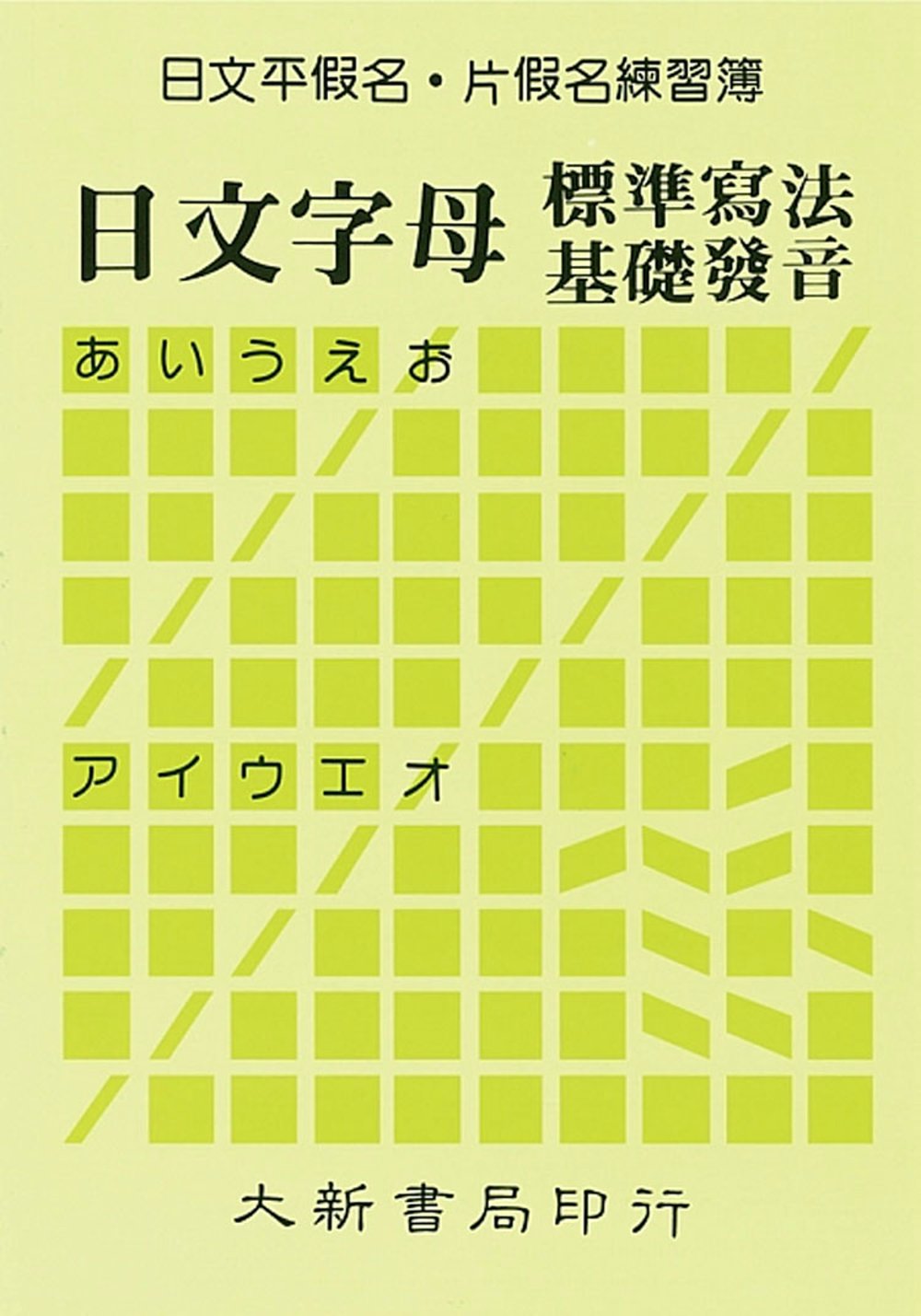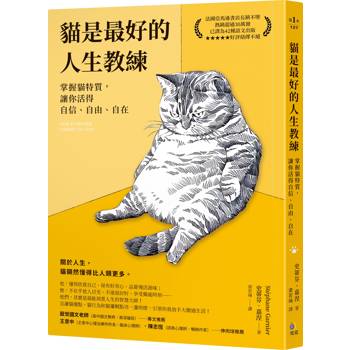第三章 台灣民眾黨
第六節 謝春木vs.台灣社會運動十年
1920年代是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的十年,期間文化政治論述與各團體/政黨組織的蓬勃發展,宛如我國春秋戰國,蔚為台灣近代史上不可抹滅的光輝十年。謝春木因本人經歷走過這十年的社會運動,在其敏銳的觀察下,有其精闢獨到的見解,可參見其所繪製的「近代社會運動系統圖」
政治宣傳vs.組織發展 在政治宣傳方面,自1921年7月16日創刊《臺灣青年》雜誌、1922年改名《臺灣》、1923年4月15日創刊《臺灣民報》半月刊雜誌、10月15日《臺灣民報》由半月刊進為旬刊。1924年6月停刊《臺灣》月刊雜誌。1925年7月12日《臺灣民報》由旬刊改為每逢星期日發行一次的週刊、同(1925)年8月《臺灣民報》突破一萬份。斯時,將近400萬的台灣人只有一家週報《臺灣民報》,但是不到20萬的日本人卻有三家日報和數家的週刊報。及至1930年3月29日《臺灣民報》才改為《臺灣新民報》,仍為週刊,直至1932年4月15日方始發行日刊 。這份臺灣本土知識菁英辦的報紙,代表日據時期1920年代十年社會運動的台灣島民政治論述。
至於組織發展,1921年10月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後,謝春木認為十年社會運動歷經三座山,1923年12月全島大逮捕的治警事件是社會運動十年史中築起的第一座山,越過此山,平坦的原野就展開在前,自然成行 。農民運動的興勃是十年史的第二座山 。「文化協會」的分裂是十年史的第三座山 。
在此期間,主要的是派別(派系)鬥爭,明瞭相互間的自我認識 ,在實際運動中分裂成各式政團/政黨,依左的順序排列有臺灣共產黨、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工友協助會、臺灣文化協會、臺灣工友總聯盟、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其間「臺灣民眾黨」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而且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永載史冊。
蔣渭水謙卑低下時 1927年2月10-11日,文協舊幹部聚集台中霧峰林獻堂宅,研議蔣渭水所提成立新政治團體及其所置總理、協理、幹事等職時,蔣渭水勸請林獻堂出任總理,林獻堂立即拒絕,告以「決不願再受總理之名,若欲以此相強,則與之絕交。」
就此際而言,突顯蔣渭水是何等低下謙卑,另一方面,林獻堂堅定反對出任新政治團體的總理,當然是瞭解這次「臺灣文化協會」分裂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他們這派太跋扈。試想,構思/創立/推動「臺灣文化協會」的是蔣渭水,初時拜訪尋求大老林獻堂的支持,結果雖然是眾人推舉林獻堂為具裁決一切會務之權的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還能出任專務理事(常務/執行理事),似尚可接受。
但兩年後改組,則總理是霧峰林家林獻堂、協理也是霧峰林家是林幼春、專務理事是其關係緊密/代理人的蔡培火,當初構思/創立/推動「臺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成了光桿理事,即霧峰林家分別佔據第一、第二把手的權力雙保險,專務理事又是堅定同派的蔡培火,霧峰林家將權力吃乾抹盡的一把抓,勢必引發有心者的不滿或無言抗議,故84名理事只有36名出席。
果其不然,「台灣文化協會」不惜分裂的關鍵在於組織,蔡培火提案是中央集權的總理制,總理對代議員會的決議有複決權、對理事會決議有否決權。最後,大會通過的決定方案,不設主席,只有中央委員長和各級委員 。也就是說,大會新通過的組織架構方案,完全否定了總理/協理獨裁制,林獻堂灰頭土臉,點滴在心頭,否則怎會堅持拒絕新政治團體的總理一職。
蔣渭水揮刀自宮/不設黨主席 及后1927年7月10日,「臺灣民眾黨」成立,黨中央不再設總理/協理二職,黨中央機關改為全島黨員大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 。9月16日該黨第一次中央委員會議決蔣渭水等中央委員20名、蔣渭水等中央常務委員14名、及彭華英等中央常務委員事務擔任者19名,居然完全没有林獻堂、林幼春、蔡培火 ,結果就是舊文協的三名領導被排除在外。接著11月6日的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因彭華英的提議推荐,決議林獻堂、林幼春、蔡式穀、蔡培火四人為「黨顧問」 。事情發展的結果,形同將舊文協領導林獻堂等架空排除於黨機器日常執行運作的核心隊伍。
整個事情始末,在「臺灣文化協會」大分裂的陰影權鬥下,新成立的「臺灣民眾黨,因林獻堂堅拒出任未來組黨后領導總理一職的情勢下,其運作結果,形同自宮,居然不敢設總理/黨主席職稱的領導職務,而以主幹者(負責人)代之。黨中央黨務運作機器設有總務、政務、財務、組織、社會、調查和宣傳等七個部門的主任,蔣渭水謙恭的只是中央七個部主任之一的財務主任;初始,謝春木係以主幹(負責人)提出組織「民眾黨」的申請,「民眾黨」成立時係中央常務委員事務擔任者任政務部主任 ,但旋於12月11日以《臺灣民報》社務多忙為由請辭,由蔡派的彭華英補主幹。但二十天后1928年1月1日元旦《臺灣民報》在報導「臺灣民眾黨」黨中央和部及黨支部的全黨組織消息時,則無主幹一職,各黨支部外報導如下:
中央各部主任
總務部主任 彭華英
政務部主任 王鍾麟
財務部主任 蔣渭水
組織部主任 吳淮水
社會部主任 洪元煌
調查部主任 許嘉種
宣傳部主任 盧丙丁
形同於新春伊始以唯一台灣人辦的報紙昭告天下,「臺灣民眾黨」無主幹(負責人),中央係由其各部主任共治,此亦反映黨內鬥爭何其激烈。
蔣渭水強勢斬亂麻 后經幾番內鬥,「臺灣民眾黨」於1929年5月26日在台北本部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會中議決除名彭華英,蔣渭水快刀斬亂麻,立即通知該黨各支部除名彭華英。接著1930年10月1日,蔣渭水毅然於是日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除林獻堂外,將蔡培火、陳逢源、洪元煌等16名參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跨黨份子,予以除名,林獻堂憤而通告退黨。
回想這與三年前,蔣渭水提出要推舉林獻堂再出任新政治團體的總理一職,是何等的謙卑,及林獻堂堅拒出任總理領導一職,依邏輯推理,蔣渭水或禀於林獻堂威勢/或為了團結,新成立「臺灣民眾黨」居然不設黨主席,故「臺灣民眾黨」雖然在台灣歷史上是第一個政黨,但也是第一個/或唯一個没有黨主席的政黨。因為隨著「臺灣民眾黨」的迅速茁壯,島內政情的快速變化,蔣渭水在台灣政治地位的迅速竄升,儼然島民第一人,結果今非昔比,蔣渭水也完全判若二人。
蔣渭水/謝春木的竄升崛起 惟自1927年7月10日「臺灣民眾黨」成立始,臺灣民眾黨各地黨支部如宜蘭、基隆、汐止、臺北、桃園、新竹、大甲、清水、臺中、南投、彰化、北港、嘉義、臺南、高雄等15個支黨部,半年不到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 ,「臺灣民眾黨」還於年底(12月13日-26日)舉行歲末全島各地演講會 。
1928年時除了「臺灣民眾黨」例行各式活動、全島各地工會紛紛成立,及高雄/臺南工會罷工等,一時間紅紅紅火火,蔣渭水和謝春木二人年青力壯全年全島走透透,或演講宣傳黨的理念、或深入群眾、處理罷工,排難解紛、服務基層、氣勢之盛,遠非舊文協的林獻堂等所可相比。
在事涉政治論述方面,從《民報》尚在海外發行,到1923年6月臺灣民報社成立時出任董事,一路走來,作為與《臺灣民報》因縁最深的蔣渭水 ,可說也是受益於《臺灣民報》此一台灣人唯一輿論平台的報紙,例如單是「臺灣民眾黨」1927年7月成立後的半年間,蔣渭水於10月23日在《臺灣民報》刊登﹤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謝春木以筆名追風於10月16日和30日在《臺灣民報》刊登﹤民眾黨は如何に戰ふべきか﹥(30日其二部分因審查未通過,還遭日本殖民當局開天窗呢!)、11月6日刊登﹤現在の農民運動﹥。蔣渭水和謝春木二人以具有中國國族高度的政治意識,提出台灣社會問題。1928年1月1日元旦,蔣渭水更在《臺灣民報》上發表〈我理想中的民眾黨〉一文,提出民眾黨路線的指導原理 ,亦即宣示黨的路線。類此高端層次的論述,是常年源源不絕,謝春木緊隨其后。
回首歷史,「臺灣民眾黨」生於內憂外患,內有林獻堂派的壓力/外有殖民政府的壓力,搞得成立時黨中央居然無黨主席,蔣渭水以財務部主任職銜,名不正言不順的率領「民眾黨」。蔣渭水帶著謝春木二人備極艱辛的勤走基層/各黨支部,發展組織;在政治論述上,蔣渭水常年不斷探討黨的路線,謝春木則從殖民地政府在教育/經濟/法律等各統治領域的不平不公為民發聲/為同胞爭權益,二人一步一腳印地建立領導威望/領導正當性。
無可諱言,「臺灣民眾黨」如此有組織/有論述/有理想的快速崛起,其掀起的政治漩風/力道/規模/影響,是遠非同期間的其它政治團體所可比擬。但古人有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民眾黨」掀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的政治風暴,日本殖民政府不可能容忍,經過慎密計劃,羅織罪狀,於1931年2月28日下令解散。
林獻堂派系完成階段性的歷史任務 作為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領導層的林獻堂,自梁啟超訪台及在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諸多政治活動的第一階段,表現亮麗閃爍,可說是第一代台灣社會運動領導者。
無奈隨著文協「啓蒙運動」的「進入實際運動」後,林獻堂派系力量囿於年齡/知識/資本家屬性等因素下,面對後起之秀力量,客觀而言實在是力有所未及。林獻堂派系可說完成了日據時期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的第一階段歷史性任務,長江後浪推前浪,無可奈何!
謝春木敢為天下先-為同胞發聲
在教育方面 日本殖民統治在教育上是高強度剝奪台灣人子弟的受教權。以中學校在校學生平均數為例,在1926-1935年十年間,台灣人佔全台灣人口數之94.9%,但中學校在學人數台灣人子弟僅佔40.8%,在台日本人佔全台灣人口僅5.1%,然而中學在校學生數日本人子弟卻佔59.2% ,這就是殘酷的異民族歧視,是何等的殘酷!謝春木因其天資極其聰穎,高中/大學都是第一名畢業,是當時接受完整現代教育的受益者,但即使是在異民族的殖民統治下,年青僅23歲的謝春木卻敢於公然為同胞發聲,自1925年5月1日刊登其以“追風"所撰〈共學之內容〉一文始,1925-29年間多次為文,以披露總督府公佈之具體數據材料方式,使同胞瞭解「台灣人の教育機會の實情」。謝春木此一正義凜然道德特質,躍然在斯時台灣社會,並增加作為一個反日的中國民族主義政黨「臺灣民眾黨」的政治高度。
在法律方面 面對日本殖民統治者藉由法律形式鎮壓之實,謝春木用筆名“追風"以〈臺灣人的法律生活〉為名撰文刊在《臺灣民報》,以逆耳的話舉野蠻法律《匪徒刑罰令》、及無罪着罰的保甲制度功過。此外,謝春木亦以〈平民常識〉為由在《臺灣民報》公開將《治安警察法》《臺灣違警例》等法令,翻譯成中文,俾免同胞誤觸法令,真是用心良苦。
在經濟方面 1929年11月10日-12月22日,謝春木在《臺灣民報》以「臺灣產業資料」為名發表長文﹤農業から見た臺灣(從農業看臺灣﹥,連載六次,接著以﹤農業生產と臺灣人の地位(農業生產和臺灣人的地位)﹥為文總結 。全文以日本殖民當局公布的統計數據,分析批判日本殖民當局的農業政策
其它重要文章,諸如1927年8月7日刊載《臺灣民報》﹤土地政策に就て﹥(關於土地政策)之文,則公然疑慮總督府的土地政策 ;有以“追風”筆名於同年11月6日在《臺灣民報》發表之﹤現在の農民運動﹥,從竹林問題、二林蔗農運動、官退者土地問題、古坑庄芎蕉、中壢芋拓殖會社農民紛爭等,分析所謂植民地特殊地區特色,反映日本帝國主義治下臺灣農民生活的臺灣農民運動 。全都是立足於同胞立場,為同胞發聲,公道自在人心。
在社會運動方面 1930年7月16日-9月27日,謝春木以記者身份,在《臺灣民報》發表﹤臺灣社會運動十年史概要﹥長文,連載十一次。因以文化的近代組織方法從事抗爭始於大正三年(1914)的同化會運動,故謝春木從同化會開始記敘詮釋,探討最近十年來臺灣社會運動的系統及其對立關係,全文自同化會的歷史意義開始、從啓發會到新民會、臺灣議會、文化協會、從新臺灣聯盟組織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實際運動!、蔗農組合、文協的分裂/民眾黨與文化協會對立、工友總聯盟、到概觀,一氣成呵,完整大氣客觀地記述分析各派系分裂抗爭的1930年代十年臺灣社會運動 。全文總結時,謝春木認為「臺灣民眾黨」因自我認識明瞭、目光指向階級解放,在運動中善於運用民族感情,全力關注現實問題鬥爭,故較為一般大眾支持 。
林獻堂熱誠接待石塚總濬vs.蔣渭水/謝春木立足國族為民仗義 無可諱言,謝春木和蔣渭水二人充分利用《臺灣民報》這個平台,或抨擊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性、或介紹新興中國大陸、或介紹中國大陸政治現勢,就以《臺灣民報》1929年11月10日和17日兩期而言,每期同時刊登謝春木的﹤農業から見た臺灣﹥﹤旅人の眼鏡﹥和蔣渭水的﹤中國國民黨の歷史﹥,每期三篇重量級批判日帝及高度中國情懷的文章。
反觀林獻堂派,在「臺灣民眾黨」遭解散前五個月前(1930年8月7-8日),林獻堂還赴車站迎接石塚總督,並在霧峰林宅設宴款待到訪之石塚總督等一行,共進午餐。席間,林獻堂敘禮之辭曰:「總督閣下及令媛登新高山實為空前之壯舉,山靈特表現其陰晴風雨自然偉大以示閣下,而閣下之胸襟得以容納此自然之偉大,令人欽仰不置。今日辱訪林家,林家不能如山靈表現其真相以示閣下,頗為殘念,然表示觀迎之誠意,當能十分也。總督答辭林家之繁盛,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願此後同為國家盡力。」 此外,「林獻堂卻在《臺灣民報》上長篇連載其﹤環球遊記﹥,尤其是「臺灣民眾黨」在遭日帝迫害強行解散之際,《臺灣新民報》(第352號/1931年2月21日)卻仍在連載他的﹤環球遊記﹥第120次。
前述蔣渭水/謝春木派與林獻堂/蔡培火派,種種情事兩相對比,不也是歷史的可貴可珍,兩派的理想性/其對當時台灣社會的影響/其對現時中國台灣社會傳統忠孝價值的影響,高下立判。
世代差異 當然,另外也含年齡的代差問題。就資產財富而言,林獻堂、林幼春、林階堂的霧峰林家是門閥冠絕全台的超級大資本家,蔡惠如也是台中清水望族的有產者,當時本土媒體《臺灣民報》就是由霧峰林家以股份董事主控,例如該報1928年董事林幼春生於1880年、林呈禄1886年、蔡惠如1881年、蔡培火1889年、蔡年亨1889年、林階堂1884年、楊肇嘉1892年,蔣渭水1891年。至於謝春木則是生於1902年。以謝春木與林幼春/蔡惠如相較,年齡相差22歲,不但有代差,而且是1895年割台的不同歷史世代(historical generation)。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等可說是清末的「遺民世代」,清朝割台時生於1880年的林獻堂已16歲,接受了完整的漢文中文教育,故日據時林獻堂坦言「不解國語(日語)、不識和文」 ,無法直接處理需與日本殖民當局交涉的諸事。
謝春木則是日本殖民下成長的一代,在6-11歲時接受強化的漢文教育,隨後也接受了自小學/初中/大學的完整日本殖民教育,聰慧的謝春木的日語運用能力不但能寫日文小說,還能寫日文詩,並且接受新時代的現代知識,使得日後諸多事情如辦理「臺灣民眾黨」的申請組黨/調停各地工運罷工等,謝春木與日本殖民當局斡旋均遊刃有餘。因為,依邏輯推理,對日本殖民當局官僚/會社(公司)負責人等而言,謝春木是他們日本佔領台灣七年後才出生,接受完整殖民教育後又赴東京留學一口流利日語的25歲美少年,總是三分好感好溝通嘛! 年青的謝春木還於1928年出任《臺灣民報》的和文科主任,尤其是謝春木敢為天下先,利用其高階日文能力及現代教育知識,撰文從政治/教育/法律/經濟諸多領域,披露殖民統治高度歧視的殘酷性。
回首日據五十年,無可諱言,結果是林獻堂派系日據五十年平安渡過,其他派系/團體則分崩離兮、成員或奔赴祖國、或被逮捕坐牢、遭刑求/或遭處決。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謝南光:從台灣民眾黨到中國共產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Social Sciences |
$ 323 |
社會人文 |
$ 342 |
中國當代人物 |
$ 342 |
毛澤東及中國近/當代人物 |
$ 342 |
社會人文 |
$ 342 |
歷史人物 |
$ 342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謝南光:從台灣民眾黨到中國共產黨
謝南光(春木)是台灣二林人,1902-1969,功在祖國,一生跨越日據、民國、光復和解放后四個時期,是兩岸近現代的傳奇人物。
謝南光是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十年的風雲人物,他以《臺灣民報》為平台,敢於自教育/法律/經濟各領域公然抨擊日帝,為同胞發聲,正義凜然。謝南光並以其長才大力協助成立「台灣民眾黨」,因建黨有功並積極參與後續黨務活動,著有貢獻,使渠成為僅次於蔣渭水的黨內第二號人物。
謝南光於1931年底前赴上海,於中共最困難時之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代後期抗戰軍興,祖國面臨生死存亡內地未嘗思及收復台灣之際,謝南光在重慶高瞻遠矚地推動台灣光復運動,對我國收復台灣可說居功厥偉。謝南光於1952年回歸祖國,依白色恐怖戒嚴年代時台灣的說法是“投共”,故無論是在戒嚴年代及其后本土政治勢力崛起,謝南光在台灣被蓄意遺忘而名不彰。但因為謝南光是研究日據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十年史無法逾越的著名政治人物,故在學術界仍二三以其為研究的對象。
但就整個近現代兩岸史,謝南光光榮一生的歷史,不應因政治原因遭埋沒/誤導,政治治理是一時的,政治價值是永恆的。故本書以嚴謹學術方式,深入史料辛勤紮實耕耘,還原謝南光的歷史真相。
作者簡介:
戚嘉林
原籍湖北、1951年生於台灣,輔仁大學商學士、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Pretoria)國際關係學博士。台灣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格,曾任外交官,曾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現為《祖國》雜誌發行人/社長,並在世新大學兼任授課。著有《台灣史(增訂四版)》、《台灣史問與答》、《中國崛起與台灣》、《台灣二二八大揭秘》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三章 台灣民眾黨
第六節 謝春木vs.台灣社會運動十年
1920年代是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的十年,期間文化政治論述與各團體/政黨組織的蓬勃發展,宛如我國春秋戰國,蔚為台灣近代史上不可抹滅的光輝十年。謝春木因本人經歷走過這十年的社會運動,在其敏銳的觀察下,有其精闢獨到的見解,可參見其所繪製的「近代社會運動系統圖」
政治宣傳vs.組織發展 在政治宣傳方面,自1921年7月16日創刊《臺灣青年》雜誌、1922年改名《臺灣》、1923年4月15日創刊《臺灣民報》半月刊雜誌、10月15日《臺灣民報》由半月刊進為旬刊。1924年6月停刊《...
第六節 謝春木vs.台灣社會運動十年
1920年代是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的十年,期間文化政治論述與各團體/政黨組織的蓬勃發展,宛如我國春秋戰國,蔚為台灣近代史上不可抹滅的光輝十年。謝春木因本人經歷走過這十年的社會運動,在其敏銳的觀察下,有其精闢獨到的見解,可參見其所繪製的「近代社會運動系統圖」
政治宣傳vs.組織發展 在政治宣傳方面,自1921年7月16日創刊《臺灣青年》雜誌、1922年改名《臺灣》、1923年4月15日創刊《臺灣民報》半月刊雜誌、10月15日《臺灣民報》由半月刊進為旬刊。1924年6月停刊《...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謝南光(春木)是台灣二林人,1902-1969,功在祖國,一生跨越日據、民國、光復和解放后四個時期,是兩岸近現代的傳奇人物。日據時期“中華民國"未曾統治台灣,但當時台灣的祖國派視中國為祖國,深信中國國情必可恢復,收復台灣,雄飛世界,謝南光就是祖國派亮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謝南光是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十年的風雲人物,他以《臺灣民報》為平台,敢於自教育/法律/經濟各領域公然抨擊日帝,為同胞發聲,正義凜然。謝南光並以其長才大力協助成立「台灣民眾黨」,該黨後成為島內第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政黨。謝南光因...
謝南光是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十年的風雲人物,他以《臺灣民報》為平台,敢於自教育/法律/經濟各領域公然抨擊日帝,為同胞發聲,正義凜然。謝南光並以其長才大力協助成立「台灣民眾黨」,該黨後成為島內第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政黨。謝南光因...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家世、求學與追風
第一節 謝春木家世 1
第二節 反日思想萌芽 7
第三節 文藝青年“追風" 10
第二章 走上反日的民族主義道路
第一節 加入「臺灣文化協會」 19
第二節 進入台灣民報社 23
第三節 批判殖民地台灣教育體制不公 27
第四節 批判殖民政府強制收買台灣農民土地 31
第五節 揭露殖民地台灣人法律生活的危逆之處 35
第六節 廢學返台參與政治活動 37
第三章 臺灣民眾黨
第一節 文化協會大分裂 45
第二節 台灣民眾黨-台灣第一個政黨 48
第三節 黨內蔣渭水/蔡培火兩派傾軋火拼 62
第四...
第一章 家世、求學與追風
第一節 謝春木家世 1
第二節 反日思想萌芽 7
第三節 文藝青年“追風" 10
第二章 走上反日的民族主義道路
第一節 加入「臺灣文化協會」 19
第二節 進入台灣民報社 23
第三節 批判殖民地台灣教育體制不公 27
第四節 批判殖民政府強制收買台灣農民土地 31
第五節 揭露殖民地台灣人法律生活的危逆之處 35
第六節 廢學返台參與政治活動 37
第三章 臺灣民眾黨
第一節 文化協會大分裂 45
第二節 台灣民眾黨-台灣第一個政黨 48
第三節 黨內蔣渭水/蔡培火兩派傾軋火拼 62
第四...
顯示全部內容
|